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13—P14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原题《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百年论述及其话语发展》,摘自《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1期,周学军摘


“中华民族”作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概念之一,虽然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产物,但在文明渊源和文化传承上却连通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从现实维度上看,“中华民族”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人群基础,也是确认“国家”与“民族”双向对应关系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政党,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阐发与创新发展,来源于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形而上”提炼和对中国国情具体而微的观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对于“中华民族”内涵和概念的界定与把握,直接关系到它所指向的目标与团结的对象。“五四”前后,“中华民族”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也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作为理解中国社会和阐释自身政治主张的关键一环,“中华民族”自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针对中国如何得救、中国革命如何团结国民等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均对“中华民族”这一论题倾注了大量心力,并展开了深入论述与探讨。他们认为,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在国民大革命和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伴随着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动员,特别是在与各少数民族产生直接深入的接触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团结“中华民族”开展内外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受。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也是中国各界对于“中华民族”展开热烈讨论的又一高潮时期。在此阶段,为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东亚民族主义”和“东亚协同体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基本概念与内涵范畴等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与论述,其间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和见解广泛散布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政策及其领导人的著述讲话之中。
除对“中华民族”的基本概念与内涵范畴展开系统论述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不仅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情境和中国土壤下的生根生长,而且也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中华民族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潜在张力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
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既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铭记于心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历史重任。在革命年代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及系统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上厥功至伟,它不仅很好地承担了思想引领和制度黏合的作用,而且也成功地将差异化的各族人群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人民”,从而使中华民族在结构与人心的双重意义上均得以被铸牢和夯实。但具体到港澳台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涉及相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如何相互兼容共处的问题。这就需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和民族情感出发,通过各个地区对于共同性“中华民族”身份的深切体认,来统辖和超越彼此在制度体制上的具体分歧。由此,“中华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得以进一步彰显:不仅中华民族自身的团结凝聚需要政治国家的引导与支持,政治国家的和平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同样需要中华民族为之提供内在性的情感认同与道义支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要发挥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通过对“中华民族”之历史生成性与内在凝聚性的深入阐发,明确中华民族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承和联结作用,从而把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中国政治国家的统一性直接联系起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阐述中国多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考察中国现实民族状况以及分析中国民族关系与格局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们当年更多还是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华各民族流动迁徙的民族史分析、不同区域和民族文化单元内在关联性的论证,对中华民族内部的多层次结构及不同结构层次之间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进行了整体性观照。因此,它虽然能够系统论证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是如何形成和维系的,却没有言及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直接关联。中国共产党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地发现并回应了这一根本性问题。通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强调和引申,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关话语直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用以解释中国国情、阐述政策方针以及处理民族事务的重要逻辑依据和理论支撑,它的指向不再只限定为文化层面,而是立体性的。由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就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学术话语,而是进一步上升成为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它与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奋斗进程,紧密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和理论体系。
新时代以来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相关话语阐述中的地位和意义变得更为凸显。在“中华民族”这一本体概念及其内涵属性的阐发上,中国共产党赋予了其更具纵深性的内在结构和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
由强调“中华民族”,到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二者之间不仅仅是话语的转变,而且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现实国情与历史奋斗使命的认识把握上,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清醒头脑和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民族”之后加上“共同体”,意味着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更加突出“中华民族”的“团结性”与“共同性”。而且,这种“团结性”“共同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有所不同。当时主要是基于推进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深层考虑,是将中华民族自外向内推向“团结”。新时代所强调的“团结性”与“共同性”,则是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性要素的确认,是由内而外的“团结”,这在程度和性质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还强调要在“意识”层面予以“铸牢”。这意味着,新时代不仅要追求中华民族“团结性”与“共同性”的外化于行,还要将之内化于心,在人心和灵魂层面上巩固下来。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目的是把各民族群众更好地团结起来,并在更深层次上凝聚为一体,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牢固紧密的双向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中华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之聚合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之下,勠力同心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上升成为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之后,其内涵意义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挖掘与提炼。简言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既是对于中华民族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系统调适和有机结合,也是能够完整准确归纳中华民族性质与特点、真正在历史与实践逻辑上实现高度自洽的重要理论概念。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一论述,也意味着在“中华民族”及其纵深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已经实现了形而上的“扬弃”过程和更为清晰透彻的理论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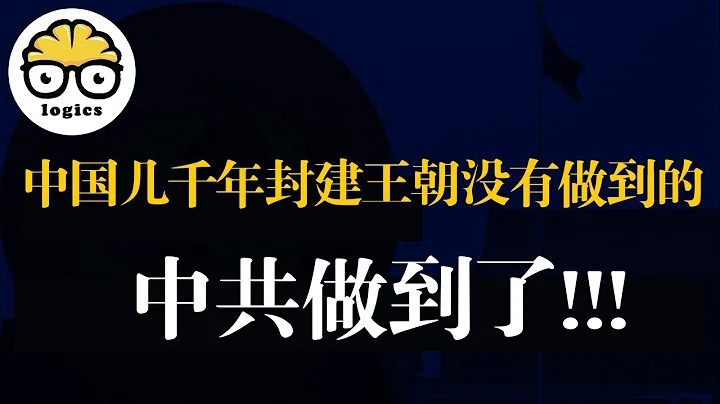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