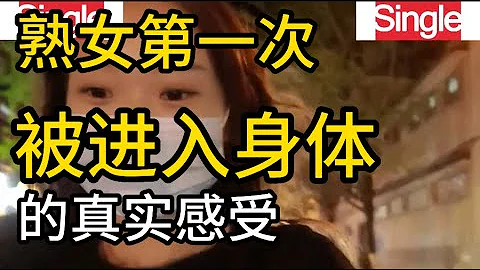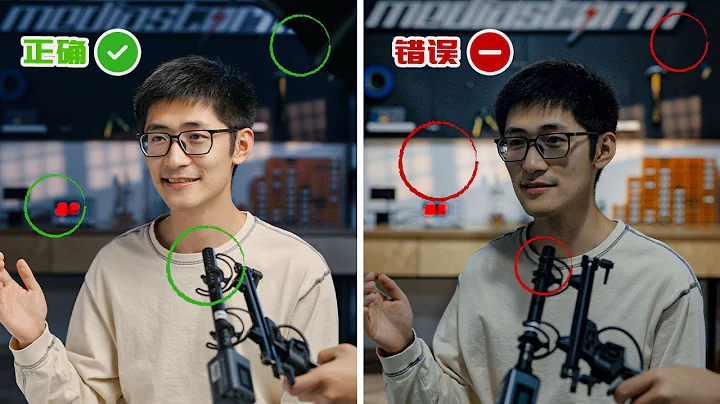⩥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世界范围内纪录片确立独立地位是在20世纪20年代,格里尔逊提出了 “documentary”一词。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具有像档案、文献一样的功能,因而可以用来进行宣传教育;其次,他强调纪录片的根本任务是“对现实进行创造 性处理”。这就是说,纪录片可以用于宣传教育,但是不能突破纪实精神的底线。

此后20世纪50年代起“直接电影”“真理电影”“真实电影”等理念蓬勃发展, 纪录片是“非虚构影片(non-fiction film)”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再到20世纪 90年代兴起的“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开始对于“非虚构影片”的否定,纪录片经历了“虚构——非虚构——再虚构”的完整回归。

这个过程中一 直保持不变的则是纪录片不依赖新闻和电影等其他任何影像类型的独立性,这恰 恰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存在的问题:电影方面新闻片与纪录片分不清边界,电视方 面专题片沿用电影新闻纪录片的模式。寻找中国纪录片独立性,最根源是要将三 者界限廓清。
«——【·“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
以建国后纪录片发展为基准,从时间上梳理三者,可发现“新闻片”与“纪录片”最初是混杂的。1953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统管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与发行。

基于技术的限制,两者分属一处管理,长此以往便造成了“新闻片”“纪录片”“纪录电影”等概念混杂不分的状况。单万里认为1976年后“新闻 片”与“纪录片”逐渐分离,1但两者分离的具体时间却无从判断,至90年代还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专题片”,而对于“专题片”概念也是不明确的。

根据1992年大连出版社出版的《新闻通讯员手册》称“新闻纪录影片”是“运用电影手段进行新闻报道的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属于新闻范畴,在表现手法上具有电影艺术的某些特征”1,足以证明“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持续时间之久, 混沌迷离的情况甚至持续到九十年代。

既然冠以“纪录”一词,为何不将其归入 纪录片的范畴,如此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离的标准是什么。纪录片脱离电影独立存在的地位,主要是划清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 界限。

因此往往会将非“故事片”归为“纪录片”,以至于后期发展出的美国“新闻电影(journalisme filmé)”德国“论战电影(un cinéma de combat)”等诸多类型都被冠以“纪录片”的名号。这类影片制作时使用最新摄制的纪录片镜头, 更多地是传递新闻事实,本质与格里尔逊认为的纪实性相符,将其归为“纪录片”是合理的,但是这也只能证明“新闻电影”可作为“纪录片”的小众分支。

20 世纪20年代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久,很多影片公司都是既拍故事片又拍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多用资料片编辑后演变为宣传电影,但创作者大多只管拍摄, 不探究理论,中国纪录片本身就处于相对蒙昧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与苏 联交流学习,大多西方的理论并未有效的传播,长此以往便造成了“新闻片”与 “纪录片”的混杂,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经过纪录片的独立化就直接将“新 闻纪录电影”意义扩大至“纪录片”,“新闻电影”带着“纪录片”的画皮偷偷 篡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原因,西方纪录片相对独立于政府,而中国纪录 片对于体制有高度的依附,加之技术的局限,新影厂拍摄大量影像用以制作“新 闻片”,这也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而编辑和生产“纪录片”的空间则没有那么 大。这种局面的改变主要从电视的普及开始,这意味着故事片有了更大的市场, 纪录片也要开始转型,“电视纪录片”隆重出场。

只是电视刚开始普及,电视新 闻工作者可谓毫无经验,很多电视新闻工作者过度依赖报纸、广播等现有的新闻 资料,创作出来的作品势必存在相似性,许多作品在成片上仍然属于“新闻片”。 这时再看专门从事纪录片创作的机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其中的“纪录”一词与“documentary”是不能划等号的。

新影厂所说的“纪录”大范围指的是将发生的重大事件通过摄影技术保留为文献,并不是将其进行“创造性处理”生成“documentary”,这样就能理解八十年代初期所说的有关名词诸如“新闻电影”“纪录电影”“新闻片”“纪录片”“新闻纪录电影”等,只有“纪录片”一词与“documentary”最为接近,其中所谓的“汇编电影”应当是距离纪录片最近的影片了,其他大多都应划分至“新闻片”的范畴。

毕竟“新 闻片”与“纪录片”两者从职能上来讲新闻片更重要的是传播新闻事态,纪录片 更多是“对客观事物的记叙、描绘和评论”。
1976年后“新闻片”与“纪录片”开始分离,电视普及只是一个开始,表现并不明显,真正能明确“纪录片”脱离“新闻片”是80年代文献纪录片的繁荣,这种基于文献档案整合的纪录片才算真正认可了格里尔逊对于“documentary”的定义。

后期基于文献纪录片演变而来的政论片更是将“新闻 片”与“纪录片”拉开了距离。20世纪20年代就独立的“documentary”在中国 步履维艰,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了实践与理论的统一。
«——【·“纪录片”与“专题片”·】——»
20世纪90年代,新影厂并入中央电视台(1993),影视合流、内外接轨,此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专题片”,这一说法可谓是中国的“创造发明”。最终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专题片”的说法开始淡出并逐步被“纪录片”一词取代。

但“纪录片”与“专题片”到底有何区别却没有定论,2006年《文汇报》 报道《忠贞》时在3月9日与4月1日分别使用了“大型文献专题片”与“大型文献纪录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当然,学界也曾对此作过讨论,部分学者认 为对两者进行区分和定义会束缚电视人的创作实践,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不将两者区分,更不利于纪录片理念持续发展。

因为两个概念总是分不清,因此还出现了“纪录专题片”以及“专题纪录片”的说法。直到2011年张瑞林的《专题片与 纪录片属性再议》,2012年熊高的《视觉传播下对电视专题片的再认识》等文章还在对这一争论进行探讨。实则如果理顺改革开放前中国纪录片发展流变,就 能明确“专题片”实际是从“新闻纪录片”即“新闻片”发展而来的。

关于“专题片”与“纪录片”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无论讨论多么热烈,都改 变不了“专题片”即具有“新闻片”特征又具有“纪录片”特征的状况。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节目需求量增多,电视片逐步发展繁荣,1976年就已然出现了“电视专题片”这一名词概念,而这一时期却是“新闻片”与“纪录片”尚未明 晰之时。表面看是“专题片”与“纪录片”的斗争,实则是“新闻片”与“纪录 片”的博弈。随着“新闻片”与“纪录片”逐步分离,“电视专题片”也在潜滋 暗长,当两者明确分离时,专题片也羽翼丰满。

反观西方却没有“专题片”类似 的概念,如此“专题片”的出现便可归因于中国纪录片独立性的缺失。如果说“新 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给与中国纪录片完成独立的喘息之机,那么“专题片” 的出现则是将中国纪录片独立化搅得天翻地覆。
«——【·结语·】——»
直至2010年前后才有学者将专题片与纪录片彻底区分开来,并将专题片划归至新闻片的范畴。之所以总是出现混沌,则是因为电视兴起带来了节目需求,创作者想要抓住受众则需要不断学习与创新,但是发展长期滞后的中国纪录片,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难在短时间将最新的理论与手法进行完整地消化,然而 拍摄手法和理念鱼龙混杂,创作者们只管学不管分,学得太多太快势必会造成创作上的积食,“专题片”被创造了出来,却不知它是什么。

因此,对于“纪录片”与“专题片”不可通过一刀切来分类,如将90年代在国际获奖的诸如《沙与海》的此类影片都算作专题片,那么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必将一片苍白。可以说新闻片 与纪录片的分离,纪录电影与电视纪录片的分离,专题片的不断增多都促使中国 纪录电影艺术开始觉醒,这也是纪录电影进行艺术探索的前提。
«——【·参考文献·】——»
1.Judith N,Martin,Thomas K,Nakayama,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M]foreing language teavhing and resesrch press
2.[英]斯特拉·布鲁兹,新纪录:批评性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日]小川绅介著山根贞男编冯艳译,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M],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