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秀云,1967年出生的,7岁之前我是幸福的。7岁之后,我沦为养女了,养母是我的邻居大妈,没出五服的本家亲戚。
说起来,大妈也不是什么高尚之人,她之所以愿意收养我,这得益于她和我爸之间的一场交易。
什么交易呢?
据说,我爸用三间大瓦房做交易,我才成了大妈的养女。
我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爸爸手巧,会木匠活,也会瓦匠活,属于双料工匠。在农村,手艺人是吃香的,谁家盖房子,娶媳妇打家具什么的,都少不了来请我爸,活多了就收钱,活少了,我爸也乐于帮忙。
不过,村里人还是懂礼数的,我爸帮了人家的忙,人家少不了一扎桃酥,两个黄桃罐头,遇到讲究人家,还有二瓶二锅头呢。
在那个吃玉米面饼子,咸菜疙瘩的年代,我们家因为爸爸的手艺儿,日子过得算是小资生活了。
可是,我妈有点“不争气”了,在我7岁那年夏天,查出了白血病,妈妈去医院走了一趟回来,再也不肯治了,她知道,她的家族长辈有得这个病走的,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该走还是走了。
我妈铁了心不治了,她扛过了夏天,扛过了冬天,就在小草发芽,万物吐绿,春天来到的时候倒下了。
妈妈走了以后,我爸突然冒出个想法,他要去城里闯荡,那个年代也没有打工一说,去城里闯荡的人叫盲流。

“盲流”这个词有点贬义,村里人见了我都会说,你爹去城里当盲流了,我那时也懂事了,别人这样说,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更恨爸爸了,恨他为什么给我扔下,恨他为什么去当盲流呢。
想起我爸走时哄我说:“小云,你听话呆在大妈家,等爸去城里把家安好了,就接你去城里上学。”
我信了。
每天晚上都站在村口,朝着城里的方向张望,我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有时候,遇到我熟悉的叔叔,大爷,我还会问,看见我爸了吗?
后来,遇见村里的倪大爷,倪大爷爱捣腾个鸡鸭鹅什么的。
有一天,倪大爷骑着摩托车,车后载着个铁笼子,骑在我面前停下了,他告诉我说;“我见到你 爸了,你 爸在城里娶媳妇了,还给你生个小弟弟,怕是不会要你了。”
倪大爷这不等于往我脑袋上泼冷水吗,他几乎浇灭了我所有的期望,爸爸有了新家,肯定不会要我的。
那天夜里,我把自己整个地蒙在被里,也不敢哭出声,就让眼泪沽沽地流。
寄人篱下哪敢在人家的地盘上 发泄情绪呢。我先前觉得自己是没妈的孩子,可现在,是没妈没爹的孩子了,我的世界里,孤零零的,只有我自己了。
我在大妈家是不受宠的,大妈家三女二男,我在这个家男女混合排老五,下面还有个弟弟,我的主要任务是看弟弟。
弟弟比我小三岁,我8岁,他5岁,他不爱走路,老爱跳上我的后背让我背着。
有一天,弟弟趁我蹲在地上,嗖一下子,窜上我的后背。冷不防的,把我拽倒了。
他却让我背着他走,不背就满地打滚。我哪里敢得罪小少爷一样的他?
我背着他正往院子里走,弟弟故意往后仰,我一点准备没有,手不知不觉松开了,弟弟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
当时,直值寒冬腊月,弟弟哭得背气了,养母这时在炕上做针线活,她听到声音后,呼地推开窗户,两只眼睛蹬得血红,操起炕上做针线活用的缠线板,像我飞来,我本能地用脚挡住,缠线板不偏不斜,砸在我的脚上,我的脚一阵功夫鼓起个大包。
我忍着痛,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大妈打孩子是不许哭的,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
我强忍着,一个人走出了家门,一瘸一拐去了东山坡,那儿有个土包儿,我妈妈埋在那里,我只有在妈妈面前才敢放声大哭。
我哭了很久,很久,想妈妈啊。
好巧,大爷从山上下来了,他听到我的哭声了,大爷把身上背的柴禾卸下来,蹲在我的身旁,用那双粗糙老茧的手,为我擦眼泪。
大爷说:“秀云,我答应过你 爸,一定会对你好,不让你在我们家受屈,快告诉大爷谁欺负你了。”
我没有说话,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在脚踝上,大爷看见我肿得老高的脚踝,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把我拽起来,摸摸我的头,满眼疼爱,领着我往山下走去,在这个家里,疼我的要数大爷了。
夜里,我听大爷对大妈说:“人家孩子也是孩子,你不能拿人家孩子不当人,咱家孩子有爹妈护着,小云有谁护着?”
大妈说:“我们养她就不错了,能添一斗不添一口啊。”
当,当,当大爷的烟袋锅子敲打着炕沿。
大爷火了,说:“你别忘了,秀云爸给咱三间房子啊,没有这三间房子,咱不得花钱盖房子,给大儿娶媳妇吗?长点心吧。”
寂静的夜里,大爷大妈的对话,我听得真切。
睡在炕头的二个姐姐早已进了梦乡,只有我躺在炕梢,透过窗帘望见黑咕隆咚的夜空,心和外面的夜空一样的黑洞和悲凉。

弟弟7岁那年上学了,我不用看弟弟了,我也想上学,和我同龄的孩子都上三年级了,都会写作文了,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和大妈说:“大妈,我也想上学。”
大妈说:“你先别上学,你弟弟那个熊样,怕不是个念书的料,万一跑回家不念了,你得在家带弟弟玩。
我点头。”
这事大爷知道,不让呛了,大爷说:“秀云都10岁了,还不好上学吗?”
大妈说:“女孩子,早晚得嫁人,识两字得了。”
大爷火了,怼着大娘说:“你咋不让你的孩子识两字得了?你不是跟秀云爸保证过吗,要对秀云好,做人不能太那个。”
次日一大早,大爷说:“秀云,你领着弟弟一块去上学。
我知道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我早晨比这些孩子起得早,晚上比这些孩子睡得晚。
尽量把作业在学校写完,这样,回到家,就一门心思喂鸡鸭鹅,烧火做饭。
一晃,小学毕业,中学离我们家很远,中午要带午饭,我主动提出不念书了,不为别的,大妈家自己孩子都是一大帮,供他们上学都不容易。
我只要念书,识自己名字,差不多就行,宫女的命非要让人家当皇后宠,是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不上学,也没在家闲着,跟着大爷大妈下田干活,他们打拢,我撒种子,他们犁地,我打土块子,午后的阳光里,有我拉长的影子。

我喜欢我的影子,它在我身后默默的陪伴着我,它陪伴我走过了童年,走向了青春。
走向青春的年月,我的心里住进了一个人,从此,我不在与影子相伴,也不再孤单了。
他是一个令我心动的大男孩,他是邻村的,我们赶集认识的。
我准备下一个集日里,向他表白时,节外生枝了,我们家来了一个陌生男人,长得又黑又丑。
大妈见了他却笑出了鹅叫,男人黑炭色的手从衣兜里摸出一把票子,嘿嘿两声递进大妈手里。
大妈眯着眼睛,她的手指缝里还存着一圈污泥,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妈用手蘸着唾沫星子,来回地数着男人递给他的票子。
数完了,大妈抬起头,一个眼神递给男人。
男人把目光落在我身上说:“我知道你叫秀云,我在集市卖牛肉,见过你,我们也算认识了。”
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怕是他长得又老又丑不吸引人,而我也不买牛肉,当然,没有感觉。
我懒得搭言,低头瞅着自己的脚尖,心里想着,怎么可以逃避这场婚事?大妈为了彩礼,把我嫁给这个男人,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大妈看出我的不高兴了,她说:“秀云,找男人就找这样式的,安心和你过日子,你跟他走吧,以后的日子保你吃香喝辣的,比我们这个穷家强多了。”
我哭了,我真不是恋这个家,我是不愿意嫁给这个男人。
但我还是跟这个男人走了,我想着只有逃出这个家,才能机会嫁给心上人。
我跟在这个男人身后默默地走,好像他领走的不是我,是一头小牛,一头小马。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命运够苦了,大妈又把我许配给这么个人,这辈子怕是跳不出火坑了。
男人走得很慢,好像在等我,他慢我更慢,慢得在原地打转。
男人说:“秀云,你累了,咱就歇会儿。”
我还是不说话,我巴望着男人火了,骂我一顿,我有理由离开他啊。
可人家不但不骂我,还坐下来陪着我说话呢。
这一阵功夫,我发现男人除了长得丑和黑外,倒是挺会疼人的。
被人疼爱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眼前这个男人总让我想起妈妈在世时的爸爸。
那时,爸爸的爱太温暖。我现在像干枯的小树苗,太想喝水了。
不知不觉,跟着这个男人来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他也和我一样的命运,不过,他有奶奶陪伴着长大,比我幸福多了。
不知道怎么,我竟有了家的感觉,我太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也许,这是老天给我安排的家,虽穷,但温暖呢。

次年,我在集上看见了大爷,大爷说起了大妈,他说:“大妈得重病了,她后悔给我嫁早了,身边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
我知道,我上面这两个姐姐都是远嫁,大姐嫁过去后,又给二嫁介绍个县城的小伙子。
在大妈后来的日子里,我还是回去照顾她些日子,不为别的,只为我当时还有个家,不至于沦落街头,至少比我亲生父亲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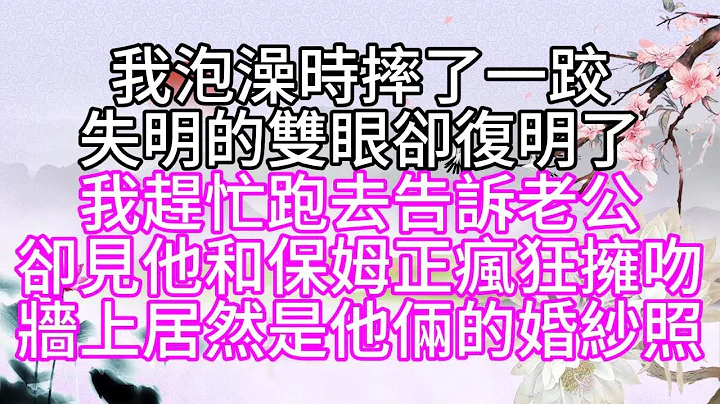







![[ 要搞事情的节奏啊!谁的声音让导师无比熟悉、无比期待 ] 《梦想的声音》第7期 预告 20161216 /浙江卫视官方超清/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iwbbOzIOma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tjukvX-Un3PIiu-clOExy3Upr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