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出版制度的时候说道:“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说的是没有出版自由的结果,也代表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倾向。

马克思是从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开始政治生涯的,无论马克思学会英语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作品,还是学会俄语在俄国的报纸上发表作品,都在利用言论出版自由争取政治权利。而资本主义社会并非要实现人人言论自由,而是要加以限制。有了书报审查制度,就会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宣扬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同时很多出版物也被限制,被筛查。资本和权力注入出版界,审查出版物,只让出版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或者有着娱乐消费导向的东西,而一些带有思想印记的东西并不能出版,就更别提影响人了。很多所谓伟大的作家并不是真正的伟大作家,而是被资本和权力承认的所谓伟大作家,也是为资本和权力鼓吹的作家。苏联的麦德维杰夫写道,这些伟大作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只是在作家死后才问世。”“起败坏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作家生前出版的作品大多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约束,并不能表达自由的观点,也不能直面社会真相,说出内心真实的话语。而他们没有出版的作品在死后出版,倒是说了真话,抒了真情。被审查之后出版的作品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大量删削,要么重新改写,都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不是表达真理或社会良心。
人们看多了这样的作品会以为描写的是真的,社会就是那个样子,其实已经被作品欺骗了,或者说被作家和资本家合伙欺骗了。他们需要传达资本家的声音,表达资本家的利益诉求,甚至直接传递消费主义价值观,传递享乐主义价值观,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而消费增长了,资本也就迅速增值了。

麦德维杰夫写道:“政府只想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或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资产阶级政府控制媒体,制造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说只是发布一些经过审查的新闻,却不会把所有的新闻全都发布出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只是要人们看到他们想让人们看到的东西,而且还要强调这种新闻是正确的,全面的,权威的。于是,人们统统被洗脑,却还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新闻,看到了领导人的雄才伟略,看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丰功伟绩。他们盲目迷信,不是迷信政府,就是迷信权和钱,还有的迷信神灵和命运,却最终要否定自己,因为自己没能耐。只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才会成为有能耐的人,而越是追求,就越是陷入资产阶级设置的陷阱。资产阶级要底层人努力奋斗,争取进入上流社,。而事实上他们早就堵死了底层人的上升通道,提高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槛,也就可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纯正属性,而不会弄很多自以为是的底层奋斗者进来。
这一切似乎都和资产阶级限制出版自由有关系,而越是限制,人们就越不自信,甚至投向了神学的怀抱。资本主义控制出版自由会产生人们失去信仰的结果,还会催生很多怪异的派别,甚至生出很多不是文学的文学,不是文艺的文艺,只是政治传声筒,或者只是为了宣扬资本运作的好处,只是带动人们消费的作品,却不是事实,也不能打动人心。资产阶级会毁坏原有的艺术形式,用资本堆积起来的艺术形式表达资产阶级的诉求,甚至直接为资产阶级支配的经济发展张本,却无视艺术本身的规律。要是用资产阶级打击和摒弃的艺术形式来重新创作艺术作品,似乎才算是走上了艺术创作的康庄大道。
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似乎是资本主义控制出版自由之后生出的变种,却日渐强大,甚至以自残来反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只是,这样“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艺术方式渐渐发展成变态的艺术形式,甚至一些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是身体残疾者就是精神变态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这种艺术形式,而是人们认可了这种艺术形式,甚至无动于衷。于是,鲁迅笔下愚昧而又麻木的一群人再次出现,虽然穿着华丽,住着楼房,不愁吃喝,但依然具备民族劣根性,甚至比阿Q还要自恋和愚昧,也就真的弄得阶层固化,社会结构稳定不变了。

原来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稳定是保证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定,而不是保证劳动人民利益的稳定。劳动人民只是资本家眼里的羊,资本家要“薅羊毛”,而且要世世代代“薅”下去。为了保证这种正当性,资产阶级就要控制出版自由,最终塑造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也最终要稳固地统治下去。不过,以前封建统治阶级也是如此实行的,只不过到了一定的时间,不得不被先知先觉者推下台。或许,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是从控制出版自由开始显露的,只不过他们自以为是,又聋又瞎,假装听不见看不见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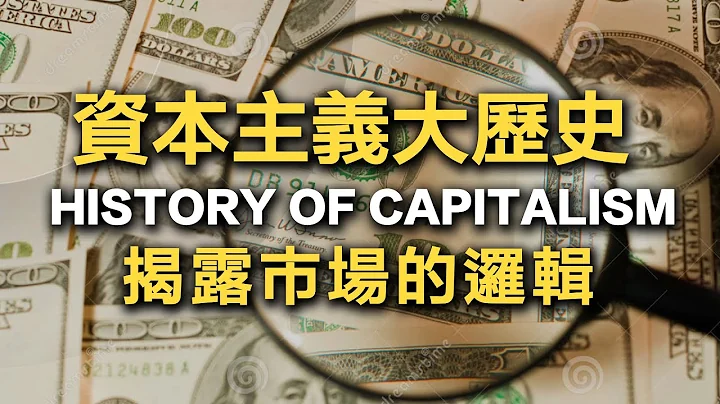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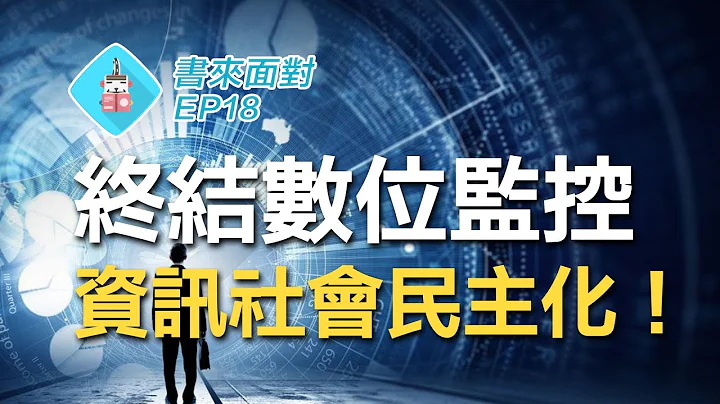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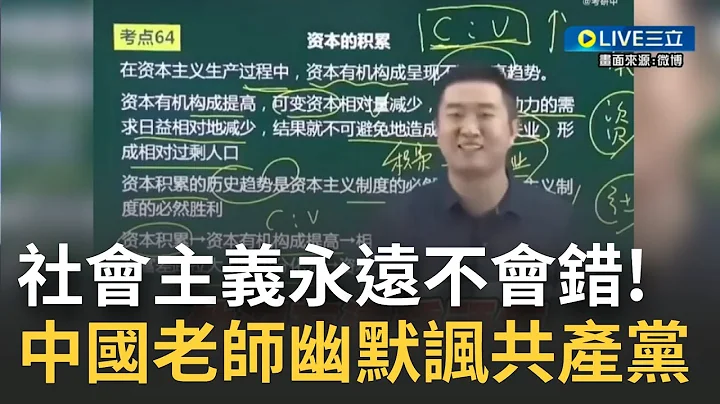





![[Chinese movie 2023]Poor girl helps disabled shareholder, changes fate!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2qSlT5aVHg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zmX0URNZaXthUulfqkBykMpzB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