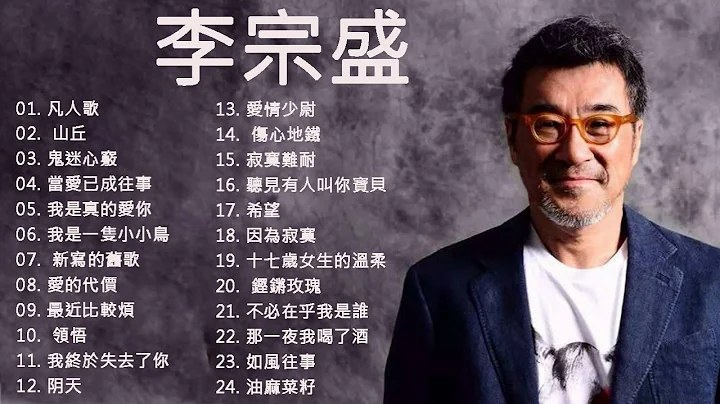上野千鶴子
◎楊早(作家)
鈴木涼美說,她母親是高知女性,就算自己沒工作,也瞧不起周圍的「那群媽媽」,也討厭那些用「女人味」做生意的人,可是,她自己喜歡化妝打扮,還嘲笑那些打扮土氣的同行女學者,「她明明渴望成為價格昂貴的商品,卻鄙視那些實際出賣自己的女人,這讓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徹底賣掉了自己。」
上野千鶴子說,你母親採用的是精英女性常會採用的生存策略,即「我跟她們不一樣」,同時拒絕與家庭主婦與同行女學者共情,其實也是一種厭女症。
鈴木涼美說,我母親全力以赴地愛我,同時我也是她作為兒童文學專家的研究對象,從小我就必須用語言解釋我的所有行為。這讓我窒息。
上野千鶴子說,我們年輕時做的種種無聊的事,都是因為它是「父母禁止的」,一旦父母不在了,這些事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是的,鈴木涼美說,母親去世後,我就徹底從夜世界裡退出了。
……
73歲的上野千鶴子,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教授,日本最著名的女性主義者;38歲的鈴木涼美,東京大學碩士畢業,日本經濟新聞社記者,2022年,她的小說《資優》入圍了日本文學最高獎之一芥川龍之介獎五強。
二人在疫情來襲的第一個春天到第二個春天之間,以二十四封往來通信構成了《始於極限:女性主義往來書簡》,十二個通信主題分別是:情色資本,母女,戀愛與性,婚姻,認可欲求,能力,工作,獨立,團結,女性主義,自由,男人。
翻開書之前,我以為《始於極限》是一本女性主義的啟蒙讀物。尤其它熱度很高,讓我警惕。其實這是那種「好書」:讓人讀後五味雜陳,難於評述,然而你知道終會再次翻開它,因為裡面有太多沒有答案的問題。
「始於極限」,鈴木涼美的解釋是「立於極限的我從自己所在之處審視事物」,上野千鶴子全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日本婦女解放運動,是首批將女性主義帶入學術圈與大眾視野的學者;鈴木涼美16歲進出「原味店」,之後有過夜店經歷,後來出版相關碩士論文。
無論是個人經歷,還是研究層面,她們都走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極限。
可是,她們確定自己越過山丘了嗎?如果確定,就不會有這本書了。
正如書中所言,疫情也是一種極限,生活隨時處於邊界。非正常生活狀態下的通信,卻能產生出意外的表達。「儘管知道書信會被公開,但一想到自己和你一對一『面對面』,我便覺得沒有糊弄與搪塞的餘地」,鈴木涼美的文字也總讓上野千鶴子「前世的舊傷在隱隱作痛」,因此打破了「我賣想法,但不賣感覺」的戒條,不憚於講述個人歷史與身體感覺。
鈴木涼美承認,自己一直強烈抵觸「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發聲」。與母親一樣,鈴木涼美的策略也是「我跟她們不一樣」。她不願意成為被同情與被拯救的對象。(讓我想起脫口秀演員楊笠的段子:「你想看什麼,老娘偏偏不長什麼。」)
上野千鶴子告訴鈴木涼美,其實,「痛了就要喊痛」,身體與精神都是易碎品,「把易碎品當成易碎品對待」。上野千鶴子自嘲說,她這是懷著「親戚大媽心態」。
個人充滿困惑,社會又何嘗不是這樣?東京大學的女學生還會在社交場合隱瞞自己的學歷,以獲得「可愛又沒有威脅」的評價。這讓兩位通信者都覺得可悲:難道女性直到今天還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認可嗎?即使那些在社會結構相當優越的女性,也無法打破「不結婚就不圓滿的幸福神話」。工作成就,經濟獨立,社會認可,似乎都無法消除「結構」對女性的鉗制與影響。
上野千鶴子忠告學生:不要讓自己成為社會用完即棄的物品。她也指出,出現一大批「厚著臉皮」優先自身利益的姑娘,包括追求「好嫁」,或許正是時代的進步。只不過,這種自身利益,不一定要通過男人去追求,也不需要用性別術語去修飾。
受此啟發,鈴木涼美總結了兩種/兩代女性對父權制社會的應對策略:我們這一代學會很多逃避傷害的方法,包括如何使用辣椒噴霧,穿著適當的衣服,但容易忽略質疑社會結構本身,其實是給了男權逃避責任的傾向;現在的年輕女性勇於批評父權社會結構,但只追求批判而不會避讓,容易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兩位通信者都認同身處男權社會的女性「必須兩手抓」,可是「同時做好互相矛盾的事可真難啊」。
最後的結論似乎是絕望的。但「絕望」也是一種極限。如果讓我總結《始於極限》的主題,那會是「如何讓女性主義成為承載著人生經歷的日常」。觀念世界與日常生活之間,往往隔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鈴木涼美的「極限」之一,是她從青春期起的經歷,讓她即使離開了夜世界,也無法再投入認真的戀愛關係,她反覆追問上野千鶴子:為何經歷那麼多「陰溝」之後,您還沒有對男性感到絕望?上野千鶴子的回答是:因為在書本里,在生活中,還是有很多讓人尊敬的男性。
在我看來上野千鶴子的回答相當無力。這個問題的本身,就包含將性別本質化的前提。如果性別是絕對的劃分標準,那就不存在「男的女性主義者」與「爹味女」了。性別本質化的好處是痛快淋漓,壞處是像熱餐刀切黃油,將日常生活經驗切得七零八落。「反正男人無藥可救」「男人,閉嘴!」是斬釘截鐵又有蠱惑力的理念,與現實中的受害者情緒也能呼應。但在邏輯上,這跟《動物莊園》中的「四條腿好,兩條腿壞」沒有區別。
兩位女性作者疫情下的通信完結了,而從極限處開始的探尋與追問,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止女性。
2022-10-30
![李宗盛2013最新單曲[山丘]官方完整版音檔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_qNpR1Ew5jA/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7bxa4PvJfzgOG0-DCeBkPQQGXHA)
![李宗盛2013最新單曲[山丘]官方完整版音檔 - 天天要聞](https://cdn-dd.daydaynews.cc/img/play.svg)




![Jonathan Lee李宗盛 [ 山丘 ] Official Music Video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rVEMTxg_LrU/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9VvOcpBuwq6N-ipIoGsyRXGh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