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年冬,吳國大軍在雍澨(湖北京山西南)擊潰了楚人最後一絲抵抗力量。楚國左司馬沈尹戌戰死疆場,仍然無力挽回戰局!強大的吳軍趁勝追擊,浩浩蕩蕩地殺向了楚都郢。
絕望之中楚昭王被迫帶領妹妹季羋出逃,將郢都白白送給了吳人!

楚王一走,郢都頓時陷入一場浩劫。在攻克郢都後,吳人從王到大夫,按照官階高低,分別住進了楚王宮和大夫家。然後,吳王闔閭以楚王之妻為妻,吳國大夫們則以楚國大夫之妻為妻,公然羞辱楚人!
然而,在楚國令尹囊瓦的家門外,卻產生了一場爭執。囊瓦執政期間長期貪賄,不知搜颳了多少奇珍異寶在家。所以,吳王闔閭兒子子山不管不顧,搶先一步住進了囊瓦家。可夫概自認功勞巨大且是吳王之弟,囊瓦家就應該只配他去住,別人都沒資格。見侄兒居然敢搶在自己之先,夫概大怒,就想率兵去攻打子山。一見叔叔真動怒,子山害怕了,趕緊騰出房屋,將囊瓦家讓給了夫概。
這時,楚國隕邑大夫斗辛聽到了吳人這段風波,在痛恨吳人無恥的同時又不無感慨地說道:「我聽說,『不能相讓就必有不和,有不和則不能遠征。』吳人在楚國爭鬥,必然會產生內亂;有內亂吳人必將回國,還怎麼佔有楚國?」楚都已被攻克,楚王也狼狽地逃到了隨國,楚國名將已損失殆盡,如此絕境之中還奢談吳國不可能征服楚國,憑什麼?
更何況,楚國的敵人還不僅僅是吳國。
因為楚國收留了王子朝,周王室公然與楚國為敵;晉國雖然沒有出兵伐楚,但見楚國倒霉,只會痛打落水狗,根本不可能幫助楚國;其它諸侯國,大多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放眼整個東周,只有隨國頂住了壓力,在危機時刻收留了楚昭王——但顯然,隨國根本不是強悍的吳人對手,無法長期保護楚昭王。

然而,斗辛也不是平凡人,他是名相子文的後裔。雖然在楚莊王時若敖氏被滅族,但因令尹子文的功勞,其後裔卻得以赦免。身為名相之後,斗辛這番話也絕不會是妄言。
可在這個節骨眼上,究竟誰會來幫楚國呢?
就在楚昭王逃入隨國後不久,吳軍就跟蹤追擊到了隨國城門之下。闔閭先派使者警告隨國國君:「周人在漢江流域的子孫,都已被楚國消滅殆盡了。現在上天有靈,降下懲罰於楚,可國君您竟然庇護楚王,周王室有什麼罪?國君您如果願報效周王室,以告慰上天之靈,這就是國君您對寡人的恩惠了。只要交出楚王,漢水以東土地,隨國都可佔有!」
吳王闔閭這番話,對隨人的誘惑力不可能不大。

春秋早期,楚國崛起,不但消滅了漢水以東的諸多姬姓諸侯國,還對隨國展開了瘋狂的進攻。甚至楚武王在去世之際,仍然不忘討伐隨國!長年生活在楚國陰影之下的隨人,不可能遺忘被楚人欺壓的那段屈辱歷史。隨人如果選擇與吳人合作,不但能報昔日大仇,還能佔據漢水之東的大片土地;誘惑如此之大,隨人能抗拒得住嗎?
楚人聽說了此事,頓時慌成一團,急忙商議對策。楚昭王庶兄子期甚至決定主動犧牲自己:「我長得像君王,如果將我交給吳人,君王就可逃過此劫了!」虎落平陽被犬欺,在此時楚人已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在得到闔閭建議後,隨人一時間也舉棋不定:與吳人合作,雖然吳國也是姬姓,但很可能因此引狼入室;救下楚王,當吳軍發起進攻時,隨國又能抵擋多久?
隨國君臣商議多時,都無法定奪,最終只得求助於占卜。不想老天在關鍵時刻居然幫了楚人一個大忙:隨人占卜將楚王交給吳人,結果卻是不吉利!結果一出來,隨人立刻回絕了吳人:「隨國小而偏僻,卻近於楚國。楚人讓隨國保存了下來,世代都有盟誓,至今未改。如果一有災難就拋棄盟友,那又怎麼侍奉君王您呢?國君您的憂患不在楚王一人,如果您能安定楚國全境,敢不從命?」

隨人的意思,吳人征服了楚國全境,隨人哪敢不交出楚王?但如吳人無力征服楚國,隨國在人屋檐下,就不得不遵從楚人了!
雖然隨人拒絕交出楚昭王,但吳王闔閭卻知道隨人說的是大實話:雖然吳國已攻下楚都,但楚地廣闊,南陽盆地北部及方城(今河南方城)之外的眾多楚人還沒放棄抵抗。現在攻打隨國,隨國都城高大而堅固,必然耗費時力。當前首要之事是先消滅楚人有生抵抗力量,而不是幾乎已成孤家寡人的楚昭王!

因此,見隨人不肯交出楚昭王,吳人也就主動撤退了。
看到隨人如此仗義,楚昭王也被感動了:他立刻命庶兄、楚司馬子期在胸口心臟位置割肉取血,來與隨人盟誓!這已經是隨人第二次拯救楚王了:一百多年前,隨人就曾搭救過楚成王;隨國能在南陽盆地存在這麼久,就是因為這次救「王」之功!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在楚昭王躲過吳人追殺後,楚國終於迎來了一位大救星。不過,這位大救星卻是吳軍主將伍子胥的好友!
當年伍子胥在楚國時,與申包胥是好友。在逃離楚國時,伍子胥對申包胥說:「我一定要推翻楚國!」望著悲憤的好友,申包胥心情極度複雜,說道:「努力吧!您能推翻楚國,我必定能挽救楚國!」
在楚昭王逃入隨國後,立刻就派申包胥前往秦國,向秦哀公緊急求救。見到秦人後,申包胥懇求道:「吳人就是害群之馬,侵害北方各國,先從楚國開始。寡君社稷失守,流亡在草莽之中。他命下臣前來告急:『夷人貪得無厭,如果將來與國君您為鄰,那麼戰事必將無可避免。還不如趁吳人立足未穩,國君您前來楚國分取一部分土地。如果楚國滅亡,您所佔有的土地就是秦土了!如果托秦君之福,楚國幸得免於災難,楚人將世世代代侍奉君王!』」十年前在東周還是不可一世的楚國,到了低聲下氣地向人求救的地步,簡直就是一種恥辱!

但更為可悲的是,楚人就是想割地求救,還得看別人臉色——秦哀公深知吳軍的強悍,心中顧慮重重,不敢輕易答應楚人!為此申包胥在秦國宮廷之外倚牆而立,七天不吃不喝,日夜哭聲不絕。
最終,秦哀公被申包胥所感動,寫下了「無衣」一詩,決心出兵救楚!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公元前505年6月,申包胥心裡回蕩著「無衣」一詩,引領著秦國五百乘救援之師,回到了南陽盆地。
秦國援軍雖到,但形勢依然嚴峻。

吳人雖然沒有強行圍攻隨國,卻使出了更為致命的戰術。吳軍主力依然在長江、漢水一帶掃蕩楚軍殘部,卻另外派出一支偏師從南陽盆地之外向北攻擊。吳軍是想利用這支偏師肅清方城之外的楚軍抵抗力量後,再南下殺入南陽盆地,配合吳軍主力來實現對楚人殘餘地盤的南北夾擊!
率領軍隊從南陽盆地外實現戰略包抄任務之人,正是在柏舉(今湖北麻城北東北)之戰中大放異彩的夫概!夫概的軍事才能,足以獨當一面。為此,闔閭派他單獨率軍繞過太行山北上:只要他能迅速蕩平南陽盆地之外的楚人,吳軍在南陽盆地內的南北夾擊戰術就可實現。
所以夫概之師雖然不過五千兵力,但對楚國的威脅卻是迫在眉睫。
為打破吳人戰略包夾意圖,楚人決心先擊退夫概之軍。秦人初遇吳軍,並不熟悉吳人的戰術戰法。因此,秦人主將子蒲讓楚軍先行出戰迎敵,秦軍則前往稷邑(今河南桐柏縣境內)與楚軍會合。
秦國軍隊突然出現,讓夫概始料未及。公元前505年6月,在沂地(今河南正陽境內),夫概被秦、楚聯軍的優勢兵力擊潰,損失慘重!

就在這前後,楚人盟友越國也不失時機地發起了對吳國的進攻。
北上包抄軍隊遭遇重創、越國入侵吳國,不利消息先後傳來,讓留在南陽盆地內的吳軍信心大受打擊,戰鬥力也大大下降。在軍祥(今湖北隨縣西南),吳軍居然被子期率領的楚國殘兵擊敗,無法繼續北上!
7月,秦軍又在司馬子期率領下返回南陽盆地,將唐國(今湖北棗陽東南的唐縣鎮)給滅了,徹底拔掉了插在楚國心腹中的大患!
形勢的發展,對楚國越來越有利了。
9月,為了應對越人的入侵,吳王闔閭不得不命令南陽盆地之外的夫概先行回國,組織抵抗。可沒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夫概一回到吳國,就自行稱王!
吳國後院起火,眼前的楚人卻已緩過氣來,開始發起更加猛烈的反擊。

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楚軍向吳軍發起了進攻,卻再次遭遇大敗;但增援的秦師勇猛如虎,又將吳軍給打敗了!面對秦、楚聯軍,吳軍第一次感覺到力不從心,被迫退到麇(qún)地(雍澨附近)。
見吳軍駐紮之地草木旺盛,子期提出了火攻之計。子西聽了,猶豫道:「楚國父兄親人的遺骸還暴露在那,到現在還未能入殮,卻要燒他們,這可不行啊!」雍澨之地,吳、楚交戰過多次,楚軍損失的大部分兵力都還橫屍在戰場上。
子期卻堅決地說:「楚已亡國!死者地下有知,復國之後他們就可享用子孫的祭祀,又怎麼會害怕焚燒?」
隨後,楚人立刻發起了火攻,結果再次大敗吳師!
吳軍出師半年多,連番遭遇大敗,軍心大大受挫。在公壻之溪(大約是接近長江處),疲憊不堪的吳軍最後一次與楚軍接戰,卻再度潰敗!

眼看敗局已定,闔閭終於死心了,只得先行撤軍,回到吳國平叛去了。雖然夫概稱王數月,但吳人顯然更加支持闔閭。闔閭回國後,夫概根本無法對抗,不得不逃亡楚國去了。
在徹底趕跑吳軍後,楚昭王終於安全地回到了郢都,開始賞功伐罪。
在楚昭王逃亡之時,要從成臼(即臼水)渡河。這時,藍尹亹(wěi)正駕船載著妻兒老小從河上經過。楚昭王想坐他的船渡河,可藍尹亹卻無情地拒絕了。這次一回到郢都,楚昭王就想殺了他!

可他的庶兄、令尹子西卻勸說道:「囊瓦就是好記舊仇,所以才會失敗。國君何必要效仿他?」楚昭王聽了,頓時醒悟過來:「好!讓他官復原職,讓我銘記楚國以前的錯誤!」
楚國傳統,就是集權佔據上風。長期集權之下,公室往往對大臣過於嚴苛、動輒得咎。特別自楚靈王以來,楚國公室奢侈成風,卻更為嚴苛地對待屬下大臣,殺戮大臣成為常有之事,致使楚國政壇陷入了萬馬齊喑的境地。正是這種萬馬齊喑的氛圍,讓楚國一步步走向了災難的深淵。
在經歷了這場國難後,楚昭王深刻地體會到只有容忍大臣們的失誤,才能讓楚人充分發揮自身才能,更好地為自身統治服務:藍尹亹雖然在危機時刻拒載,卻警醒了國君;斗懷曾想殺死楚昭王為父報仇,但最終還是為楚復國作出了貢獻;申包胥雖然放走了伍子胥,卻是因為他才求來了秦國援軍……。沒有從不犯錯的大臣;如果大臣一犯錯就殺,那還有多少大臣甘心為楚國出力?
楚昭王能原諒藍尹亹、斗懷等人,這是他深刻意識到了過往求全責備式行政的積弊。過於求全責備,就類似於現代管理理念中的「零缺陷」——沒有任何人或物是毫無瑕疵、完美無缺;一味地強壓下屬在工作中要做到「零缺陷」,下屬要麼就作假,要麼就乾脆不作為。如此一來,楚國政壇怎能不萬馬齊喑?

只有適當地容忍下屬的工作失誤,下屬才敢於承擔責任、主動任事。楚國能成功復國,就是因為楚國公室不計前嫌,能最大限度地將楚人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最終在秦人幫助下戰勝了強大的吳軍。楚昭王原諒藍尹亹、斗懷之舉,證明楚國政壇風氣開始由嚴苛轉向寬容,使得楚大夫做事時不再畏首畏尾,可以更加主動地發揮自身才幹,由此楚國才有了重新崛起的基礎。
所以說,這次滅國之難就像一場大型外科手術,在切除積瘤後,讓楚國再度踏上了復興的征程。
然而,這場外科手術雖然切除了積瘤,卻沒能徹底斬斷病根。
楚國嚴苛執政的根源在於權力過於集中,而楚國權力集中的根源又在於「任人唯親」的宗法制:在楚武王改革了分封制後,公室權力大大集中;可這種權力集中要麼是在國君之手,要麼是集中在公子、公孫之手。權力長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就難免會誘發種種積弊。
在這次國難前後,楚昭王任命庶兄子西為令尹、庶兄子期為司馬——這足以證明楚國「任人唯親」的大格局依然沒有改變。如此一來,楚人下一次國難又會是什麼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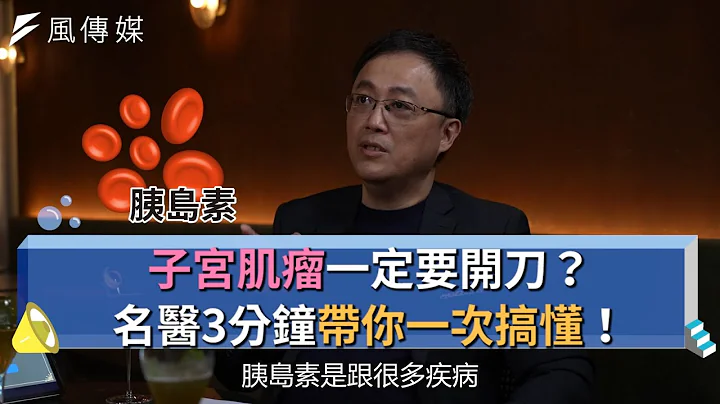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