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遼寧瀋陽岫岩縣的一戶姜姓的人家誕生了一個女娃。女娃模樣素凈,機敏好動,其父姜福慶大喜,便為其取為「姜素敏」。
姜家是岫岩縣有名的富貴人家,姜福慶老來得此一女,自然得是好生疼愛教養。
素敏尚且三歲的時候,家人就給她請來了私塾先生,日日教授琴棋書畫、詩歌禮儀,大有將其培養成名門淑女之意。

而作為姜家的掌上明珠,素敏在功課上也十分爭氣,小小年紀就能把四書五經、詩文古籍背的個滾瓜爛熟,靠著一身斐然才氣成為岫岩縣人口口讚譽的「小小女先生」。
按說按照姜家的門第和威望,這「小小女先生」長大後大抵是會嫁得個門當戶對的玉面郎君,兩人舉案齊眉,兒孫繞膝,和和美美地度過一輩子。
但這世間的一切就好像冥冥中註定好了似的,讓人不得不朝著那看似巧合實則命中注定的軌跡悄然靠近。而改變姜素敏的宿命的東西,正是讓人猜不著也摸不透的「佛緣」。

一日,在私塾上學時,姜素敏從先生那裡無意間接觸到了類似《大悲咒》、《心經》等佛教的修行心經。
或許出於孩童的好奇心,姜素敏在看見這些書籍後,一下子就被它們吸引住了。每日除了吃飯睡覺,基本上書不離手,眼不離書。
按理說,姜素敏僅才12,3歲的年紀就開始閱讀這些生澀難懂的佛經典籍未免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但在姜家父母看來,女兒自小便聰慧異於常人,會沉迷於這些書籍也不算奇怪。再者於普通人而言,這些修行心經也算是能修身養性、陶冶情操,便也由她去了。

沒了旁人的干擾,姜素敏看書看得更狠了些,沒多少日子便將這些心經背誦了下來。而正如姜家父母的預料的那樣,在接觸到這些佛教典籍後,姜素敏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年紀就擁有一顆「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
除去施粥布善,每次在街上看見潦倒的乞兒時,心善的姜素敏總會於心不忍,給予他們吃食。
事情發展到這裡,姜素敏的行為倒沒什麼異常。畢竟無論在什麼年代,熱衷學佛禮佛,從來都不是什麼壞事。
而姜素敏從佛學中學來的樂善好施,也是姜家父母樂見其成的。可接下來的一系列變故,卻大大超出了眾人的想像。

首先是隨著佛教學習的深入,姜素敏越來越愛往寺廟裡跑了。據伴隨其左右的傭人描述,每次姜素敏來到寺廟,臉上的表情總會變得特別莊嚴肅穆,彷彿她之前就來過好多次似的。
而在這撞鐘伐鼓的寺廟中,這位富家小姐什麼都不幹,單是聽主持師父誦讀經文,就能在這呆上好幾天。
更讓其家人詫異的是,自從迷戀上了禪學,每日清晨從姜素敏房間傳出的朗朗讀書聲便不再是詩詞歌,而是佛學經書。
宅外一些不明就裡的人聽了,更是紛紛驚嘆以商賈為謀生的姜家莫不是出了個小尼姑。
對於外人的眾說紛紜,姜素敏的父母也是聽在耳里,急在心裡。但作為姜素敏誦讀佛經的初代擁護者,他們也不好對姜素敏的行為多說什麼,只能旁敲側擊地幾番暗示。

父母原本想著女兒只是對禪學一時興起,等過些日子玩鬧勁過了,也就沒心思跑去那寺里禮佛了。
可沒成想,夫婦倆別的沒等到,倒是在姜素敏15歲那年等來了一句「女兒欲出家為僧」。
要知道若放在古代,15歲對女子來說,那可是及笄出嫁的年紀。而顯然,從小就接受新思想的姜素敏,雖依舊遵循著「三寸金蓮」的封建陋習,在很多事情上卻已然有了自己的主見。
她要出家的決定,自然不可能僅是一時興起,說說而已。眼看女兒真有遁入空門的心思,姜家父母便再也無法坐視不管。在將其19歲的時候,一紙婚書就把其嫁給了遼寧大學的一位講師。
要說姜素敏這未來夫婿的家境,與門庭若市的姜家也算是不分伯仲的。婆家是吉林通化市的有名的實業家,靠著一家生產傢具的工廠每年賺的是盆滿缽滿。

而作為姜素敏丈夫本人,這位大學講師也是一表人才,年紀輕輕就獲得教員的評稱。像這樣的人家,無論是才學還是財富,與姜素敏都極為相配。
事實上,男方在姜家初次與姜素敏見面時,就對其一見鍾情,願娶其為共度餘生的結髮妻子。奈何郎有情而妾無意,姜素敏對這個未來夫婿倒不是很感冒。
在婚禮前夕,為了故意刁難對方,她甚至提出了出嫁時「不著嫁衣著法衣,不戴鳳冠戴道姑髮髻」的無理要求。
當然,要說這世間被偏愛的人總是有恃無恐。對於姜素敏種種的任性舉動,這姑爺最終都是一一應允了。
前有娘家施壓,後有夫家「圍追堵截」,無奈之下,姜素敏也只好暫且放下剃髮為尼的心思,兩眼一閉,嫁為人婦。

嫁入婆家後,因婚禮上的種種怪異舉動,姜素敏並不受公婆待見,但好在她還有丈夫疼愛,其婚後生活還算是過的安逸舒適。
可是一隻家養的金絲雀,哪怕再安逸,那也是被豢養在籠子里,身心沒個自由。
於是在結婚的第二年,為了擺脫這種無形的束縛,也為了滿足自己在中醫上的志向,姜素敏就以學習針灸為由,來到了瀋陽中醫學院進修。而姜素敏在這學院里一待,就足足待了6年時間。
對於這個自幼喜靜且獨立自強的女性來說,在瀋陽中醫學院學習的6年,無疑是快樂且充實的。在這裡,她像塊孜孜不倦的海綿一樣,不斷從書本和課堂中汲取中醫針灸知識。
在這裡,抱著一顆「醫者仁心」的善心,她在渡人之前,先實現了渡己,許下了「普渡眾生」的信念。

而更讓姜素敏驚喜的是,在她學成歸來的時候,通過與丈夫生活點滴,她竟然逐漸愛上了這樁包辦婚姻的對象。畢竟哪怕是再堅硬的石頭,在常年的同床共枕後,也會焐出溫度。
何況兩人無論在學識上還是抱負上,都算是志同道合,興趣相投。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倒不如一齊做對歡喜鴛鴦。
只可惜鴛鴦短命,只需一股時代的洪流就能把他們給拆散了。1940年,因參加「反對國民政府專制」的重慶請願活動不順利,丈夫回家後便一直卧病在床。
儘管在這段時間裡,期間姜素敏日夜在其身邊貼心照料,但鬱郁不得志的丈夫最終還是恨病逝了。
丈夫去世後,原本就不討公婆喜愛的姜素敏在婆家的處境又越發艱難。加上兩人結婚的10年中,因聚少離多,兩人也沒生下個一兒半女的。
或許是因為相看兩厭,在丈夫病逝後的那個秋天,姜素敏便拿著一紙和離書,徹底與婆家斷絕了關係。

離開婆家後,姜素敏本打算投奔岫岩縣的娘家。奈何還沒等她進家門,就聽見宅里傳出陣陣長輩的指責聲。
原來是遠在通化的原婆家,在姜素敏走後,便快馬加鞭地把其和離的消息告知了姜素敏的父母。
要知道,在那個並不開明的年代,和離就意味「退貨」。對於面子比里子重要百倍的姜家父母,又怎麼忍受得了這種恥辱呢?
於是,這才有了姜素敏在門口聽見的那番指責聲。事實上,在唯一一個會無條件包容自己的人離世後,姜素敏也算是看淡了紅塵。
對於昔日親友的挖苦,她心頭雖些許苦澀,但也不至於想不開。甚至乎,孑然一身後,反而有種豁然輕鬆之感。看來我和佛祖的緣分真的到了!
抱著這樣的念頭,姜素敏調轉了回家的腳步,孤身一人從遼寧瀋陽來到山西五台山的顯通寺。

1940年,伴隨著秋風與鐘鳴,29歲的姜素敏終於了卻了年少時的心愿,從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小姐搖身一變,成為了吃齋念佛的仁義法師。
和所有僧人一樣,姜素敏在寺廟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打坐讀經,念佛講習。每日清晨聞鐘聲為起,每日夜晚叩鐘聲而睡。
不過,和普通僧人不同的是,作為苦學中醫六載的赤腳醫生,姜素敏除了按例做些闡教功課外,還經常會利用自己的針灸技術為山下的百姓們義診。
每次看診時,她總能將病人們的病理癥狀、治療手段講的頭頭是道,甚至事後還不收取一分一厘。怪不得百姓們見了她,總愛將其稱作「活菩薩」。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了。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為了揚立新中國的國威,中國人民志願軍慷慨激昂,240萬人馬帶著滿腔的仁義與勇敢,先後跨過鴨綠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戰場中。

姜素敏雖為遁入空門的女子,卻並非手無縛雞之力。作為同樣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的有志之士,她不僅有一顆肝膽報國之心,更有一雙能行醫救人的巧手。
當時,在五台山上得知抗美援朝的消息後,姜素敏便不顧自己的安危,毅然決然的加入到了志願軍的隨行軍醫中。
戰爭無情人有情。在與中國志願軍並肩作戰的三年中,姜素敏靠著自己高超的中醫針灸技術,從閻王爺手裡搶回了無數受傷戰士的性命。
儘管在這個槍林彈雨的殘酷戰場上,因裹著小腳,姜素敏行動並不算方便,甚至可以說她所遭遇的危險比旁人還要多些。
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這位愛國的仁醫對自己行醫救人的使命卻從未有過一刻的鬆懈。
都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但在姜素敏眼裡,戰士的髮膚卻比自己的重要的多。一次,因敵方的炮火過於猛烈,姜素敏左手腕活生生被子彈打出個血窟窿,血流不止。

面對錐心的疼痛,姜素敏卻沒有絲毫的抱怨和委屈,只是簡單地用紗布處理了下傷口,就又投入到搶救傷員的工作中去了。
如此大義凜然、捨生忘死的崇高氣派,又何止一個 「活菩薩」可以形容的呢?
正義之師必有天佑,1953年,6千位志願軍帶著無數青山忠骨的夙願凱旋而歸,而作為隨行軍醫的姜素敏也在班師回國的隊伍中。
回到祖國後,因當時宗教政策尚未徹底落實,姜素敏並沒有回到寺廟,而是來到了遼寧省瀋陽202軍醫院,繼續在救死扶傷的事業中發光發熱。而她這顆「小燈泡」,一亮就足足亮了三十年。
1982年,姜素敏已至72歲高齡。一般來說,像這個年紀的老太太,要是有個一兒半女的話,如今大多都是在家裡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了。
但早已煢煢孑立的姜素敏已然看破紅塵,了無牽掛了。

要說她心中唯一所求的,莫過於回到寺廟,與青燈古佛共度餘生。
不過這次,她的心之所向,卻不再是當初剃度時的五台山南山寺,而是曲徑通幽,鳥語花香的九華山通慧禪林。
1983年,在五台山塔院寺受過具足大戒後,姜素敏開始了雲遊四海的逍遙生活。
那段時期,她住過甘露寺、菩提閣這樣的名寺,也露宿過簡陋破舊的荒廟。
或許是過去的歲月和經歷造就了這位太師寵辱不驚的心態,無論是名事或是荒廟,皆未在她心中掀起半分漣漪。
直至有一日,偶然的情況下,姜素敏途徑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九華山通慧禪林。
與如今香火旺盛、修繕完好的通慧禪林不同的是,當時姜素敏眼前的通慧禪林卻是一處極為天然質樸的聖地。這裡溪水潺潺,環境清幽。

雖因年久失修破爛不堪,然而隨處可見的的參天古木、深幽曲徑卻給人一種遺世獨立的豁然之感。
而對於一生都在追求這份豁達從容的姜素敏來說,只需瞧上一眼,便有了一眼萬年的感覺。
或許是與這個古廟無形中萌發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在這兒歇了幾天腳後,姜素敏便決意用自己12萬元的積蓄好好將這個古廟修繕一番。
要知道,這12萬元可是姜素敏這幾十年來,靠著售賣草藥、行醫問診好不容易才積攢下來的,甚至裡面大部分的錢還是她當初做志願軍的隨行軍醫的津貼金。
然而,為了能這個「遲暮英雄」在禪林文化中重振雄風,姜素敏掏錢的時候卻是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
不僅如此,在正式開啟寺廟的修繕工作後,這個年至古稀的老太師甚至還拖著那雙三寸小腳在施工場地上親力親為。

建築材料的採購,工程質量的檢驗甚至工人們的伙食,修繕期間的方方面面,姜素敏都對其一一過問,唯恐裡面出了什麼岔子,影響了寺廟的修葺和復興。
而在經過兩年的忙碌操勞後,那座因位置偏僻、外觀破舊而被人遺忘多年的通慧禪林,也終於在姜素敏的努力下恢復了初建時的光景,每日來此地祈福的香客更是絡繹不絕,熙來攘往。
通慧禪林能得以「重振雄風」,按理說作為修繕工作的發起人,姜素敏應當是功不可沒的。無論是寺廟裡的主持、小僧,還算是來往的香客,都對其讚不絕口,敬佩有加。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姜素敏卻彷彿深藏功與名般,一人帶著一口用以研磨草藥的石磨盤繼續下山行醫去了。
或許有人會問,石墨盤也不算是個稀罕物,為何姜素敏一把年紀了還非要親自帶著這個兩百斤的大傢伙四處奔波呢?

而每次聽見這個問題,姜素敏總是會微笑解釋道:「東西雖不罕見,卻不一定哪裡都有得賣?要是在深山老林里看見個病人,手邊沒個磨葯的工具,這不是在耽誤了人家的性命嗎?」
的確,在行醫救人的這條道路上,姜素敏從來就不是個怕麻煩的人。只要對病人的病情有好處的東西,姜素敏從不嫌麻煩。
就好像當初在朝鮮戰場行醫救人一樣,只要能挽救戰友的性命,哪怕舍掉她的一條左手,她也義無反顧地衝上前去的。
石磨盤隨姜素敏行醫的腳步,途徑萬里,製藥無數,在紅塵人間挽救了無數病患的生命,最終在1995年5月,又與她的主人從人間回到了鐘鳴古剎的寺廟。
或許是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回到通慧禪林後,姜素敏表現地極為平靜。

除去吃飯睡覺,姜素敏每日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念誦大悲神咒。儘管那段經文她早在懵懂的少女時期就已經背的滾瓜爛熟,熟記於心了。
但是,在姜素敏認為,同樣一件事物,在人的不同階段去品味,總會從中得到不同的收穫。
被稱作修道成佛的重要口訣的大悲神咒,便是這樣「愈品愈新」的存在。而為了能從大悲神咒中領悟出不一樣的人生哲理,姜素敏甚至在戰場上做軍醫的時候,都未懈怠過這門功課。
1995年10月7日,在經歷了一周的停食辟穀後,姜素敏以十分安詳的狀態圓寂在了九華山通慧禪林內。
師太圓寂後,寺內的弟子皆悲痛泯然,甚至山下的廣受姜素敏恩澤的百姓在得知師太離開人世的消息後, 都紛紛聚在寺前為其默哀。

逝者已矣,弟子心中雖悲痛萬分,卻仍不敢忘記姜素敏生前的叮嚀。原來,在姜素敏圓寂前夕,曾有過自己或能修成肉身舍利的預兆,遂對其弟子萬般囑咐,告知他們等自己圓寂後,萬不可將她的屍身做火化處理,而是要給她坐缸。
所謂的坐缸,是佛教僧人圓寂後的一種特殊的儀式。相傳,坐缸之人,只需以打坐的姿待在一口陶缸中,靠堆至胸口處的石灰和木炭來維持身體的儀態。
而後,等缸口封閉好後,再在缸底留出一個用以點火的傳火孔。通過缸底的不斷加熱,以實現缸中屍身的不腐保存。而要想塑成這容顏不腐的「肉身菩薩」,得足足經歷三年的時間。
儘管坐缸算是佛教中人圓寂後慣用的處理屍身的手法,但因為這種手法處理難度之大,自唐朝佛教興盛以來,攏共也就只有10位僧人塑成了肉身不腐的金身,且這10人還皆是男性僧人。
至於姜素敏這種身體構造比男性更加敏感軟弱的比丘尼,卻還未有過成功的案例。

儘管對於姜素敏能否塑成金身心裡還有些發憷,對於老師太圓寂前的叮嚀,弟子們卻未敢怠慢。
眾人只待平復好心情後,便立即嚴密謹慎地對姜素敏的屍身裝入缸中,在九華山的後山坡上對其進行了坐缸儀式。
1999年1月2日下午三時,應姜素敏生前的要求,通慧禪林的僧人們一齊將裝載著姜素敏屍身的坐缸給打開了。
而在開缸的那一剎那,目睹此景的僧人們紛紛一驚。只見在這個密閉了三年的坐缸中,早已羽化的姜素敏,卻依舊端正地端坐在這個坐缸中間。
且更讓人嘖嘖稱奇的是師太的毛髮和皮膚,經過三年又兩個月的變遷,依然如生前般富有光澤,彈性十足,甚至原本黑白相間的發間竟還長出了些許烏髮。

而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師太在入缸前,原本十指相向的雙手,經由一番坐缸,竟逐漸演變成了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抬高呈捏針狀,儼然與師太生前為病人針灸的架勢如出一轍。
對於姜素敏塑成「肉身菩薩」的緣由,一些了解其生平飲食的弟子猜測,莫不是因為師太常年使用不沾油水青菜和白米粥,羽化之後,她的皮膚才會如此光澤透亮。
而專家們在仔細觀察老師太圓寂後的身體,卻發現其象徵著女性特徵的胸部和下身長合已然平整後,饒是「無神論者」的他們,也不得不驚嘆這傳說中的千年不腐的「肉身菩薩」,實則也是來自於人間。
自通慧禪林內出現了中國佛教史上首尊女性「肉身菩薩」後,來寺內瞻仰功供奉其金身的香客便比以往更加絡繹不絕。
而在一陣陣古寺鐘鳴和經文誦讀聲中,來往者的心靈也得了極大的洗滌和凈化。

在這個有些浮躁的時代,還能尋到一片如此清靜無為、和風細雨的佛教聖地用以瞻仰靜心沉思,這不正是當年姜素敏傾盡家產也要將這座古寺修繕好的原因嗎?
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富家小姐,到一個一心向佛的浮世過客。從一個捨生取義的志願軍軍醫,再到一個廣渡天下的「肉身菩薩」。姜素敏一生雖皆於佛有緣,但最後將她渡成「佛」的,卻不是佛祖本身,而是她自己。
一雙將前路踩出升雲梯的三寸小腳,一道永遠留在左手腕上的傷疤,一塊背了幾十年的石墨盤,一段念誦了千次萬次的大悲神咒。這位「活菩薩」的渡己之路雖苦難重重,荊棘遍地,所幸也算是求仁得仁,如願以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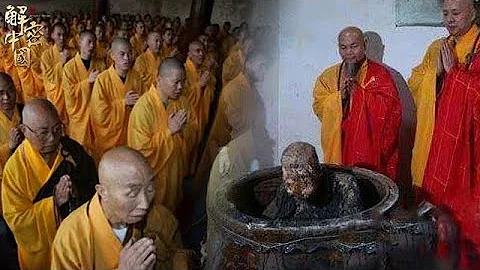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