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毛主席之於新中國的誕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打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處境,為了給中國人民創造一個新世界,毛主席將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他熱愛的祖國。
在這場改天換地的大革命中,毛主席先後失去了六位親人,是世界領袖人物中,犧牲最多,犧牲最大的領導人。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毛主席唯一活下來的兒子毛岸青,擁有了一段完整的人生。不僅過上了「平凡」的生活,更擁有美滿的家庭。那麼,他的晚年過得如何呢?又享受到了哪些待遇?

苦難童年與無盡的病痛
毛岸青是楊開慧和毛主席的次子。他1923年生於長沙的中南大學湘雅醫院,4歲時,因母親楊開慧被何鍵殺害,不得不跟著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龍到外婆家生活。
然而,弟弟毛岸龍不久夭折,國民黨的圍剿又愈演愈烈,毛岸英倆兄弟只好被送往中共地下黨在上海所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生活。
那時,兩兄弟還不知道,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們將面臨前所未有的人生挑戰。

1932年3月,由於大同幼稚園保育員管荷英在外出期間失蹤,負責管理幼稚園的特科員為保證孩子們的安全,只好解散幼稚園,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寄養到地下黨董健吾的家中。
當時董健吾的家是地下黨的聯絡點,位置還跟法國捕房相隔不遠,董健吾為了兄弟兩人的安全著想,只好求助前妻黃慧光代為照顧孩子,每月還給他們送去30元錢的生活費。

黃慧光本就是家庭婦女,除了毛家兄弟外,他自己也有四個小孩要養。起初,他們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黃慧光雖然不事生產,但警覺性卻很高。
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她就立刻帶著孩子搬家。在毛岸青的記憶中,那段時間,他們總共換過六個地方。
可後來,他們的日子就難過了。董健吾的失業直接影響了黃家的生活,黃慧光只能帶著幾個孩子做些手工靈活維持生計。偏偏,毛岸青還得了麻疹,毛岸英感染風寒。

缺吃少喝的情況下,黃慧光更是忙得焦頭爛額,心浮氣躁間便會打罵孩子。這對於少小離家的毛岸英衝擊巨大。所以,趁著黃慧光不注意,他就帶著弟弟離家出走了。
那是1935年的秋天,兩個操著湖南口音的小孩子,就在茫茫大上海當起了流浪兒。
白天,他們就靠給別人拖地板、撿破爛換口飯吃,困了,就找個馬路牙子睡覺。後來,毛岸英發現上海外白渡橋那裡經常有黃包車拉不上去,幫忙推車,對方就會給幾個小錢,他又帶著岸青干起了這個活計。
可不幸的是,流浪期間,毛岸青遭遇了巡警的追打,對方專門往孩子的頭部招呼。這番毆打,讓年幼的毛岸青被打出了腦震蕩,其後遺症就是讓他患上了折磨終身的精神分裂症。

與此同時,留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人員得知毛主席的兒子出走後,急得團團轉。他們發動了所有隱藏在上海的地下黨,奔走了大半年的時間,這才在一間破廟裡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
1936年4月,受毛主席委託,在張學良將軍的幫助下,毛岸英和毛岸青跟隨東北義勇軍的李杜將軍前往法國馬賽,在那裡,他被蘇聯駐法國大使館接收,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蘇生活。

婚姻與晚年
抵達莫斯科後,毛岸青跟著哥哥住進了國際第二兒童院,還擁有了個俄國名字亞歷山大。
由於在上海時沒能進入學校讀書,毛岸青的中文讀寫能力較差,給爸爸毛主席寫信用的都是俄文。搞得毛主席每次樂呵呵地讀兒子的家書,旁邊還要跟著師哲,這麼個俄文翻譯。
衛國戰爭期間,性格忠烈的毛岸英主動申請去前線參戰,一直跟隨哥哥的毛岸青便也跟上了戰場,幹些挖戰壕、送傷員的後勤工作。

再回故土時,已是1947年,毛岸青已經從當年的半大小子長成了24歲的青年。儘管已經許久沒見過爸爸的面,但是對於父親的工作,毛岸青給予全力支持。在毛主席身邊沒待多久,毛岸青就跟著其他工作人員跑到氣候寒冷的黑龍江齊齊哈爾搞土改工作去了。
奈何,精神疾病始終不肯放過這個有志向的年輕人。1949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馬列著作編譯室做俄文翻譯的毛岸青經常給毛主席寫信。詳細地告訴父親,自己的腦子裡始終有一個「小傢伙」在跟他搗亂。
身為人父,毛主席心疼兒子、愧對兒子、同樣也深愛著兒子。在聽取其他醫護的意見後,他只好忍痛,再次將毛岸青送到蘇聯去治療。

然而,苦難並沒有離開,反而對毛岸青百般刁難。當時,在蘇聯使用的是封閉治療。因為過度使用激素的緣故,毛岸青渾身浮腫,病情不減反重。再加上當時中蘇關係,毛主席便安排毛岸青到大連去療養。
當時在中蘇邊境迎接毛岸青的是時任旅大市(大連市舊稱)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的張世保。據他回憶,第一次見到毛岸青時他心裡很不是滋味。

30多歲的毛岸青神情憔悴,沉默寡言,整天都是病懨懨的樣子,眼神憂鬱得很難跟風華正茂的中年人聯繫到一起。因此,張世保決心要好好照顧他,為毛岸青提供最好的服務。
脫離封閉的空間,大連的海風和沙灘讓毛岸青的心胸逐漸開闊了起來,話也越來越多。由於少年時期在蘇聯的成長經歷,毛岸青的很多生活習慣跟歐洲人相似,沒事就跟張世保打克朗棋,看俄國文學書。張世保還特意給他找了一本俄文版《西遊記》,常常把毛岸青看得捧腹大笑。

毛岸青病情向好後,旅大市的很多人開始琢磨想給毛岸青介紹個女朋友談談。於是,幾個熱心腸的同志就給他找了一個女護士,讓其在照顧毛岸青的時候,培養感情。
豈料,36歲的毛岸青從來沒對哪個姑娘動過心,更沒有戀愛經驗。女護士照顧他兩個多月,他一點感覺都沒有。還是按照張世保給他安排的作息,出門散步,打克朗棋,閑暇看書。有時候,看書太專註忘了吃藥,女護士還要再三催促。
大家一看這個情況,也就知道兩人沒戲,便不好再給他介紹女孩了。
不過,緣分這個東西,有時候就很玄妙。1960年1月,毛主席的親家母張文秋帶著自己的二女兒邵華也來到旅大療養。張文秋此行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同意下,來給邵華和毛岸青「相親」來的。
邵華是毛岸英妻子劉思齊的妹妹,從小就經常跟著姐姐、姐夫到毛主席家玩耍。長大後,她因酷愛文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有一天,她在跟毛主席談論《簡·愛》時,毛主席就想起了在旅大養病的毛岸青,說他三十好幾的人,找對象談戀愛不應該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兒子,應該介紹自己是中宣部的翻譯。
毛主席還說,要毛岸青把擇偶標準降低些,找工人或者農民。眼光高了,人家能力強,會被人看不起,生活自然不如意。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邵華雖沒見過毛岸青,但是卻對他產生了好奇心。正好,張文秋有意跟主席家再結連理,他們便安排放寒假的邵華到大連來探望毛岸青。

誰也沒想到,兩人一見面,毛岸青就對邵華一見鍾情。這次相見雖然短暫,但是兩人卻經常往來書信,以信寄情。
此後,在交往一段時間後,毛岸青與邵華在196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在旅大賓館舉行了婚禮。
婚後,他們在旅大生活了一年時間。邵華酷愛攝影,經常拉著毛岸青去海邊、公園拍照。毛岸青則喜靜,常常捧著俄文書看個不停,間或翻譯的俄文材料也總會被拿去刊登。
這麼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相處起來,竟然非常和睦。學習好的邵華還跟著學會了不少俄語,常常跟毛岸青用俄語交流。

用邵華自己的話說,毛岸青跟當時很多的周邊人不同,特別浪漫,還能歌善舞。不僅教會了她跳華爾茲,還喜歡一件大衣兩個人披,挽著她在街上散步。這在當時的男性中,是很少有的浪漫舉動,讓邵華倍感甜蜜。
就在這種幸福中,他們迎來了自己的兒子。當時,消息傳回中南海,毛主席笑得合不攏嘴,親自給孩子取了名字。
此後,毛岸青和邵華一直居住在北京市郊,除了日常工作,就跟很多父母一樣,忙著教育孩子。

毛主席過世後,毛岸青按照父親的意願繼續當一個「平凡」人,不願接受特殊的待遇,只有在醫療上破格享受到了副總理級別的照顧。
除了繼續翻譯俄文著作外,他經常帶著妻子和兒子重走長征路,搜集革命時期的點點滴滴。並且,與邵華一起整理大型叢書《中國出了個毛主席》的文獻資料。
唯一特別的是,每年的毛主席誕辰,他都會帶著妻子兒女出現在毛主席紀念堂,回憶他與毛主席那短暫,難忘的父子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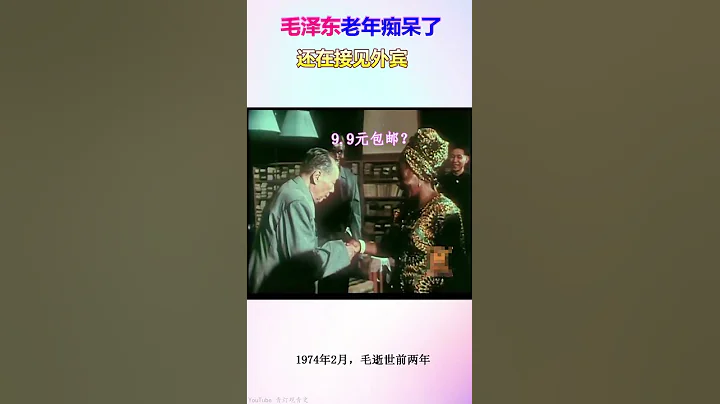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