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 一個國家的崛起常常伴隨著戰爭。
發展軍事力量, 為實現國家崛起提供暴力支撐, 是每個國家的必然選擇, 但英國發展軍事力量有其策略和特色。

其一, 有重點地發展軍事力量。
西方軍事理論家富勒說:「在一個商業的時代中, 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利用有利的地緣條件全力發展海軍, 是幾個世紀英國軍事發展的重點。
從16世紀起, 英國政治家就堅信:在優勢海軍的保護下, 英國既可防範歐陸國家的入侵, 又能保護戰略通道並安全地從事殖民擴張。

英國在亨利八世 (1491~1547) 時就創立了正規海軍, 設立海軍事務委員會, 組建航海技術學校, 其「大哈利」號戰艦的設計和建造走在了所有國家前面。
到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前夕, 查理士國王建立了一筆「軍艦準備金」, 開始建立近代職業海軍。
到1688年「光榮革命」時其艦隻的噸位已僅次於法國, 1790年躍升首位 (48.59萬噸) , 法國退居次席 (31.43萬噸) 。

到1815年, 英國海軍總噸位達到了60.93萬噸, 超過其後的法、俄、西3國的總和。其後英國海軍一直佔據絕對優勢。
憑著海軍的保護, 英國長時間免受歐洲大陸戰火的殃及;在外交上也保持著充分的行動自由———進可面向海洋擴張、面向歐洲大陸操縱均勢, 退可固守家園。
1 8 8 0~1914年各大國的戰艦噸位

1 8 8 0~1914年大國的陸海軍人數

其二, 以質量取勝而非以數量取勝。從軍隊數量看, 即使在其霸業的頂峰時, 英軍也沒有名列過世界前茅。
英國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一直是以質量取勝, 主要方法有:一是不斷革新軍事技術和裝備。
亨利八世建造了快速靈活的新型戰船, 不僅廣泛採用側舷炮, 而且充分利用新發明的4輪炮架給戰船裝上重型火炮, 使英軍的海軍戰術率先進入火炮交戰時代。
利用火力優勢和機動靈活的戰術, 艦艇數量處於劣勢的英國艦隊, 打敗了仍然採用舊戰術 (迫近並強行登上敵艦進行肉搏) 的西班牙「無敵艦隊」。

資產階級革命之後, 英國率先把工業革命的成果運用于海軍。
19世紀30年代以後, 英國帶頭完成從帆船艦隊向蒸汽鐵甲艦隊的過渡, 以蒸汽機和螺旋槳為標誌的新動力系統代替了傳統的風帆動力, 以爆破彈和線膛炮為標誌的新火炮系統應用于海軍艦船, 鋼鐵替代木材成為新的造船材料。
二是革新海軍戰術和制度。
1650年, 英國依艦船的噸位和裝載舷炮的數量, 採用了6類分級法給大小不同的各種艦船劃分等級, 提高了協同作戰能力。

在「七年戰爭」中, 英國海軍大膽地摒棄了戰列線戰術, 開始嘗試機動戰術。
拿破崙戰爭期間, 英國艦隊利用機動戰術在特拉法加戰勝了海上最大的對手———法、西聯合艦隊。
三是創新軍事理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 英國人科洛姆和科貝特先後發表了《海上戰爭及基本原則與經驗》和《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 強調奪取制海權的作用。
他們的思想對馬漢的制海權理論產生重大影響。

不過, 英國的軍事創新有其顯著特點:一是少說多做或只做不說;二是不求卓越和一流, 但求持之以恆、推廣應用和納入法制體系。
如何削弱敵手實際上是一個對外戰略問題。
實現國家的崛起, 不僅要不斷壯大自身, 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削弱競爭對手。
務實而靈活的對外戰略, 尤其是妙用三角關係和制衡之術, 是抑制和削弱對手的最好方法。
三角關係指的是敵、我、友三者之間互動關係。

制衡之術指的是利用各種方法和手段, 維持有利於己的國家之間勢力均衡的力量結構。
英國是近代運用「均勢戰略」最成功的國家。
在其崛起和稱霸階段, 英國或結盟、或「孤立」、或干涉、或戰爭, 用盡各種手段, 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 目的是建立並維持一個勢均力敵、互相牽制的歐洲大陸, 既確保了自身的安全, 又為自己全力經略海洋、爭奪殖民地創造了條件, 始終把握著戰略主動權。
其主要策略手段有:
(一) 善於利用別國或國家集團力量
藉助別國力量來對付自己的主要對手, 彌補其國家小、人口少的硬體條件之不足, 是英國崛起的重要秘訣。
英國根據實際情況決定結盟或「孤立」, 既最大限度發揮聯盟的正面作用, 又防止被其拖累。

19世紀以前綜合國力還不夠強大時, 英國主要藉助外力來對付自己的主要對手, 因此廣施結盟戰略。
在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 英國與荷蘭、勃蘭登堡和薩瓦結盟, 與西班牙和法國進行殊死搏鬥, 最終挫敗了西、法聯合稱霸的企圖。
由於獲利甚多, 英國的沃爾波爾政府實行了近20年的孤立主義政策。
到18世紀50年代中期法國勢力膨脹, 英國又聯合普魯士, 通過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 削弱法國和奧地利。
18世紀末19世紀初,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再次打破歐洲均勢, 英國與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等組織了反法同盟, 幾乎聯合了整個歐洲, 經過20餘年的武裝較量, 終於打敗法國, 建立起英國多年所追逐的歐洲五極均勢體系———法國雖然戰敗, 但未遭到過度削弱;俄國力量雖然增強, 但遭到法國和奧地利的遏制;歐洲大陸存在著俄國、普魯士與法國、奧地利的對抗, 這種二對二的陣營, 對於英國操縱歐洲大陸均勢和稱霸海上最為有利。

霸主地位確立後, 英國的首要考慮是不為盟國拖累, 保持行動自由。
當出現某一強國或國家集團稱霸歐洲大陸時, 英國通常採用扶弱抑強的手段來恢復歐陸均勢, 如聯合法國和奧斯曼帝國, 通過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 打敗了因鎮壓匈牙利革命而暫時主宰歐洲大陸的沙皇俄國。
而大部分時間裡歐陸相對穩定時, 英國便以「光榮孤立」而自豪, 並於1870年11月、1879年10月、1891年5月3次拒絕了德、意的加盟要求。
英國史學家指出, 英國19世紀的對外政策指導是「避免與其他歐洲國家發生太密切的關係, 並集中力量對殖民地的侵略。」

(二) 不斷變換盟友, 保持行動自由
19世紀英國著名外交家帕麥斯頓說過:「英國沒有永恆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不變的利益。」
英國總是根據大國力量天平的擺動, 充分利用其它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 時而把砝碼加到這一邊, 時而又加到另一邊, 使它們始終處於相互敵對、相互牽制的均勢狀態。
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 英國曾與法國聯合起來, 打敗了西班牙和荷蘭。
到18世紀, 英國轉而聯合荷蘭等國家, 對抗法國;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站到奧地利一邊, 英國反對普魯士和法國;「七年戰爭」發生時, 英國又轉而與普魯士一起攻打奧地利和法國。
19世紀中期, 英國又聯合法國和奧斯曼帝國, 通過克里米亞戰爭打敗了勢力逐漸壯大的俄國。
到了20世紀初的全球化時代, 在自身走向衰落的情況下, 英國的戰略視野仍然廣闊———它與長期的對手美國和解, 解決了西半球的問題;通過與日本建立同盟, 使其東亞利益得到了保障;在歐洲又與昔日敵人法、俄結盟, 再次扭轉了江河日下的戰略頹勢, 並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敗了主要競爭對手德國。

(三) 善於化被動為主動
大國的崛起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戰略家必須有逆境中化被動為主動的能力和智慧。
英國在崛起之初曾經主要依靠武力, 在北美、印度等地佔領了大片土地。
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獨立, 宣告英國從伊麗莎白一世起, 通過兩個世紀時間的努力建立起來的第一帝國的終結。
英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從內部看, 最早的殖民地———北美殖民地丟失, 其他殖民地也被歐洲列強覬覦, 英國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帝國;從外部看, 老對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都加入了反英戰爭, 英國多面受敵。
然而, 英國迅速調整政策:經濟方面放棄重商主義, 轉向自由主義;海外殖民的重點不是拓展新的殖民地, 而是佔領那些確保貿易通暢的基地、海島, 以及對於工業化非常重要的原料產地與銷售市場;對外政策則利用1789年「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動蕩, 組織「反法聯盟」, 再次打敗法國, 建立起第二帝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

(四) 適度、巧妙使用武力
英國適度、巧妙使用武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 主要在海上使用武力, 在歐洲大陸使用武力十分謹慎。
集中精力對付主要對手, 避免多線作戰, 是英國堅持的主要原則。
近代英國的戰略目標很明確, 很具體, 也很持久:對歐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 只求建立並維持均勢, 以便於自己在海上和殖民地建立並維護霸權。
這就是英國的兩大核心戰略――「大陸戰略」和「海上戰略」。
其中, 「大陸戰略」是為「海上戰略」服務的。

給盟國以經濟或軍事援助, 讓其充當打手, 牽制歐洲大陸的強國和霸主, 自己則全力從事海上擴張, 打擊企圖稱霸海洋的國家, 是英國的慣常做法。
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的政策從來就在於在歐洲尋找肯用自己的身軀維護英國利益的傻瓜。」「法國大革命」爆發後, 英國組織「反法同盟」, 其主要目標是打敗法國艦隊。
1805年, 英國艦隊在特拉法加與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進行了決戰, 戰鬥進行得十分艱難, 英軍統帥納爾遜也陣亡了, 但是優勢的海軍使英國最終取勝。
在歐洲大陸, 英國向參加「反法同盟」的國家提供了6500萬英鎊的經濟援助, 讓其牽製法國。直到特拉法加海戰取勝後, 英軍才真正投入歐洲大陸的作戰中。

另一方面, 在海上也不濫用武力, 而是有重點、有選擇。
尤其是崛起後期, 英國海上運用武力的重點不是佔領新的殖民地, 而是確保海外貿易安全。
為了確保戰略資源的獲取和戰略通道的安全, 不求佔據的地方多, 而求佔據地方位置的重要。
英國主要佔領那些處於交通要道的基地、海島, 以及重要的原料產地與銷售市場。
如好望角、馬爾他島、錫蘭 (今斯里蘭卡) 和西印度群島、印度等。
儘管這些地方面積不大, 但是對於維持英國的工業和貿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通過這種方法, 英國的國力迅速增強, 很快就成為海上霸主和世界霸主。

近代英國崛起的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 大國崛起是國家間戰略博弈的結果, 敢於擔當、具有大戰略思維的領導人 (或領導核心) , 對一個國家的崛起具有掌舵的關鍵性作用;其二, 國家崛起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等諸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 必須剛柔相濟, 硬實力與軟實力相結合, 全方位籌劃;其三, 大國崛起的真諦在於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的相對平衡, 這既體現在能夠正確評估自己的實力, 定下適當的戰略目標和正確的崛起道路, 同時要求具備戰略定力, 保持大政方針和戰略決策的一致性和延續性, 沿著既定方向和道路不斷前進。
其四, 在崛起過程中要善於利用結盟、孤立、戰爭以及扶弱抑強等手段, 化解外交困境, 最大限度地削弱敵手, 不斷壯大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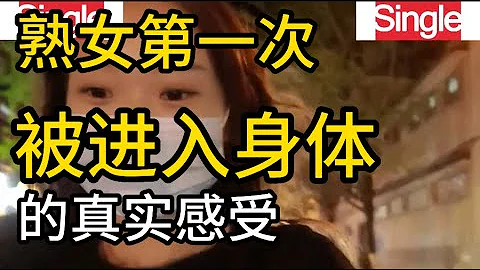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