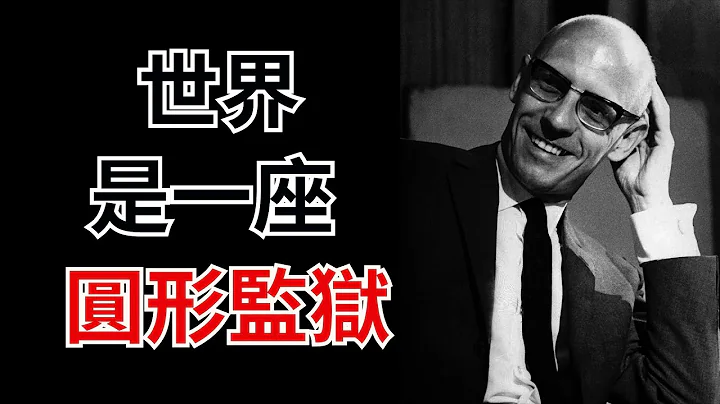了不起的概念有时候因为过于正确,会散发出一丝徒劳感,好像用不用它都问题不大。要么你死命把它用到透支,要么,就只当它是手边能随时助兴的小摆饰。比方说,“影响的焦虑”,道理自然是有的,但似乎并不值得为此消耗那么些纸张。读书时不慎沉醉其中,跟着比读者更兴奋百倍的布鲁姆在正典间吆五喝六,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剩这么一条信念还足够坚实:有些写作者是很像的,但他们也很不一样。
写东西的人,在书架上发现了跟自己脾气相投的天才,既忍不住学他,又怕太像他,这是肯定的,但照布鲁姆的构想,你只能“误读”,只能靠把范本想歪了才能写出自己,这种恶性的冲动能看作创造力的源泉吗?布鲁姆教授深信不疑,在他眼里,文学史就好比一张家谱,能用教鞭指着,一路点出每对父子间的吵架内容。
但如果都是你很在意的人自己说破此类传承关系,还是很难忘的。去年马丁·艾米斯过世的时候,杰夫·戴尔说,现在未满四十岁的人难以想象,八九十年代艾米斯奴役整个英国文坛时,他们那代作家的心悦诚服。还说,或许应该加上,那代“男”作家。其实不一定。扎迪·史密斯就写过,大学里《白牙》还没出版的时候,她一直忙着抄袭艾米斯。我向来喜欢她径直用了plagiarise这个词,潇洒认可,创造通常从模仿开始,但如果有足够才华对得起模仿对象,那它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永远不会只是剽窃。
这一回,大概是十几年来第一次重读《白牙》,快感层次丰富,首先是那股新鲜感居然完全没有折旧,喜出望外,但它似乎又给我一种念旧怀古般的感慨。当年太习惯于为这类文字心花怒放,就觉得理所当然,觉得所有人都跟扎迪有一样的想法,都想把小说写成这样。

马丁·艾米斯
艾米斯1984年的《金钱》,主人公一个醉胖子,舟车劳顿到纽约,耳鸣、牙疼、磕了脑袋,住进酒店。“refreshed by a blackout”,怎么翻呢,“被断片儿神清气爽了一下”?他走到街头,听到粗劣的警报声,两轮、滑板、卡丁车、弹簧高跷、风帆冲浪板,携主人啸叫,汽车、的士被喇叭的力量推搡,横冲直撞。“我感受着空气中所有的争斗、民主,和斜体字。”……all the italics in the air……
谁不想写这种把译者一掌拍倒在马路牙子上的句子?我那时候以为,任何作家在年轻时能被艾米斯强烈甚至暴力地影响,那才真叫“老天爷赏饭”。扎迪·史密斯所谓的“抄袭”,抄的是一种节奏,一种跟字词的亲近,一种跟语言同一战线的心里有底之感;她懂得,小说家全新认知世界的责任,跟取悦读者是同一件事;就好像她自己都急切想要看看,世界本身的荒唐和有趣会怎么化成下一个句子。我就记得,那时候为了写论文一句一句细嚼《金钱》和《伦敦场地》,艾米斯对英文的所作所为——就像他读到他爹金斯利给继母写的情书,如何描绘那种一见钟情,是“那种让天空突然绚烂的电闪雷鸣”。他好像在你意识上加了一个很强大的插件,或者说,你原先都不知道自己的意识里有这么一块疆域,现在火树银花。很多人夸艾米斯的文字electric,带着电的,科学的事情我少插嘴,但生物学上,他是庆贺生命的,他让你对人类的创造力充满信心。

《金钱》

《伦敦场地》
艾米斯的这种效应,对于英文读者,尤其是英伦三岛的年轻写作者,似乎在不同年代不停被复制。艾米斯过世前后,出来两家专门讲他的新播客,来宾络绎不绝地动情回忆,在生命的重要节点,读到艾米斯,发现这事儿还能这么干,如饮醍醐。他们每个人对艾米斯感激涕零的地方不一样,但核心相似:语言的可能性催生创造的愉悦,感染力巨大,引发幻觉,让你也想写东西。有人说他那些年不管写什么都先读五十页《伦敦场地》,有人说他认识好几位同行,都把《与陈词滥调一战》带在身边——我想象全世界成千上万写作者,把一卷艾米斯当成应急装备,像哮喘病人口袋里的喷雾罐子,能立马缓解呼吸不畅。

《与陈词滥调一战》
但那些上节目的人,好些也都抱怨艾米斯的各种问题,我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他们都很怕听众没有听明白,他们后来已经摆脱了艾米斯的影响,那种对文字和写作本身的迷恋似乎只属于一个正经写作者的学徒期。我发现自己经常会暂停播客,跟来宾吵架,开迷你讲座,暗暗觉得对艾米斯的冷淡跟他们在文学上的驽钝成正比。比如,有人说他曾经深爱艾米斯的评论,但总觉得那些幅度尺度很大的断言莫名其妙。艾米斯有一个“三字短句”,经常挂在嘴边,叫“文风即道德”,style is morality,他们高喊,这啥意思啊,文风怎么能覆盖道德呢?当然,他们并不真的提问,讥诮的语气是他们的答案:只有艾米斯这样完全活在自己趣味里的自大狂,才会为发出这种空泛的口号而自矜自喜。而我的困惑在于,一个以文字谋生的人,居然能完全避开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平时到底能看懂多少书?文风,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不是装饰,不关乎技巧,它是你感受到的宇宙的质感(这个宇宙,只有你能看见,艺术家提供的愉悦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那个宇宙)。
而那个“道德”,也不是那种能颁布行为规范的道德,它指的是作家用何种姿态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宇宙中,用什么东西给自己导航。当然,有人能在腐坏的想法周围编织优美的文字,但艾米斯只是相信——这不该是每个读者的信念吗?——我们能辨别出那种不匹配,如何写比写什么更会出卖作者。
前一段虽然读艾米斯读得高兴,可要我再想新言语夸他怎么写得好,想想就累坏了;把我从拖延症里一把推出去的,是扎迪·史密斯宣传新书,跟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亚当·瑟尔威尔(adam thirlwell)对谈。扎迪说了这么一段(她跟艾米斯彼此热爱已经二十多年了):
有时候见到马丁,很难跟他解释为什么我最近读到的一本当代小说特别好。要是一个句子没有那种美学上的密度,对他来说就是读不通的。他就无法理解那是个什么东西。很多类型的写作就被他直接忽略了。我爱马丁,但我真的不想变成那样。
我们要干的活儿,其中一部分就是永远要读新东西。不同类型的句子,有的时候是粗野(brutal)的句子。它们粗野的时候是有原因的,它们想对你引发某种效果,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文风,style,从来都不是写漂亮话,它指的是你要透彻地敲打一个句子,直到它贴合这个句子里要传递的意味和情绪。扎迪难道觉得《金钱》和《白牙》里没有粗野的句子吗?索尔·贝娄不写粗野的句子吗?(你看,布鲁姆确实好用,只要你足够固执,随处都是“弑父”和“误读”。)艾米斯反对的是坏句子、懒句子,如果扎迪想说的是,坏句子或者无聊的句子放在那里也自有它的道理(她很喜欢克瑙斯高),我感觉艾米斯的意见会是这样:好句子能比粗野的句子更好地唤起粗野,有趣的句子能比无聊的句子更好地刻画无聊……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与陈词滥调一战,就是他不相信有任何东西普遍到你只能用枯燥的写法才能呈现。庸常永远要求它那份应得的美。陈词滥调是一个写作者偷懒,怠工,是他在某种不真切的认知面前躺平,说“算了,就这样吧”,这的确是个道德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读到艾米斯的文学评论像发现了宝贝,发现了让自己爱岗敬业的意义。他明白,文字质感、阅读体验、写作方式,这三样东西不分彼此,搞清楚了其中一个,也就搞清楚了你要评论的是怎样的写作者。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西方经典”,读荷马,读但丁,读塞万提斯。我看书困到昏厥是常有的事,但《堂吉诃德》那两三周尤为频繁,那部书是我在书桌上趴睡间隙,见缝插针读完的(昏厥之后那些短暂的神清气爽)。后来在学院图书室发现了《与陈词滥调一战》,艾米斯写他读新版的《堂吉诃德》(其他的大评论家读“正典”从来都是第四第五遍“重读”,艾米斯不是):
《堂吉诃德》显然是一部坚不可摧的杰作,但它也有一个颇为难以承受的缺憾——就是它完全读不下去。这个书评人是知道的,因为他刚刚读完。这部小说有张牙舞爪的美、亲切,和高妙的喜剧;但它也很多篇幅(接近全书的百分之七十五)无聊到惨绝人寰。
然后他借摘抄的“陈词滥调”复制了一下阅读体验,情节推进就是堂吉诃德反复挨揍,而且挨的揍每回都一样。艾米斯有一句他自己也很满意的话:“这部小说没有‘后来’,只有‘还有’……”
我觉得艾米斯文学评论里最动人的部分,就是类似这种几乎是官能上、肺腑间对文学的回应。他会取阅读体验中很真切的一个切片,不止把它写过头,有时简直写到光怪陆离,但你被他逗笑的时候,就不小心成了他的同伙,默许了他在那个过剩之中想要传递的一些文学标准。对艾米斯的狂妄和浮夸有天然反感的读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一旦这种“过剩”是好笑的,它就必定会携带一定剂量的反讽。比如,说《堂吉诃德》“没法读”,言下之意当然是:我何尝不知这部小说意义重大,四百年来有无数人为之神魂颠倒,要是我在大学研究了每个文学传统,能舒服住进所有时代和地域的文学场面,精通所有语言,那我一定能从《堂吉诃德》中获得更多乐趣,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读者、更好的作家,或者,塞万提斯无趣到灭绝人性的比例很可能到不了百分之七十五。但没有办法,我被锁在我过往的人生、教育、阅读和另外所有局限之中,包括吾生也有涯和阅读费工夫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文学事上摆出不偏不倚的百科全书气度,其实是反文学的。
他的小说,原理也一样。从他二十四岁的出道小说开始,艾米斯的主题基本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头脑及其周边:男性的自负和好色、对暴力的想象、对死亡的恐惧、中年危机、作家间的妒忌和钦服;而最为重大的,是一个作家如何用直觉回应他的时代,他写核威胁,写生态灾害,写拜金,写“9/11”,写宗教,写养老,当然也仰赖异于常人的勤学好思,但从来不脱离某种私人印象、身体感受。
不管是他的重要小说还是次要杂文,就算不是每次都把作家当成主角、叙事者,也一定饱含对写作这项志业或者类似过程的关心。有人说他主题太有限了,这就像说亨利·詹姆斯和艾丽丝·门罗的主题太有限了,肯定是瞎扯,但我更排斥的是那些话底下那层不言而喻,就是你写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在关心这些事情,居然还没想明白吗?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拼老命打磨句子,想要取悦读者,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好像这些事情并没有艾米斯想象的这么难,这么值得乐此不疲。多年前,有两个我很喜欢的读者,不喜欢艾米斯,说他是个“想当托尔斯泰的狄更斯”,我倒觉得很恰当。首先,对一个在英国文坛当了二十年正儿八经狄更斯的人表示失望,这就很不寻常,但所谓的托尔斯泰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即便在他最好的小说里,比如《伦敦场地》《讯息》里面,也有很多对宇宙动向、人类进程一些票友式的思考,在我看来,确实只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但伟大的写作是可以容纳这些困惑、疑问和不懂的。
中后期艾米斯有一大块是他对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执念,很多评论者想把它们划到一边,想说,它们就算有些意思,也只是作为一个大作家的小怪癖能引发好奇。但对艾米斯来说,自己心智中有个最为黑暗的结,朝它伸手,用写作去解开它,是作家的职责。暴力、权势,幽默感和自由的完全缺失,我得去弄明白;但在这个方向上,他又是可以接受失败的:人类有时候就会没有来由地残忍;我不理解纳粹;我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我难以想象这个俊美、虔诚的特朗普支持者看着自己的领袖居然没有一丝尴尬。
2002年,他出了一本书,《恐怖科巴:笑声与两千万》。副标题的那个“笑声”引来很多疑惑;另外,书里满是艾米斯研习史料的现学现卖,又经常把私人的伤痛穿插其间(主要是他妹妹的死),也让一些人很不舒服。最贴题的“笑声”,是他跟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起参加活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希钦斯称呼观众为“同志”,底下发出哄笑——“这是一种宠溺的笑声,是所有人还对那个完美社会的古老构想保留着一丝温存;这也是一种遗忘的笑声”。他无法理解这种残忍,也无法理解这种忽略和遗忘的轻佻。读者都带着自我的生平读书,对我来说,艾米斯在这本书里那种不知该作何想的骇然,不管在音准还是音色上都是恰如其分的。甚至,他对某种主义作“文风”上的批判也因为刁钻而正中靶心。他当时有个好朋友,詹姆斯·芬顿,在才华的样式上很像一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奥登,也是个托派。艾米斯写:“一个把文学当作国家仆役的系统,我不明白他作为一个诗人要怎样跟这么一个系统同心协力,我还以为他一定憎恶那些如钢似铁的陈词滥调,那些套话和委婉说法,那些似乎要昭示未来和节省时间的简称和缩写。”
艾米斯在2014年又写了《利益之畿》,可以看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关于集中营的高级公务员如何在营墙的另一侧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又是狄更斯想当普里莫·莱维了。当然会有人说他没有资格写大屠杀,也没有这个心性去体会纳粹军官的日常;而对于艾米斯来说,让想象力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但值得褒奖,简直是一道必须全力应对的必答题。艾米斯离世的第二天,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戛纳展映,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六分钟。在大众媒介,近年来还有哪部作品更刺骨地唤起了纳粹的丧心病狂?而它的力量就取自艾米斯的那份对不可理喻的探究欲。
艾米斯说,大众为了省心,很乐意用一个词概括某位作家。对于他的朋友希钦斯,那个词是“叛逆者”;而他自己,分配到的词是“衰落”。伦敦三部曲(《金钱》《伦敦场地》《讯息》)之后,他没有再写出工力悉敌的小说。尤其《黄狗》和《莱昂奈尔·阿斯博》甚为难笑,让我也很不好意思喊出“没写好的艾米斯也比其他人好的时候更好”这样的预制应答。格雷厄姆·格林曾当面告诉艾米斯,信仰是要靠力道的,岁数大了会体力不支;艾米斯觉得这句话极富洞见。好笑也是种能量,相信自己只需负责有趣,世间真相会自己依附上来,多少是种年轻气盛。力气最大的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年之后更加难以写透,发现自己毕不了业了,多少让人灰心。但是艾米斯并没有让步,他依然在写那些纠缠他的东西。最后一本书,《内幕》,带虚构元素的回忆录,写拉金、贝娄、希钦斯离他而去,里面穿插着很多“写作课”板块,说你一句话里,词尾不小心押韵是不可以的,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本来的书名是invitation to an execution,一定要改成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长的段落和短的段落要穿插着来,相邻两段不能用同一个单词开头(比如我这两段都用“艾米斯”开头,是大忌)……我都读得有些倦了,他依然把这当成是全世界最引人入胜的话题。
最近王安忆老师接受法国人勋章时说,语言不发达,心思也必然简单;有了词汇量,才能发现情感,甚至生造情感。这种王尔德式的人生模仿艺术,从唯美主义一路直通艾米斯。“没有道德的书,没有不道德的书;书要么写得好,要么写得糟糕,仅此而已”,既可以放在《道连·格雷》的开头,也可以出自艾米斯的任何一个访谈。艾米斯在牛津读英语专业,拿到的是所谓“恭喜式头等学位”,据说规矩是答辩的时候叫进去,考官不问问题,只拍手叫好。他毕业就去了几家大报当文学版面的编辑,已经开始朝“陈词滥调”宣战,一仗打了半个世纪,态度决绝,他说不能留的,不只是笔头的陈词滥调,还有头脑的陈词滥调和心里的陈词滥调。我笔记本里一直有这么一个题目,把艾米斯称作学徒,是我向来觉得,对一些我在书店门口展示台上拿起又很快放下的新小说,还有很多急于摆脱艾米斯影响的人,是很好的提醒,可能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