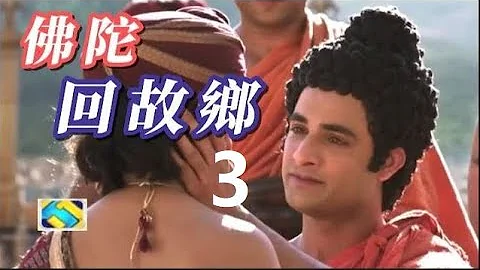闲话少叙,就说说我在实践的不同阶段对“忍辱”的理解吧。
起初,我是强迫自己认同“忍辱”的,必定吃亏是福,忍辱的过程就是消业的过程,忍辱也是一种慈悲;这些句子成了我的座右铭。
遇到别人的苛责和冒犯时要尽量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那段时期的我,为了修好“忍辱”,总是自己给自己挑错,有时虽然心里并不认同自己有错,那也要强行找出错误扣在自己头上,否则无法安慰自己那颗受伤的心。

很多时候心里是憋屈和压抑的,不明白如果错不在我,我为什么要原谅对方?忍让对方?这样长此以往,对方真的会认识到他的错误还是会觉得我软弱无能呢?如果他觉得我很懦弱而愈发得寸进尺,那么我的忍让不就是一种纵容和罪过吗?
按照佛教的因果观(当然,因果观并非如我举例这般简单直接,它是错综复杂的,也非我能解释的)他欺负我是因为我前世曾经欺负过他,那如果这个人今生是个混账,他嚣张跋扈、经常性地欺辱他人,那么所有被他欺负的人都是欠他的吗?因此才要忍让的吗?
他前世既然是一个被众人欺负的人,今生成为一个混蛋就是必然性,只是为了要报仇?如果这样,他的业障也够深重的啊,也是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观点。那么来世的我也会如今世的他一样?每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不寒而栗,也无法照此再推下去了。

如果我走在街上遇到一个流氓欺负我,我是应该忍辱呢还是应该还击呢?如果路见不平时我是该一声怒吼呢还是袖手旁观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搅得我心烦意乱,我懒得往深处去想,因为我知道以我的头脑是想不出答案的,它最终还是无解。
那为什么佛教还要倡导人们修忍辱呢?佛菩萨可以包容万事万物,是因为它们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没有好坏善恶。但我们凡夫则不然,我们生活在这世上,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有标准的,好和坏是有界定的,如果我们见恶行不闻不问,就成为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了。

到了第二个阶段,我觉得一味的忍让不是办法,错不在我时我何苦让自己憋屈,见到恶行时我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如果长此以往,我没修好忍辱,反倒会给自己憋出毛病,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
更何况佛教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慈悲和怒目是交替使用的,见善行自然欢喜,见恶行心生嗔恨,我不是神仙,我是凡人,那我就按凡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吧,做个好人,但是要善恶分明。

就这样我又恢复到从前,没有修忍辱之前的状态,一个个性分明的普通人,喜怒哀乐随性流露,不同的是我心里有个“修”的概念,我觉得我当前就如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之中的第二重境界。
在这第二层状态中,我很自在也很舒服,因为我不用委屈自己了,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善恶来主观的评断我认为的是非曲直,并且还有佛教的理论做为支撑。

突然某一天晚上我又开始思索这个令我理不清的问题,我想我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离第三个阶段就不会太远了。
而能够到达第三个阶段,需要我没有分别心,没有是非善恶,我能够欣然地接受所有的荣辱而不为所动,接受忍辱是因为我没有了恶的概念,我也就没有了忍的觉知,我清醒的知道一切都是在因果中打转。

想啊想啊,我突然有些明白了,当我觉得我明白后,我失望了,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
归根结底我就是一个凡夫,今生是,若有来世我还是凡夫,我做不到包容万事万物,就像我们能接受鲜花,但是无法容忍垃圾;我们喜欢得到,而无法接受失去。
想到此处,虽失望,但也有些释然了,那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了,先脚踏实地地做个好人吧,所做一切凭良心、凭良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