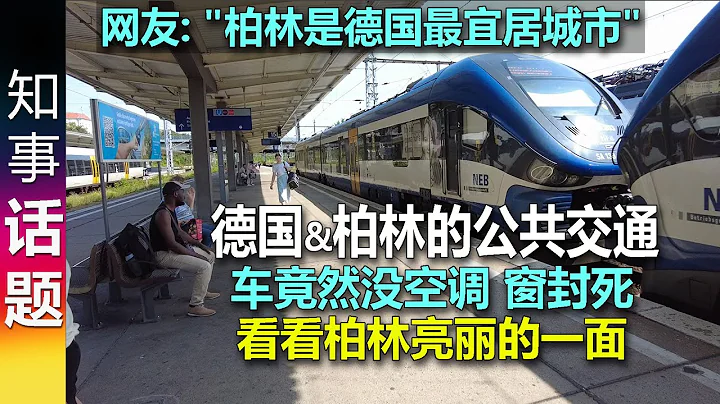前言
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并不是随机和暂时的,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不仅有长期的历史积淀,而且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严峻和深化。贫困所引发的一系列状况和问题需要相应的举措来应对,所以反贫困政策应运而生。就 19 世纪德国城市的反贫困政策而言,其提出和实施既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背景,也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其社会表现形式也具有当地特色。

宗教改革伊始德国的济贫传统
自中世纪始,贫困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出于怜悯和道德宗教责任感,向穷人、老年人、寡妇和孤儿提供物质以及非物质形式的救济,是世界上所有文明的一项社会伦理规范和实践。基督教文明更是从最开始就特别强调这一职责,通过各种形式的体系、机构及活动塑造了个人和团体的实际利他主义形象。就教会而言,“通过教会个体成员的救济援助来完成利他主义的工作是基督教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教会的一项基本功能”。

所以,从宗教改革开始,神学改革家们就密切关注贫困、乞讨等社会问题。马丁·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也反复强调帮助穷人和善行的重要性,“遇见需要帮助的人而弃之不管,却将钱用于买赎罪券,买的不是教宗的特赦而是上帝的愤怒”。在济贫观念上将救赎和善行分割开来。可以说,宗教改革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其中济贫改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社会贫困救济具有悠久的历史,宗教是其形成的基础,济贫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神恩济贫观念。德国在宗教战争耗尽精力之后,所有政治力量都集中于国家君主手中,开始通过更密集的社会制度以及活动来克服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难。

其中,消除贫困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的相关机构和运作方式也在逐渐的形成过程中。德国的济贫模式也极具特色,“最先开始尝试有关社会救济制度化的地区是维滕伯格,该地提出了共同钱箱计划,于 1520 年末或 1521 年初由维滕伯格市政议会通过,其得到路德教的支持。”共同钱箱的募捐所得会用于社会救济,为弱势群体和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且会定期筹集资金。
从城市的各阶层中选出管理人员,“他们要掌握申请救济者的收入、人品以及出身等,还需要判断出救济者是否有从事工作的能力”。虽然这一救济政策是临时的,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为以后德国其他城镇的贫困救济政策奠定了基础,对其进行了补充和继承。可以说“共同钱箱”是新教济贫迈向制度化的第一步。马克思·韦伯曾说:“人们对贫困和济贫问题态度的转变受到新教思想的影响,济贫制度开始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投入运用,并具有一定的现代意味。”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工业化兴起的影响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各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引起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人口、就业等都随之发生转变。这也导致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贫困化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出现,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贫困群体的主要成员包括年老体弱者、失业和低收入者、单亲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以及外来移民等。

工业化时期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引起了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和社会排斥现象,同时也影响到城市的土地利用、居民的空间分布和贫困的分布。随着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大量的贫困现象相伴而生,虽然城市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但是贫困人口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减少的趋势。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兴起,乡村和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逐渐聚集起来,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穷困的无产者。资本积累的反面也是贫困的积累,财富积累的一个沉重代价便是有更多人成为社会贫困者,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新兴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动、土地市场以及新兴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当然也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其中包括迁移到工业地区适应工作需求的跨境流动工人。

19 世纪德国人口急剧增加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反过来,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城市的快速发展。社会进程的加速,生活水平的提升,德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与之而来的就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即社会老龄化问题凸显。相当比例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下。城市民众的健康状况恶化也受到贫困的影响,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是衡量这个国家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之一。婴儿死亡率作为城市人口死亡率的一大重要分支,其变化与城市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息息相关。

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也给德国城市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公共卫生环境恶劣、传染性等疾病蔓延、公共服务缺失、大规模失业等。面对如此棘手的各类问题,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采取新的城市管理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表现最明显的是贫困问题。
城市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农村的劳动者进入城市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必然会出现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此导致居民贫富差距的分化,居民会受到社会因素以及自身情况的影响在社会生存中处于贫困状态。

而且出身于贫困家庭的人所受教育及工作条件较差,其生病率高,死亡较早。原来城市中的
居民以及后来转移的居民都会面临生存环境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还会因为失业、疾病、年老等失去收入来源,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这些问题就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导致酗酒、盗窃、抢劫、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犯罪案件增加,社会治安出现一系列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市政采取相应的举措进行社会救助。在 19 世纪初期德国开始制定对于贫困人口的最低救济标准,但大多数州没有能力实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开始探索更加具体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贫困问题。

城市中还出现了阶级分化不断严重的状况,随着新技术的投入和新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更加速了这一分化,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以城市交通方式为例,在柏林市内乘坐轨道交通每月所需的费用相当于一名建筑工人每月工资的五分之一,这使得工人根本没有能力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便捷生活。除此之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为代表的旧有中产阶层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逐渐衰落,而城市的“新型中产阶层”如公司职员、科研工作者和公务员等随之而生。这些变化让城市成为阶级冲突最集中的地方,各种形式的罢工和游行屡见不鲜。

德国社会贫困问题
在德国工业化开始之前社会贫困问题就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工业门类较少的地区往往最为严重。随着国家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贫困问题愈加严重。1780 年到1850 年间,德国人口从 2100 万增长到 3500 万,增幅达 67% ,而正是在社会秩序中缺乏财产和安全位置的社会群体增长最快。
人口增长伴随着农业、技术贸易以及原始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危机同时发生。贫民阶层的产生受到若干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南部地区,可利用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更无法产生出一定的必要利润,无生存技能也没有足够财产的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自然成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一部分。

面对外国的出口以及早期的国内机械化生产,手工纺织业生产的衰落是导致贫困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破坏了原始手工业者的经济生存能力。第三类陷入贫困危机的主要群体是行会手艺人,职业自由的建立导致了许多行业的人满为患,但是由于熟练工将自己设定为行业的独立生产者,其数量受到行会的限制,很难进入其他行业谋生。这些因素再加上对移民的有限利用,以及早期的工业制造业无法提供替代性的就业机会,最终凝结成了大规模的贫困危机,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城市和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到四分之一。 而且还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这不同于因身体问题或个人不幸造成的自然贫困,也不同于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可以通过最艰苦的工作来维持最低生计,但是他们陷入卖淫、吸毒等恶习中,这种情况在贫民窟、工作间以及监狱新兵中逐渐普遍,这也加重了社会的贫困危机。

结语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德国步入工业化浪潮,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化时期德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贫困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贫困阶层人数增加、城市住屋困难、民众工资水平低、工人问题严峻等方面。所以德国城市的反贫困政策也在逐步调整,日趋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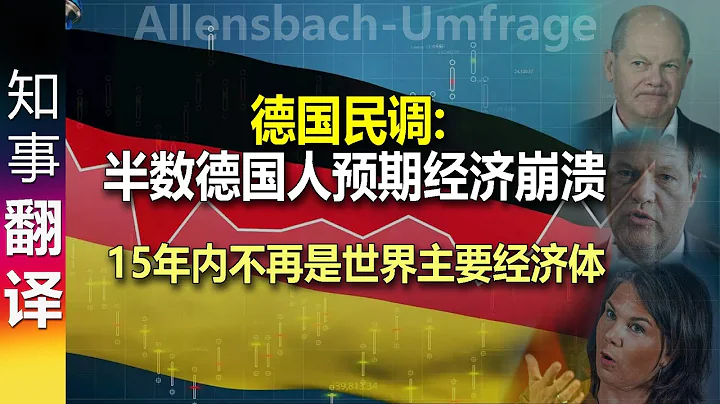
![[ENG SUB] 失能人口 人才去哪儿?你我老之路 迈入高龄社会准备好了吗?!【特别报导精选】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vWLjfCzRKI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8b5Q_6MdbkwsetqSk4wjCmb3F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