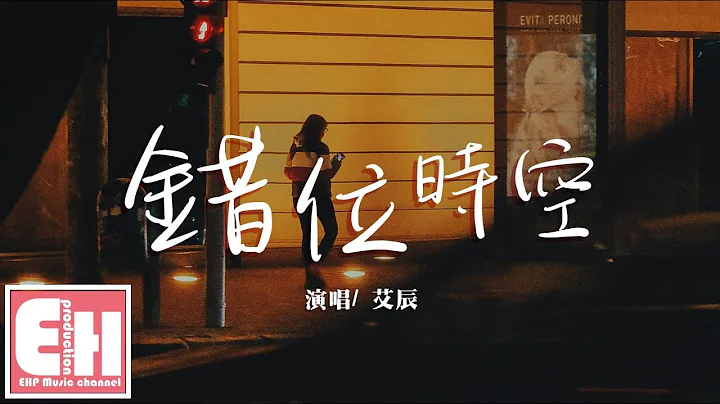阎老师围绕老乔转了三圈,我站在一边冷眼看他。
老乔是一棵树。一棵高大的油松。不知为啥,阎老师叫它老乔。
老乔居住的那座山,叫帽山,是瓦城辖区内海拔最高的山。它不是一座山,是一座连着一座的群山。
阎老师的相机镜头,不分春夏秋冬,无数次对准老乔,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他的摄影工作室里,有老乔一张大幅照片,朝霞的橘红,松针的幽绿,树干的黑褐,以及舞龙状的枝态,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呈现出别样的雄壮和肃穆。这是阎老师的风光代表作之一。
以往阎老师只把老乔作为摄影对象,从来不到它身边去。今年早春的一天却一反常态,他指了指老乔脚下的那片峭壁,对我说,上去看看。
老乔脚下的峭壁上,开满大片的映山红。
我们费了很大脚力才爬到老乔身边。我以为阎老师会居高临下拍摄那些火焰般的映山红,结果没有,他围着老乔转了三圈,说,下山。
阎老师说下,那就下呗。类似的无厘头言行,是他的常态,我早就习惯了,从不刨根问底。
我结识阎老师将近二十年,可是一直对他琢磨不透。
阎老师是瓦城最早的一批摄影发烧友,从胶片机到单反机,一直走在时尚前沿,他还特别擅长把爱好跟谋生之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可以这么说,他的爱好就是他的职业。反过来说也对。
我见过阎老师年轻时的照片。长头发,喇叭裤,以稍息的姿势,站在北京火车站前面。长头发喇叭裤是1980年代初男青年的流行打扮。他们整天在大街上闲逛,鼻梁上架个蛤蟆镜,一只镜片的一角贴着商标,有时手里还要拎着个双卡录放机。
我笑着说,没想到阎老师还是时尚一族。
阎老师也笑,笑罢张罗吃喝。我常在他的工作室里吃喝。
借着酒劲,阎老师把他在喇叭裤时代的恋爱故事都抖搂出来了。知青返城那年,他认识了两个女孩,跟她们轮流约会。后来一个女孩跳了渤海,另一个女孩跳了黄海。好在都被人及时救了上来。上岸后的女孩不约而同,发誓从此不见阎老师,说一见他就有跳海的冲动。
阎老师好酒,他说他曾经一个人到五姑庵的槐树林里野餐,喝得大醉,在槐花的香气里沉睡一个下午。两位尼姑结伴而来,用木棍捅他,看他是死是活。
阎老师还曾经在自家楼下的一棵合欢树下,一边赏花,一边喝啤酒吃扇贝。他坐在啤酒箱子上,对瓶喝。喝光一瓶,咣当,把瓶子扔到脚下,从屁股底下再掏出一瓶,接着喝。结果没等把酒喝完,屁股就掉进了箱子,把邻居一个胖娘们笑得岔气。
忘了是哪一年的孟秋季节,阎老师、我、我的同事小高,我们一行三人,去远郊的云台山采野菊花。也不是采野菊花,是采野菊花的花蕾。阎老师用花蕾制作菊花茶。阎老师对市面上销售的菊花茶嗤之以鼻,他只喝自己制作的菊花茶。
那天中午,我们在云台山的柞树林里野餐时,下雨了。是小雨。雨点打在柞树叶上,簌簌作响。树叶很密,雨滴很少能落到我们身上。我提议下山,阎老师说,这点雨算什么,酒后我们还要喝茶呢。他有一套完整的野外烧茶器具,气罐、炉灶、水壶、茶杯,应有尽有。在野地里喝酒喝茶,是他的生活常态。看得出来。他身上洋溢着浓郁的魏晋风度。
雨渐渐大起来。落进茶杯里的雨,开始是一滴一滴,随后是一簇一簇。我的头发湿了,我的肩膀、我的衣袖,也都湿了。我说,阎老师,我们走吧。话音刚落,突然一盆冷水浇到我的脑门上,我大叫一声跳起来,紧紧抱住身边的一棵树。我早就注意到,雨下了那么久,那棵树的树干却一直是干的。我抱住那棵树,定神再看,阎老师和小高,也都各自抱住一棵树,三个人水淋淋地大眼瞪小眼。此时,小高挂在树杈上的袖珍音响里,正在播放降央卓玛的《西海情歌》。
那天,阎老师、小高和我,身上除了犄角旮旯,别处都湿透了。
那时候没有抓酒驾一说。后来有了,阎老师从此进入半戒酒状态。也是没法子,谁能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呢?
让我最琢磨不透的是,阎老师怎么会掌握那么多让人犯糊涂的知识呢?比如说,他能闻到蘑菇的气味,一起采蘑菇,没人采得过他。比如说采酸枣,他眼里有一道双黄线,必须是生长在碎石上的酸枣才行,最好是页岩上的,黄土上的坚决不要。比如说在辽东的大山里,他沿着一条小溪走走停停,不长时间就寻到一块河磨玉。
从帽山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又一次去看望老乔。阎老师从衣兜里掏出窄窄一片红布条,把它绑在树干上,随后双手合十,口中喃喃有词。等他喃喃完毕,我才小心地问了一句,这是干吗?
阎老师把树根部位的一团枯草踢开,说,你来看看。我探头过去,吓了一跳,树根处有半尺多长两寸多深的斧痕,木茬很新鲜。
阎老师说,有人打老乔的主意,我得保护它。
我指了指树干上的红布条,说,能行?
阎老师笑而无语。
那天阎老师兴致很高,拍了一整天映山红。
两周后,我们第三次去看望老乔。我看到老乔身上,已经缠了三道红布条,树下还多了一只香炉,炉内有三炷残香。
阎老师往老乔身上拍了三巴掌,笑着说,老乔你成神了。
前不久,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棵油松的照片,树干上缠了很多红布条,树枝上也有,照片名为“帽山神树”。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老乔。
我把那张照片转发到阎老师的微信上,下面紧跟着一个点赞的表情。(作者 侯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