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漢趙劉曜在俘虜晉懷帝後主動撤出長安,馮翊太守索琳與安定太守賈疋迎立秦王司馬鄴為帝,是為晉愍帝。
313年五月,愍帝發佈詔書,命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劉琨出兵三十萬取平陽,右丞相、南陽王司馬保率兵三十萬來長安,左丞相、琅邪王司馬睿率兵二十萬攻洛陽,聲稱要「掃除漢趙,奉迎梓宮」,迎回懷帝棺木。

然而卻無人響應,并州的劉琨靠慕容鮮卑才能在并州勉強立腳;幽州的王浚只想乘危割據,獨霸一方;上邽的司馬保和江東的司馬睿則毫無反應,只有避亂南渡的范陽人祖逖請纓北伐。
於是司馬睿便給了祖逖一千人的糧餉和三千匹布,讓他自己招兵。面對這樣的冷遇,祖逖迎難而上,他率百餘部曲渡江,中流擊楫立誓:「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但孤木不成林,他拼盡全力也只是剛剛看到了黃河邊。

最終愍帝堅守長安三年,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身死國滅。
很多人覺得司馬睿無收復神州之志,是故意不救,好坐收漁翁之利,其實不然,他當時的處境與後世的趙構完全不同,趙構是不敢也不願北伐,他是真正的有心無力。
當時北宋雖亡,但屬於猝然而死,宋朝無論是在軍事上,民心上都遠未到崩盤的時候,尤其是長江以南,趙氏已統治一百多年,根基穩固,趙構南遷,南方士族民心還在宋室這一邊。

而司馬睿則不然,晉朝立國僅五十餘年,先是八位之亂,又是五胡亂華,再加上司馬氏得國不正,民心遠未歸附,而長江以南,孫吳滅國也就二十來年,對司馬氏的恨遠大於敬,司馬睿能不能在江東立定腳跟都成問題,何談北伐?
當時的司馬睿雖然已經到江東好幾年了,但並沒有多少實力,說了也不算。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和惠帝、懷帝同一輩分,世襲琅邪王。永興元年(304年),盪陰之戰後,惠帝被司馬穎挾持到鄴城,司馬睿也被裹挾其中。不久司馬穎殺東安王司馬繇,作為司馬繇的嫡親侄子,司馬睿怕遭連累,連夜出逃。

但是司馬穎早有防備,他下令一切關口都不許貴人通過。司馬睿儘管換了裝束,但到了黃河邊,還是被攔住了。幸而從者宋典見機,用馬鞭朝主人身上抽了一記,笑道:「舍長(看管房舍的小吏),官禁貴人,怎麼你也被拘了?」守渡口的小吏信以為真,才放他過河。
永興二年,東海王司馬越起兵討伐河間王司馬順和張方,命司馬睿留守下邳,司馬睿趁機向他要來臨沂王氏大族、參軍王導,讓他擔任自己的軍中司馬,才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親信班底。

永嘉元年(307年),東海王取得八王之亂的最終勝利,開始執掌朝政,他派宗室諸王出鎮襄陽、長安、鄴城等幾個北方重鎮,又派司馬睿去鎮守江東的建鄴。
然而諸王叛亂的前車之鑒不遠,雖然他與司馬睿關係還算親善,但還是防了一手,司馬睿赴建鄴時,除了王導,身邊只有親隨百人,外加三千兵卒。

這是司馬睿在江東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點,但談何容易!
江東是孫吳故土,強宗大族根深蒂固,吳郡顧氏、義興周氏、山陰賀氏等勢力都很強大,原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自封楚公的陳敏就是被這些大族推翻的。司馬睿初到建鄴時,陳敏被覆滅只不過半年光景,要想立定腳跟,取得江東大族的支持艱難卻勢在必行。
司馬睿資歷不深,兵又不多,江東名士根本不將他放在眼裡,不用說主動前去拜見,就是相召,很多人也是愛理不理,為此王導傷透了腦筋,他先是讓司馬睿坐着人抬的「肩輿」出行,去參加「楔祭」,大刷存在感,後又讓司馬睿親自去請在吳中、會稽一帶聲望最高的顧榮和賀循出仕。
最終,司馬睿成功的請出了二人,他用顧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一切軍國大事,都向他諮詢;用賀循為吳國內史,做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此外,他還對紀瞻、張闓等江東名流也都委以重任,自此,江東人士才開始逐漸接受司馬睿。

但這與擁護還差了十萬八千里。司馬睿雖然努力爭取南方士族的支持,但總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合作。特別是在南遷的北方人增多後,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一部分南方士人的反感和疑慮,發生在建興元年的周玘危政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
義興周氏是江東勢力第二強的大姓。周玘的祖父是西晉名臣、鄱陽太守周魴,其父更是在歷史上大大有名,他就是那個浪子回頭除三害的平西將軍周處,周玘自身也不凡,他曾用鄉里義兵三次平定叛亂,在地方上聲望極高。
但他因為父親周處因梁王司馬彤公報私仇,以孤軍御強敵,戰死沙場,因此對晉室並無好感,當年他平定石冰、陳敏的叛亂,目的也僅是為安定鄉土,並不願為晉室辦事,他每次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隊,既不向朝廷報備,也不向朝廷請賞,雖然說不上蔑視晉廷,至少也是沒有巴結的慾望。

所以,建興元年,當周玘看到司馬睿重用刁協、劉隗等北人後深感不滿,於是就秘密聯絡一部分人,要殺死執政的北人,改用南方人士。
司馬睿發覺後,並不敢公開鎮壓(當時周玘為吳興太守),只先調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動身後,再改任軍咨祭酒,拿掉了他的兵權。
周玘也知道密謀泄露,不久便憂憤而死,臨終還對兒子周勰說:「殺我的是中原人,能報此仇,才算我的兒子。」司馬睿明知他要造反,但仍謚他為「忠烈」,對周家不敢稍有怠慢。

司馬睿的本意是想息事寧人,安撫周氏,但事情遠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建興二年,念念不忘父仇的周勰,指使吳興功曹徐馥詐傳叔父周札(時任丞相從事中郎)之令,殺死吳興太守袁琇,起兵舉事。徐馥本來就有部曲千人,加上響應的其他江東土豪,一下就集結了上萬人。孫皓的族人孫弼也在廣德起兵,與之呼應,一時狼煙四起,江東震動。

多虧此後的周札不願被擁立為主,又派人給義興太守孔侃報訊,才使周勰沒有敢一同發動。後來周氏族人周續又在家鄉陽羨起兵,雖然最終也被平定,但還是讓司馬睿驚出了一身冷汗。
事後,司馬睿對周氏族人並不追究,後來還讓周勰做了臨淮太守。
此事就發生在祖逖請求北伐的當年,司馬睿自顧不暇,又怎麼會有餘力鼎力相助兄長愍帝呢?
司馬睿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東大族合作,是真心的不容易,處境如此,他們也只能先集中精力來穩定東南,再圖其他。
另外,即便司馬睿逐漸得到了江東大族的擁護,但還是只能用王導這樣的士族門閥,想獨掌大權,一人說了算還差的遠。

在東晉草創時期,之所以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除了司馬睿信任王導以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建鄴早在永嘉三年就成了王氏的天下。史載,王導居機樞之地,「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其他王氏兄弟子侄也把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比如王導的從弟王敦就是揚州刺史,掌京師重地。
司馬睿是在永嘉元年南下建鄴的,當時他的職位是安東將軍、都督揚州之江南諸軍事、假節,但是到了永嘉五年(311年),江南的很多封疆大吏還是不服從他的命令,有些甚至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 比如江州刺史華軼。

華軼早在司馬睿剛到建鄴時就因不服從司馬睿的命令而鬧了不少矛盾,當時因為晉懷帝尚在洛陽,司馬睿也沒有過多計較,但永嘉之亂發生,洛陽失陷,懷帝北擄,司馬睿被推為盟主,華軼還是不服從。
所以,司馬睿派揚州刺史王敦討伐華軼,雖然王敦最終攻殺了華軼,又督率陶侃、周訪等平定了杜弢,穩定了對長江中下游的統治,但是事後王敦又先加江州刺史,後加荊州刺史,掌握了長江上游的軍政大權,更加勢大難制。

後來司馬睿對王導也產生了猜忌,對王敦更是疑慮重重,最終釀成了王敦之亂。
所以,在江東草創之初,司馬睿本人不僅力量單薄,而且內部還矛盾重重,對於北伐實在是有心無力。
再者,就算司馬睿矢志北伐對當時的西晉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用。
愍帝雖然發佈詔令時口氣很大,但當時的西晉也就僅還保有長安一城之地,而且長安城也因多次失陷賊手,早已不復舊觀,史載,當時的長安城荊棘雜草密布,居民不滿百戶,車駕只有四乘,連百官官印都已失落大半。

另外,晉廷內部也是矛盾重重。
當時在長安擁護愍帝的閻鼎、賈疋、索琳等人,原本就不是一伙人,只在共同對敵時能夠合作,一旦「功成」,就窩裡鬥起來了。
先是賈疋與漢將彭天護作戰,中計被殺。接着,閻鼎又與原來的關中諸將爭權,最後閻鼎殺死京兆太守梁綜,又引起麴允、索琳等群起攻之,閻鼎兵敗而逃,也被殺死。
即便最後,僅存的大將軍索琳還打算臨危變節,派人出城秘見劉曜,詐稱城中存糧尚富,若能對自己許以高官,即願獻城投降,被劉曜拒絕。
這樣的晉廷實在是已經沒有救援的必要。
當時的王導就持此種意見,所以並沒有多少自主權的司馬睿也就放棄長安,任愍帝自生自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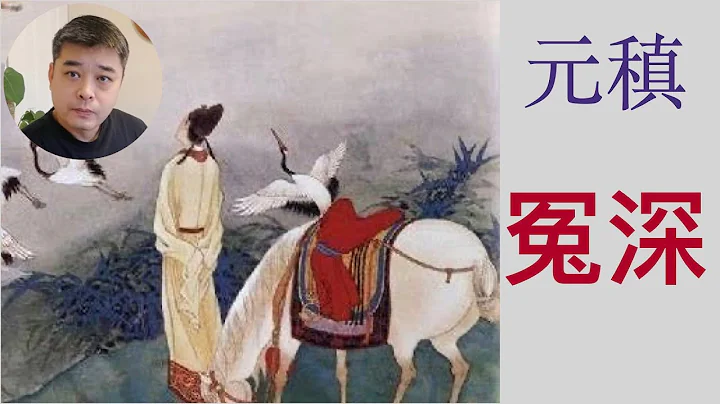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