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內頁圖。
當課堂中的老師與孩子精讀文學作品的時候,他們到底在讀什麼?能讀懂嗎?曾作為語文老師在課堂中開設「髒話課」和文學課的馮軍鶴,將他的12堂文學課寫成了一套虛構作品——《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在書中,孩子們圍繞着性別、災難、情感、霸凌等主題,藉由文學作品展開討論。
撰文 | 陳賽
最早認識馮軍鶴,是他幫學生給《少年新知》編輯部投了一篇小說,是仿照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寫的一個故事。剛看到文章時,我很震驚,不敢相信是一個13歲的孩子寫的。而且,這個叫回祖霆的孩子似乎並不算多熱愛寫作,只是碰巧喜歡養爬行動物而已,所以他將自己的這個愛好編排給了《小城畸人》中一個幾乎空白的背景角色。他管這個孤僻的老頭叫喬尼·喬斯達,並讓他在一場大雨中尋找自己的寶貝寵物,並由此牽引出他的故事。從這個故事裏,我們知道,再孤僻的老頭也曾經是柔軟的孩子,曾經遭受過嚴重的傷害,曾經渴望愛和溫暖,而給予他愛和溫暖的,不是他的父母或同伴,而恰恰是一隻爬行動物。

《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全6冊)》,作者: 馮軍鶴,出版社: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4年4月。
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在雜誌里開闢「寫作實驗室」的項目。我們根據每期的雜誌主題擬出一些有趣的題目,邀請讀者來投稿。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教讀者怎麼寫作,也不是要在我們的讀者中挖掘寫作天才,我們想做的,是在讀者中撩撥一種熱情,這種熱情中包含一個少年對世界的獨特思考,對自己生命經驗的獨特表達,就像回祖霆寫他的爬行動物一樣。
我很喜歡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他說自己的寫作分為兩種,動機也各不相同。當他憤怒的時候,就寫散文;而當他好奇時,就寫小說。好奇,在他看來,不僅是認知的維度,也是道德的維度。比起沒有好奇心的人,一個有好奇心的人是一個更好的人,因為他能代入他者的視角,去理解別人的感受。

《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內頁圖。
在x書店發生的這12節課里,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群青少年對世界、對他者、對自我的好奇心被喚醒的過程。一個童年被戰火摧毀的人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一個人怎樣被一個念頭困住,甚至捆綁了一生?一個被命運剝奪一切的人在人生最後的瞬間會想些什麼?……
如果不是「喬尼·喬斯達」的例子在前,我大概也會懷疑書中的馬老師對文本的選擇是否明智。約翰·史坦貝克、科塔薩爾、理乍得·耶茲,甚至張愛玲,都不是簡單的文本,十三四歲的孩子真的具備對這些複雜文本的理解力嗎?
這些文本的好處在於,它珍視每一個個體的獨特性,並樂於呈現這些個體複雜的處境。人是多麼不自知的生物。一個人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而不是那樣的選擇?人生的各種情境中,是哪些微小的變化影響了我們的選擇?這些是書中的少年們在馬老師的課堂上不斷討論的東西。

《死亡詩社》劇照。
十個孩子和一個老師圍繞文學展開的討論,被寫成一個虛構故事,會讓人想到《死亡詩社》。但與那部電影中的基丁老師不同,馬老師沒有那麼強大的人格魅力,她在故事中的存在感並不強,她並沒有具體地教給這些孩子什麼,甚至在面對他們的困惑時也並不給出什麼答案。除了選擇文本之外,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引導這些孩子從他們各自的生命經驗中調取能夠與這些文本相碰撞的火花。而且,她顯然對這些少年理解複雜文本的能力有着充分的尊重和信心。
通過這些文本,這些少年對人生有了更多的理解嗎?當然。但我相信他們恐怕也產生了更多的困惑、不解和不確定。而我恰恰覺得這些困惑、不解和不確定是更可貴的。當你意識到自己並不了解生活時,才算是窺見了生活的真相。正是在對這些不解、困惑和不確定的求索中,我們的心靈一點點變得更加豐厚、開放和明智。
撰文/陳賽
編輯/王銘博
校對/柳寶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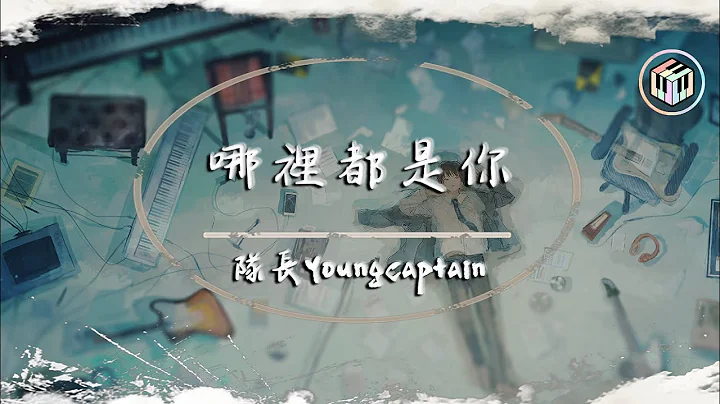









![[ 要搞事情的節奏啊!誰的聲音讓導師無比熟悉、無比期待 ] 《夢想的聲音》第7期 預告 20161216 /浙江衛視官方超清/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wbbOzIOma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tjukvX-Un3PIiu-clOExy3Upr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