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寫的那篇文章《你有隨時可以打擾的人嗎?》下面,有小夥伴留言,講述了關於他一個朋友的故事。
我就用第一人稱講講這位小夥伴要說的故事吧:

「隨時可以打擾的朋友」,我還真有一個這樣的朋友,而且她是一個特別懂得善解人意特別厲害的女孩。
她是我高中時候的班長,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認識十年了。
她八歲那年,父母離異。
十一歲那年,父母再婚。
她曾經跟我說過,雖然新家也很不錯,但畢竟現實生活不會是《家有兒女》,重組家庭,很多東西還是要小心應付的。
或許就因為這樣的應付,你也被雕塑成了一個對人類情緒洞若觀火的,且能在任何情況下周全一切的人。
她不僅有能力照顧好自己,而且有餘力和智慧為身邊的人擺平他們擺平不了的事兒。
毫不誇張的講,只要在她身邊,聽到她開口說話,你就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和信服感。
所以高中時候,在她的領導下,我們班級實現了去班主任化管理。
無論是紀律、衛生、學習、大小活動、同學矛盾,甚至老師間的糾紛,她一個人全權負責。
並且處理的從容不迫,得心應手。
也正是如此,很多時候,你看到她不屬於這個年紀的幹練,會忘記她僅僅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
她也有自己的迷茫,也應該有自己的脆弱。

後來,她去北方,我去了南方。
我們高中畢業,也有七年了,見面的機會並不多。
這幾年,我也去過很多地方,接觸過很多人,也發生過很多事兒。
不知道怎麼了,無論我多麼用力去社交,多麼努力靠近一個人,我好像始終都是孤獨的。
這種孤獨,很難形容。
就好像你看到一段有意思的視頻,一段很觸動的文字,特別想分享,特別想分享到你的通訊錄里某個好友。
但是,當你打開通訊錄,發現你不知道分享給誰。
於是你只好分享到朋友圈,然後你期待有人給你點贊,期待有人給你評論跟你探討。
但其實你明知道,可能沒有人會打開看,沒有人真正在意你那些細微的悲喜。
孤獨並不是來自於身邊無人,感到孤獨真正的原因,是無法與他人交流最重要的感受。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和我說,她失戀了。
我知道,她因為那段感情,淡出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拋棄了情緒的其他出口,戀愛就是她唯一的快樂源泉。
她甚至把他們之間的共同未來,當做精神圖騰。
失戀後,她說她很痛苦,但她沒有辦法把這些負面情緒交給朋友。
因為她不想做掃興的人。
「雨,不大,自己能挺住。」
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我們之所以成為十年摯友,是因為在我眼裡,一直以來,我看到的都不是她在其他人面前的圓滑剛毅,而是她的無援可依。
我就覺得,不能讓她隻身一人站在滂沱大雨中。
於是,我要去她的城市,也為她撐傘。
我們見面後,沒有什麼熱淚相擁,也沒有什麼悲痛深聊,就簡單的兩人。
我們逛商場,唱k,躺在一堆外賣里看劇,有的是聊不完的幼稚笑話。

這個時候,讓人戲劇性的事兒發生了,家中父親急病,母親着急電話。
我要趕緊回去,沒有當天的機票,只好明早的機票。
當訂完票放下手機後,我不知所措。
旁邊的她,突然張開雙手,給了我一個擁抱。
我當時特別想哭,但沒哭出來。
好像就在我被擁抱的那一瞬間,我那幾年積攢的所有疲憊、孤獨、痛苦都被消解了。
後來我回到家後,有想過,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接到這個電話,我會怎麼接受呢?
大概是在床上什麼也不做,開始思考死亡,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開始思考千百年來,哲學家想了一輩子都沒明白的課題。
最後拖着疲憊的心智,度過接下來一段痛苦難熬的日子。
可在她身邊,我的苦難,僅僅被她的一個擁抱治好了,就被一個擁抱治好了。
故事講完了,

或許我們都太想做一個無堅不摧的完人了,總要逼迫自己吞噬世界的規則,在龐雜的信息流命令自己必須成熟,獨立思考問題。
於是,我們在高維世界裏不斷錯位,逐漸活成了一個個不相關的質點。
然後,我們變得羞於展露脆弱,不敢麻煩彼此。
或者說我們認為沒有必要麻煩彼此。
我們都習慣了自己一個人消解自己的全部情緒,習慣思考着漫無目的的思考,最終論入虛無。

這或許就是精神內耗的根源吧。
可這東西,誰能治得了呢?
能治好它的,可能只有那個願意為你撐傘,也願意讓你為ta撐傘的人。
如果你站在雨里,不妨回頭看看,傘在哪裡。
雨很大,你可以躲在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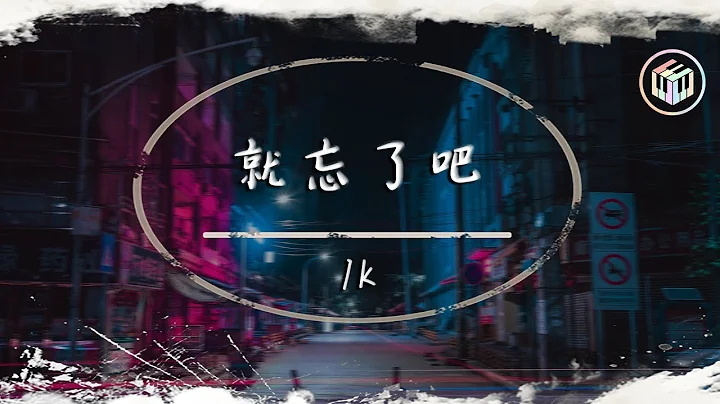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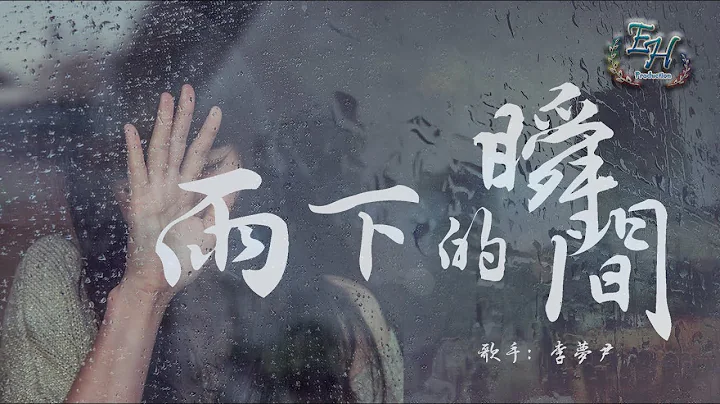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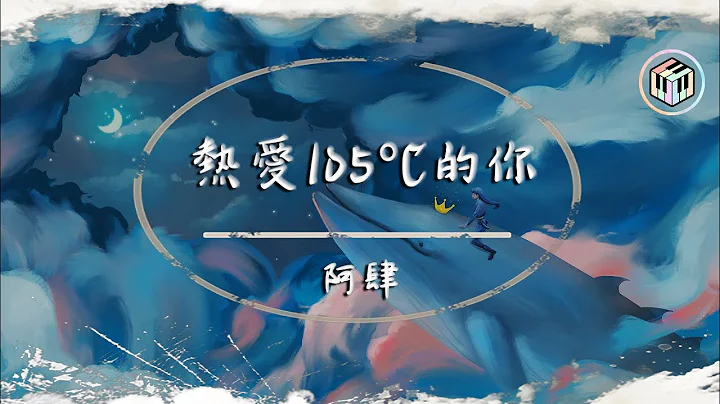










![[ 要搞事情的節奏啊!誰的聲音讓導師無比熟悉、無比期待 ] 《夢想的聲音》第7期 預告 20161216 /浙江衛視官方超清/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wbbOzIOma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tjukvX-Un3PIiu-clOExy3Upr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