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人民公社電報送至杭州老家時,黑龍江知青海聞發現自己從圖書館系被調劑至經濟系,他疑惑:什麼是經濟學?
1977年,因「文革」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復,570多萬應考生湧入考場,最終錄取率僅為4.6%,激烈的競爭空前絕後。第二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那幾年,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同學們常常為了一件國家大事爭得面紅耳赤,學術自由和對社會的責任感俯首可拾。
時隔40年,當年的學生林雙林感慨,沒料到經濟學成了以後中國最熱門的學科。
一
什麼是經濟學?這是當時不少經濟系學生的疑問。
北京朝陽無線機加工車間主任潘慕平拿到報名表時,距離報名截止時間只剩一個小時。沒時間琢磨學校了,匆匆填了招生目錄上的第一個學校北京大學,中文系和經濟系後,同事小王立馬揣上他的報名表,飛快地往區里騎去。
陝西農村娃林雙林的夢想是學哲學「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至於經濟學?他記得一位老師回老家說自己學經濟,沒人懂,老鄉以為是「京劇」,硬讓他唱。
就在姜斯棟去北京的火車上,坐在他對面的兩個女生嘟噥着:「我明明報的中文系,怎麼給我換成了經濟系。什麼是經濟?」姜斯棟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經濟政策研究,他喜歡這份一年裡跑十來個縣調研的工作。29歲了,還想學,姜斯棟三所大學報的都是政治經濟學專業。和他一樣,也有一批同學想學經濟。
陶海粟出任陝西省延川縣人民公社書記的第一天就下鄉去村裡轉了圈。那年大旱,整個川道顆粒無收,而山上那塊「資本主義的尾巴」的自留地倒是一片綠油油。在農村九年,28歲的陶海粟對當時處於國民經濟崩潰邊緣的農村積累了不少困惑。而在中國的南方,23歲廣東青年何小鋒則已經是單位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輔導員。
1977年8月8日,在科技教育知識分子的講座上,鄧小平確定恢復「文革」以來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4個月後的冬天,570多萬應考生湧入考場。
就在恢復高考前一年,海聞到北京出差,在北大校門口往裏面看了半天他都沒敢進去。他特別羨慕,又特別失落。他想,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跨進大學校門?
17歲到26歲,北大荒九年,一批又一批地知青被推薦去讀大學,海聞幾次被公社選去參加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活動、被推薦上大學當工農兵學員,都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被否。命運就像「菜場里的剩菜一樣」。
海聞對澎湃新聞說:「高考進入北大後,我就不再背有政治包袱,是高考把我從舊體制中解放出來。」
在高考中斷的十多年中,中學的教學也早已支離破碎。何小鋒對澎湃新聞回憶,「學理科,會開拖拉機,但不會解方程。英語沒有學滿26個字母,而是學了幾句口號,We love Chairman Mao,我們愛毛主席。還有『繳槍不殺』,怕再打仗。」
1977年的高考錄取率為4.6%,激烈的競爭空前絕後。時隔40年,林雙林感慨,沒料到經濟學成了以後中國最熱門的學科。
北京大學經濟系77級只設一個專業政治經濟學,學生共80人,分成兩個班級。1954年是他們出生年份的中位數。32歲的張文祥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而年齡最小的郭京平只有17歲。「像我們老三屆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班級中年齡小的1966年的時候才6、7歲。」26歲的海聞正處中間。
姜斯棟29歲,年齡排班級第三,屬於「老」字輩,老薑說:「其實對老師來說也不一樣,他們從來沒有教過這樣一批學生,30歲上大學,在原來單位是幹部,恨不得比老師還會管班級。」老字輩幾乎都帶薪上學,陶海粟每月拿44塊錢,有時還敢上全聚德吃一頓烤鴨。
入校時,黃少敏很想當班幹部,但他發現身邊的同學都很有資歷:黨支部書記于吉做過多年工廠廠長;組織委員姜斯棟是山西省委寫作班子的大筆杆子;宣傳委員吳小賀是京郊某村大隊黨支部女書記;青年委員張煒是武漢市教育局科長……像於華、海聞這樣久經考驗的中共黨員只能做小組長。
相比北大其他的學科,經濟系的學生年齡偏大,黨員比例更高。據姜斯棟和何小鋒回憶,他們的高考數學接近滿分。「到底是因為我們被淘汰下來調劑過來的還是因為被挑選出來的,不知道。」海聞猜測,「說不定我們是被挑選出來的。」
成分複雜與年齡跨度大是這屆學生的兩大特徵。來自工農兵學各成分的學生構成了77級,他們如小溪匯入大海般來到北大37號樓二層,再上面是法律、政治系,他們則是「經濟基礎」。
1978年至1982年,77級的本科四年,也是舉國上下除陳布新,新舊碰撞的年代。
1978年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確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也是這四年,包產到戶一直艱難地前行,直至77級畢業,人民公社制度也未宣布解體。
而當整個社會和校園在試圖全面反思和否定「文革」時,作為「文革」末期的最後兩屆工農兵學員的尷尬與困惑,與從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77級的優越自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拿我們自己來說,77級的學生當時普遍被認為是來自基層的精英,其實我們自己也是剛剛走出那個荒謬的年代,在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上,都難免帶着那個時代的痕迹。」陶海粟回憶。
即使每個人的特質是如此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姜斯棟說:「這個機會對所有人來說都太珍貴了。所以要說上進心,那是發自內心的。」
四十年過去,陶海粟對澎湃新聞表示:「恢復高考就是中國在教育領域回歸人類文明的大道。」

北大經濟系77級2班六組(若未做說明,圖片均由海聞提供)

北大經濟系77級2班四組

北大經濟系2班五組
二
「332路,開往頤和園……」天剛蒙蒙亮,唯一一趟公交車的報站聲響起時,也是北大學生起床的時間。
醒來後,何小鋒總要問一下自己,上北大是不是夢啊?「就覺得根本不可能,我那時候根本沒出過廣東。」何小鋒廣東口音重,剛入學那會兒,他都不敢開頭說話,有些同學也不叫他名字,就叫他「廣廣廣」。
在邊陲小縣下鄉九年後初入北大,海聞的第一感受是自己的「土」:「就是鄉下人進城了。」「北京的人天天討論中央的事,他們還會對毛主席評價,我們就會覺得怎麼可以討論毛主席呢?完全就覺得是一種很新奇的事情,給人很多衝擊。」從陝西農村進京的林雙林感受相同,「過去的環境下,啥話都不說,語言特別謹慎,來了北大之後,我發現同學的語言都特別敞開。」
為了班級「創三好」,團支書林雙林掙扎着起了床,參加早上的集體體育鍛煉。而此時,同宿舍的潘慕平已經在院子里背單詞背了半個小時了。

圖書館學習
經歷了「文革」後的中國,開始了瘋狂的學習和追趕。在北大,學生的生活以讀書和鍛煉為主,每日起床後要繞校園跑兩圈,如果哪天有遠足計劃,那麼就提前幾天多跑幾圈。「那個時候大家都有種感覺,覺得未來要肩負很大的責任,所以要準備好。」石小敏曾回憶。
早上,北大圖書館門前早已候着一大批學生。門一開,「噠噠」腳步聲一陣,學生們魚貫而入。如果晚自習不佔座,就別想找到位置。
無論是走路、吃飯、坐公交車,林雙林手裡都拿着單詞本。一個學期後,同在英語慢班的海聞納悶,林雙林怎麼去快班了?他們常晚上湊在一起聽美國之音。
林雙林決定念研究生。在陝西農村,林雙林一心想去「面外的世界」,當兵、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他全都報了名,用他的話說「奮不顧身」。來到北大後,他拼了命地學習,三個暑假都留校自學,同學稱他在北大讀了五年本科。


課餘生活,編排英語劇
懷疑精神是那個特殊時代學生的另一個特質。大學前兩年,石小敏對老師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有懷疑,他模糊地覺得哪裡不對,又說不上來。「我們參加過工作的人再去學習馬列主義,就會覺得這些跟實際不大一樣。」
「不好學,馬克思那邏輯咱也跟不上,開始也質疑,但考試要考這些東西,老師一字一句地念,學生呢就記。」林雙林把筆記記得連老師的一聲咳嗽都寫了下來。
潘慕平對石小敏印象深刻,「他最大的特點是憂國憂民,相對來講他悲觀一點,所以總把事情想得非常嚴重。」
那些年,學生關心國家大事,經濟系尤甚,常常為了某件國家大事爭得面紅耳赤。何小鋒記得:「那個時候風氣很好,天天都在爭,一個宿舍也爭,開會也爭,當時北大有很多講座,如果聽的不好,站起來就爭。大家很強調個性和自由。」
1978年春,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村民為了能吃飽飯,在契約上摁下紅手印,率先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給予支持,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包產到戶」拉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序幕。
海聞至今能記得當時的疑惑,「當時一個新舊思想轉換的過程,我們一直批包產到戶,現在搞包產到戶,那大家怎麼理解?還有剝削,私人企業到底算不算剝削?」直到經濟學家孫冶方來北大開講座,他說:「中國的發展問題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封建殘餘的問題,反封建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民主、科學的建設還差很遠。」
1979年初,由北大經濟系77級學生自主創辦的《學友》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應運而生。鄧英淘參加國務院農村改革課題組,探討了包產到戶等改革最前沿問題;丘小雄比較發行債券籌集資金的利弊;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率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日考察後寫下觀感;石小敏質疑按勞分配等敏感問題,引發了77級、78級的討論……
創刊9個月後,北大37號樓225室很忙碌,全國42所院校經濟類學生的投稿信件紛然而至。
1979年夏,北大經濟系與南開、廈大、人大、復旦、暨南、武大七院校經濟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學術團體共同發起,向全國各大學倡議創辦《全國大學生經濟學報》和「全國大學生經濟學團體聯合會」,受到了全國經濟類學子的響應,首期《全國大學生經濟學報》經選擇、編輯,收集文章40多篇,9萬多字。「那時候我們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潘慕平說。
林雙林家裡窮,一年只穿一件制服,冬天加件棉襖,但胸前別著一枚北大白色的校徽,就自豪得不行。「當時也不愁分配,我們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林雙林說。
在當時,大學生的國家榮譽感強烈到可以被一場球賽引爆。1981年3月20日深夜,廣播里傳來中國男排擊敗南朝鮮(韓國)隊,取得參加世界盃排球賽資格的消息。
整個校園沸騰了,學生敲打着盆碗湧出宿舍樓,燒了掃帚當火把,高喊着「中國萬歲」。中文系的劉志達忽然高喊出一句「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口號在隊伍中迅速傳開。那夜,伴隨着這句口號,北大學生一路遊行至中關村。
姜斯棟說:「整個北大就是有這個氣氛,一方面是那批學生有一種一定要好好學習有所作為,因為國家正在振興。就那麼簡單一個球賽,把年輕人激動了一把,一個晚上燒啊鬧啊,那種振奮。」
在八十年代,新事物的衝擊是應接不暇的。喇叭褲、迪斯科、鄧麗君、朦朧詩、潘曉來信、傷痕文學、星星美展……當時的大學生幾乎都是鄧麗君的粉絲,有條件的買個磚頭錄音機,聽得如痴如醉。「以前都是那種雄壯的,打倒美帝蘇修,竟然會有鄧麗君這種,抒發人的一點基本的感情,以前都是絕對不可能有的。」陶海粟說。
在火車上,海聞讀着盧新華的小說《傷痕》,眼淚直往下淌。「其實人不會因為打擊而流淚,但會因委屈而流淚。過去那麼多年我認為我應該是需要被改造的,從來沒想到這是對我的不公平待遇。」
大三西風東漸,社會逐漸開放,交誼舞流行起來。經濟系男生多,女生少,找不到舞伴的男生就在宿舍里抱着凳子跳舞。一位女同學主動表示要教林雙林跳舞,「我那時思想封建,還不好意思。後來追悔莫及,至今不會跳。」林雙林回憶。

喇叭褲、吉他和校園歌曲(來源網絡)

學跳舞(來源網絡)

班級party

系運動會奪冠

密雲水庫春遊

籃球比賽
三
在經濟系,中青年教授被稱為老師,老教授們被稱為「先生」,這是當時大家表達尊敬最高的稱謂。經濟系的多門課由幾位老師合開,一些年輕老師只能做助教。上課前,學生為老師帶一個玻璃杯,再拎上一個暖壺倒上熱水。
78歲的系主任陳岱孫被師生們親切地喚為岱老。民國政府曾聘請他當財政部部長,岱老以志不在官謝絕。"文革"時期,被戴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帽子的岱老從未被人直呼姓名,工宣隊、軍宣隊都尊稱他"陳先生",在北大找不出第二人。
1980年,北大率先全國高校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但這樣的先行之舉備受壓力,也因此受到上級對其辦學方向問題的調查。隨後,不少高校因仿照北大增設較多西方經濟學課程而受到批評指責,甚至停止西方經濟學課程。
在一股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中,岱老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發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隨後《人民日報》用半版重登,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岱老提出的「整體批判,個體借鑒」的態度,使西方經濟學有了一個合法的生存空間。
「據說陳岱老在『反右』時有一句名言『就是不開口,神仙難下手』,那時候他都沒被抓住毛病,卻在反對改革開放的思潮下發表他的看法,這很不容易,80歲的老頭,明顯是鬥爭來了,他就挺身而出了。」姜斯棟說在北大受到影響最深的是「批判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77級經濟系的師資之豐富,令林雙林至今感慨。「像陳振漢先生,那都是大師啊。」陳先生1941年就在美國經濟頂級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發文章,北大至今無人再及。而中國經濟思想史權威趙靖先生每次講課都講到汗流浹背。趙先生鼻樑高聳,眼窩深凹,講話時雙目直視對方,語氣斬釘截鐵。
現今87歲的經濟學界泰斗厲以寧在給77級教授「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時只有50歲。他把經濟學講得極為通俗易懂,「兩條線一個點,經濟學就是依賴供給、需求的分析框架」。說著,林雙林將兩根食指交叉一疊。
學生喜歡向厲以寧提問,有些還挺尖銳,包括對政治的看法。厲以寧很坦誠,面對他沒思考過的問題,他會直接回答,對不起這個問題我沒想過,或者我需要回去思考一下再告訴你。海聞印象深刻,「一個老師居然很明確地告訴你這個東西我沒想過。」
厲以寧也是較早將西方經濟學理論和中國改革開放結合的人。當時就有聲音說他是投機,「我當時也覺得他有點趕時髦,因為北大很多老師,像陳岱孫是非常嚴謹做學問的,學問就是學問,和政治不搭邊,你不能把學問隨意地拿過來跟當前的實際情況結合,然後做一個修正和發展。但厲老師後來有所堅守。」潘慕平說。
1986年春的北大五四經濟學論壇上,厲以寧發表著名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演講,「中國經濟改革可能會因價格改革而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定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他提出將股份製作為企業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貢獻。
也是受到厲以寧「西方國民收入統計」講座的啟發,何小鋒寫下《勞務價值論初探》一文。當時學術界批判西方把服務業也計入產值,何小鋒則撰文表示,中國的經濟統計只算「物質生產」領域的產值,是一種拜物教的表現。這挑戰了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學中「勞務不創造價值」的說法。1981年4月,最高權威專業刊物《經濟研究》將其刊登,引起很多反響。
當何小鋒趕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會議室時,已滿滿坐了50多人。權威經濟學家孫冶方、國家統計局領導在會議上點名批評了何小鋒的觀點。會後,何小鋒追上孫冶方,感謝孫老的批評,但不打算改變觀點。孫冶方對他說,批評你不是壓制你,我們是平等的,你也可以點名反駁我。
後來,中國提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國民經濟統計吸納第三產業,服務經濟學理論得到迅猛發展。

經濟系主任陳岱孫(左)與何小鋒(右)(來源網絡)
「北大那時還保持着一點兒『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官僚氣也不是那麼濃,加之80年代初社會上思想解放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校內思想和學術是相當活躍的。但是對於馬克思理論這種量級的體系,還是照抄照傳、闡發詮釋居多,鮮有不同聲音發出。」陶海粟於今年回憶。
1982年初,經濟系77級畢業了。在原本歡聲笑語的全系師生歡送77級畢業大會上,一位年輕的老師突然站起來再次反對了何小鋒的觀點。這時,厲以寧站起來大聲回到:「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話十年後沒人記得;有的年輕人人微言輕,但他的話十年後仍然有人想起。」何小鋒至今難忘厲以寧對一個學生的解圍,他將之稱為「經濟系的溫情」。
四
畢業前,海聞收到了美國長灘加州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為恢復高考後北大自費出國的第一人——海聞對「發達國家」、「現代化」等名詞充滿好奇,美國的經濟政策和市場機制是怎樣的?大三開始,他便騎車奔波於北大與北京圖書館查資料、遞交申請。
而林雙林正在圖書館看書呢,突然被叫去了陳岱孫的辦公室。學校決定派他公費去美國留學。林雙林立馬錶態,一定好好學習,早日學成歸來。
畢業後去哪兒?陶海粟和鄧英淘談起這個話題。早就參加了農村發展研究組,常在各地調查的鄧英淘說,國家正是急等用人之際,哪有再泡幾年的時間呢?

北京大學經濟系七七級畢業照
畢業十年後,中國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帶動下,熱火朝天地進行着經濟建設。楊濱抓住了90年代中期的市場機遇,在汽車市場爆發期,做起了汽車貿易業務,後又在中國中產階層飛速擴展時投入至藝術品收藏領域,成為現在77級經濟系的「首富」。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來到中國,舉辦「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國際研討會」。曾在北大是上下鋪兄弟的海聞和易綱都曾在學會擔任過會長。在舉辦地海口,他們見到了從英國來的張維迎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四人聊起來,是不是可以創辦一個中國經濟的研究機構?
1994年,易綱和海聞先後放棄美國大學終身教職回到中國。這年夏天,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勺園5號樓成立。隨後,CCER發展成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國發院),是現在中國經濟研究的重要智庫。
「當時出去就是為了以後回來參與經濟工作、參與改革,那一定要了解發達國家是怎麼樣的,學更多的知識,去看看人家是怎麼做的。」海聞說。

1980年大三,北大經濟系77級2班歡送易綱(二排中)赴美留學。
兩年後,易綱去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央行旁邊的民族飯店,潘慕平問易綱,你現在掙多少錢。900多塊。當時,在投行的潘慕平一天掙的錢相當於易綱一個月的工資。
「但是他的作用要比我在投行重要得多。我對他說,如果由於你的努力,為中國參與制定了一個正確的貨幣政策的話,那你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是很大的。後來他提升得非常快,在宏觀經濟上的問題我就沒有辦法和他對話了。」潘慕平說。
如今政、學、商界許多領軍人為77、78級大學生,被稱之為「77、78級現象」。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劉海峰曾撰文指出,「77、78級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時代的需要、特定時代的產物。
何小鋒說:「我們這80個同學,第一沒有私心,第二不會搞貪腐。我們這批同學正好反映了這段歷史(恢復高考後至今)。」
在去北大國發院上班的路上,每每走過未名湖畔,林雙林的心情就沉重起來。「就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重大,覺得應該對這個國家的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而40年後,面對澎湃新聞的採訪,陶海粟則嚴肅地提醒道:「人是活生生的人,在滿足我們基本需求的情況下,再來談個人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不要把人都變成一種純粹的符號或者口號。」
附北京大學77級經濟系不完全名單:
畢井泉,國家葯監局局長,第十九屆中央委員,原國務院副秘書長
易 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張曉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丘小雄,原國家稅務局副局長,原總理辦公室主任
李鐵軍,原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能源局局長
陶海粟,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摩科瑞能源集團亞洲區執行董事
吳稼祥,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現為學者
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於 吉,原國務院國資委企業分配局局長
張克洪,寧夏自治區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
李錦平,原寧夏科協黨組書記、主席,曾擔任寧夏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正廳級)
趙慕蘭,原北京市政府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劉 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原北京大學副校長
海 聞,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滙豐商學院院長,原北京大學副校長
林雙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經濟學教授
何小鋒,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王志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蔡曙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少民,美國歐道明大學管理學院國際商業講座教授
王家卓,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金融學教授,大史泰頓島學院會計與金融系主任
黃少敏,美國劉易斯克拉克州立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
張 菁,美國國家社保局經濟學家
何 劍,美國俄亥俄州政府政策研究與戰略規劃部研究員
劉英莉,美國諾福克市社區服務局財務總監
於 華,摩根斯坦利華鑫基金董事長,原深交所研究所所長
楊 濱,北京達世行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小賀,北京北方聯盟公司董事長
潘慕平,曾任國際投資銀行-洛希爾父子有限公司董事,已退休
任保山,曾任許昌市黨校副校長,已退休
鄧英淘,原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故)
鄭學益,原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部長,經濟學院教授(已故)
朱善利,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已故)
參考書目與文章:
《百年華章——北大經濟學院(系)100周年紀念文集》、陶海粟回憶北大經濟系77級博客文章
(實習生慕立瓊對此文亦有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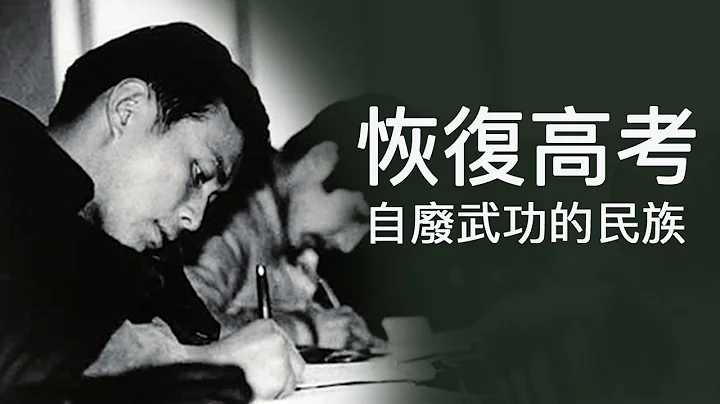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