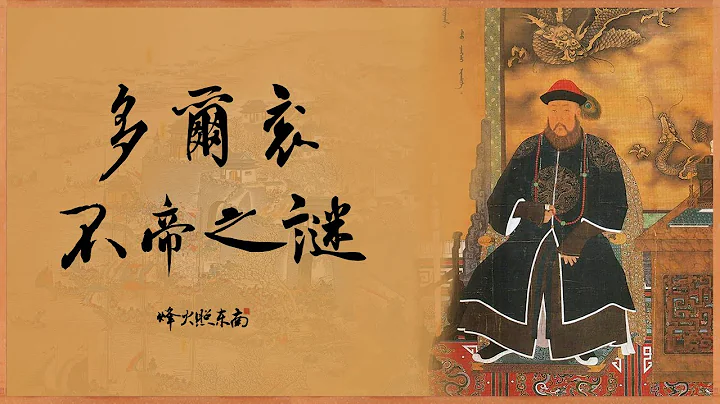摘要 :梁啟超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較早對列強侵略進行理論思考與闡釋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有形—無形瓜分」論,對列強侵略中國的方式、手段進行深入剖析,得出「無形」更慘於「有形」的結論,觸及到列強殖民擴張的本質特徵。之後,隨着歐美日本政學界「帝國主義」論的盛行,梁啟超不僅將之輸入國內,而且對其進行理論闡釋。與西方「帝國主義」論旨在為列強殖民侵略辯護不同,梁啟超的「帝國主義」論則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上,在借鑒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論相關概念的同時,摒棄其中正義化甚至美化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內容,充分警惕並揭示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尤其強調經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危害,與其「有形—無形瓜分」論有着內在的思想延續性。梁啟超對於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大勢及其手段、特徵的認知與中國應對之道的闡發,構成了此期中國知識界分析國際局勢與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話語,在當時輿論界產生深遠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的對外擴張進入新的階段,歐美政學界對此迅速作出理論上的闡釋,提出帝國主義論。隨後,此一理論不脛而走,向全球蔓延。誠如時人所言:「盛矣哉!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也,勢如燎原,不可嚮邇。世界萬邦,皆折服於其膝下,讚美之,崇拜之,而奉持之。」帝國主義論之所以受到了歐美日本知識界、政治家的崇尚,關鍵在於它為列強的侵略擴張提供了理論支持。對於歐美各國而言,帝國主義不只是理論,更是實踐。
而此時的中國,恰是列強侵略的最大目標地,列強的擴張意味着中國的亡國滅種。甲午戰後不久,先進的中國人即已感受到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因此,面對列強的侵略擴張,中國知識界自然有不同於歐美知識界的感受,他們既看到列強在世界範圍內掠奪殖民地的瘋狂,又切身感受到各國「瓜分」中國的危迫,故而其理論思考也與歐美各國的帝國主義論全然不同。以往學界比較關注歐美特別是日本的帝國主義論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知識界應對列強侵略的理論思考早在歐美帝國主義論輸入之前即已開始,梁啟超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較早思考此一問題的思想家,他的「有形—無形瓜分」論就是此一思考的最初結果。歐美帝國主義論輸入中國之後,由於立場不同、問題意識不同,中國知識人關於帝國主義及其理論的認知也與歐美日本有較大的差距,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故本文擬以梁啟超為中心,從較長時段出發,考察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所做的理論探索,重點關注他們最初提出的「瓜分」論與後來「帝國主義」論之間的思想關聯,從而揭示中國知識界相關思考的內在連續性和獨特性。
一、從「有形之瓜分」到「無形之瓜分」
「瓜分」一詞,中國古已有之。但將「瓜分」與中國聯繫起來,則是甲午以後的事了。甲午之前,儘管中國的主權已開始被列強侵奪,但此時的國人尚不認為中國有被「瓜分」的危險。甲午一戰,泱泱大國竟敗給蕞爾島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清朝的腐敗無能暴露無遺,國人的危機意識驟然從此前的積貧積弱轉變為生死存亡,扶危之方也由之前的求富求強轉變為救亡圖存。緣是,中國有識之士奔走呼號,上到開明督撫下到地方精英都以變法為職志,維新風氣為之一開。在看到「草茅之間、風氣大開」、各省封疆「攘臂苦口,思雪國恥者,所在皆有」的局面後,梁啟超一度態度樂觀,曾不無自信地表示:「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然而,緩不濟急,梁啟超的話音剛落,德國便強行佔領膠州灣。這一無端掠奪中國領土與主權的行徑給中國朝野帶來極大刺激,梁啟超等有識之士據此認定:「瓜分之事已見,為奴之局已成。」他甚至與譚嗣同等人聚集湖南,開始籌備「亡後之計」。

梁啟超(1873—1929)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在膠州灣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梁啟超上書陳寶箴,公開其變法「自立」、以備「亡後之事」的主張,稱:「數年之後,吾十八省為中原血,為俎上肉,寧有一幸?故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天下之事變既已若此矣,決裂糜爛,眾所共睹,及今不圖,數年之後,所守之土,不為台灣之獻,即為膠州之奪……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六飛有駐足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倚恃之所。」如果說甲午戰敗後,梁啟超等人呼籲變法尚是為了救亡圖存的話,那麼此時,他所討論的已經是「亡後」之圖了,這顯然是膠州灣事件刺激下樑啟超對中國前途的最新判斷。
在相近的時間裏,譚嗣同也上書陳寶箴,闡述中國面臨的「瓜分」危局與應對之道:「夫以各國之挺劍而起,爭先恐後,俄、法、德暗有合縱之約,明為瓜華之舉……今已西正月矣,在西二月分割之期,直不瞬息耳,危更逾於累棋,勢將不及旋踵。」從「西二月分割之期」一語可見,當時已有二月分割之說在流傳;「今已正月」,距離「瓜分」之期僅一月之隔,因此譚嗣同提出興「民權」的主張,同樣是作為「亡後之事」。他說:「練兵固所以救亡,而非能決其不亡也明矣。於不能決其不亡之中,而作一亡後之想,則一面練兵以救亡,仍當一面籌辦亡後之事……語曰:善敗者不亂。嗣同請賡之曰:善亡者亦不亂。善亡之策有二:曰國會,曰公司……言興民權於此時,非第養生之類也,是乃送死之類也。」無論是國會、公司,還是民權、議院,在譚嗣同這裡,統統都是「善亡之策」,這同樣是在膠州灣事件刺激下產生的。

1898年3月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
其實,不只是譚、梁準備「亡後之事」,身為巡撫的陳寶箴也不無共識。據梁啟超所言,膠州灣事件發生一月後,陳三立突然約梁啟超等人「集於堂中,坐次述世丈(陳寶箴——引者注)之言,謂時局危促,至於今日,欲與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萬死一生之策。彼時同座諸公,咸為動容」。陳寶箴所說的「破釜沉舟、萬死一生之策」,正與梁、譚的「善亡之策」異曲同工。而梁、譚的自立、民權主張正是在陳寶箴的這一啟發與支持下提出的。
梁、譚、陳可謂先知先覺者,膠州灣事件發生後,他們立刻意識到中國就此被「瓜分」的危險,因此第一時間開始籌備「亡後之事」「善亡之策」。而由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列強「租借」中國港口、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也佐證了他們判斷。俄佔旅大、英國占威海衛、法佔廣州灣,他們並將一省或數省劃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其中的路權、礦權、用人權、財權隨之喪失。這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時人的亡國之憂隨之加劇。與此同時,「瓜分」中國的輿論也迅速在東西方各報流播,報刊上甚至開始流傳多種「瓜分」中國圖。一時間,中國被「瓜分」的陰影籠罩在有識者的心頭。《格致新報》刊發了一篇關於「瓜分」的問答,其中的「問」頗能反映時人的普遍心態。該文「問」道:「瓜分中國一說,始於中日失和之後,德人占膠以來,其說尤甚。竊以為憑空無稽之談,不足為信,然中外報章,言之鑿鑿,視為定論,小民不察,大為惶惑,不知能得其實情否?」中外報章言之鑿鑿、小民大為惶惑均為實情。俄佔旅大之後,時在北京準備會試的梁啟超、麥孟華等人,在上都察院的「呈稿」中如是說:「西人之覷我中國久矣,瓜分之圖,騰布宇內。特今俄割旅、大,英、法必不肯獨讓,法割滇、粵,英割長江,日割福建,眈眈逐逐,紛至疊來,二萬萬里之幅員,一旦可以立盡。皇上豈忍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天下,一朝瓦解而亡哉?又豈忍率土四萬萬之臣民,一朝而盡為奴隸哉?」痛憤之情溢於言表。正是在「瓜分」危機的刺激下,戊戌變法極速開展。但不幸的是,變法很快以政變的形式收場,清朝政局在復舊與排外的路上越陷越深,連籌備「善亡之策」的能力也已喪失,有識者認定,清朝之被「瓜分」指日可待。

1898年3月在上海創辦的《格致新報》
然而,意外的是,列強並沒有就此分割中國,政變後,孱弱不堪的清朝仍然維持着形式上的領土完整,儘管諸多主權已經喪失。這與膠州灣事件後譚、梁所認定的亡國滅種有所不同。列強遲遲沒有分割中國土地的表象甚至迷惑了不少國人,他們以為「日日言瓜分,而十餘年不睹瓜分之實事。今日瓜分之言,猶昔日之言也,吾始終不信有是事,則彼莠言亂政者無所行其計也」。列強侵略方式的改變與國人此種心理變化,引起了梁啟超的關注與思考。流亡日本的他在深入研究世界大勢的基礎上,率先對列強侵略方式的改變作出理論上的闡釋,提出「有形—無形瓜分」論。
梁啟超承認,列強確實沒有對中國進行領土分割,沒有實行「有形之瓜分」,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有可以抵拒瓜分之力」,更不意味着「列國之無瓜分之志也」。事實上,「以泰西各國之力,加於中國,如以千鈞之弩潰癰,苟其欲之,則何求而不得?」有瓜分之心、瓜分之力而沒有「瓜分」的原因,在於「各國互相猜忌、憚於開戰」,「譬如群虎同搏一羊,未及朵頤,而必有先受其斃者」,列強已熟慮及此,「相持不下,持均勢之策,相與暗中抵拒……故中國得以偃然癱卧於其間,歷有年所,以至於今日也」。列強間的均勢制衡雖然維持了中國形式上的完整,但卻開啟了瓜分中國的新方法——「無形之瓜分」。
通過比較列強在世界範圍內滅人國的歷史,梁啟超指出其方式有「有形之瓜分」與「無形之瓜分」之別:「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吾所言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儘管中國在將來仍有被「有形之瓜分」的禍患,但目前各國採取的則是「無形之瓜分」,即國雖未亡,但國權已經喪失。這是野蠻國滅人國與文明國滅人國的不同:「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奪其土然後奪其權焉;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奪其權不必奪其土焉,奪其實不必奪其名焉。故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今歐洲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故中國之精血,瓜分已盡,而我朝野上下,猶且囂囂然曰:西人無瓜分之事,無瓜分之志。」與昔日野蠻人滅人國的赤裸、暴虐相比,在「文明」的掩飾下,今日列強滅人國的方式更加隱蔽,更有欺騙性,以至於「我朝野上下」皆受蒙蔽,以為「西人無瓜分之志」。
分析甲午戰後各國侵略中國的種種手段,梁啟超總結出「無形之瓜分」的多種途徑,首先就是控制路權,「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鐵路所及之地,即為主權已失之地」。伴隨路權喪失的國權還有礦權、練兵權、用人權、財權等。一個國家在喪失了如此多之國權後,就如人的身體一樣,只剩下皮毛:「一國猶一身也……鐵路者,國之脈絡也;礦務者,國之骨節焉;財政者,國之肌肉也;兵者,國之手足也;港灣要地者,國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國之皮毛也。今者脈絡已被瓜分矣,骨節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僅餘外觀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軀,尚得謂之為完人也哉!」這裡,梁啟超觸及到列強「瓜分」中國最為致命的手段,即控制一國之鐵路權、礦務權、財政權、練兵權、港口要地的駐兵權,這與以往赤裸裸地分割其土地的做法截然不同,其隱蔽性更強,危害性更大,「故無形之瓜分者,不過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無形之瓜分,則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險最巧之處,而吾所以謂無形更慘於有形也」。「無形更慘於有形」包含了梁啟超警示國人的深刻用意,因為沒有了亡國滅種、分崩離析的慘烈,國人易於心生僥倖,放鬆警惕。
列強何以要「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者也?」梁啟超認為,除了列強間的均勢原則之外,還與國人的愛國心、團結力有關:「骨節、肌肉、脈絡、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則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萬萬同胞愛國之心,團結之力是也。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之間,系茲一發。」由於腹心不可得而瓜分,因此列強為了免去瓜分後統治的困難,放棄「有形之瓜分」轉而採取「無形之瓜分」。國人的愛國心、團結力不利於列強行瓜分之策,卻是中國救亡圖存的根本所在,「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人決不能因列強的「無形之瓜分」而放鬆警惕,應充分發揮各自的愛國心、團結力,以便實現民族的獨立。
至此,基於列強侵略方式的改變,梁啟超開始目光向下,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將中國的救亡之路寄託於四萬萬國人身上。這一思路也成為此後一段時間內梁啟超思想的主調。在相近時間裏刊出的《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梁啟超更是明確將中國的前途與中國國民聯繫在一起,他說:「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之,猶將存也。」國民能否自存成為中國存亡的關鍵。這一思路直接促成了梁啟超「新民」的思想轉變。

1900年,法國Le Petit Journal畫報增刊彩色石印畫,描繪出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
「無形之瓜分」論是梁啟超對戊戌政變後列強侵略方式的最新概括,既是在警醒國人,更是在尋找出路。將中國的出路寄託於四萬萬國民正是梁啟超為應對列強「無形之瓜分」而提出的全新思路。庚子事變後,列強侵略方式的此種變化表現得更加清晰,梁啟超的認識也更進一步,先後提出「保全即瓜分」「滅國新法」等,作為「無形之瓜分」論的補充。
庚子事變徹底暴露了清朝的腐敗、無能,但卻進一步堅定了列強「無形之瓜分」「保全」中國的決心。這絕非列強愛中國的結果,而是列強希望保持中國虛弱之現狀,通過扶植清政府,控制其路權、礦權、財權乃至練兵權、用人權,達到「以中國人而自凌中國人、自製中國人,則相與俯首帖耳」的效果。對此,梁啟超分析說:「皮相者流,孰不謂瓜分之議,將於今實行乎?而豈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環球政治家之論,反為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於報紙中。」箇中原因在於歐人深知「以瓜分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為瓜分」。如果今日實行瓜分,「吾國民於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何如「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更能收買人心,「於是乎中國乃為歐洲之中國,中國人亦隨而為歐洲之國民」。與瓜分相比,保全更具有欺騙性。
梁啟超將列強這種不言瓜分而言保全的滅國之法稱為「滅國新法」。所謂「新法」是相對於舊法而言的:「昔者以國為一人一家之國,故滅國者必虜其君焉,瀦其宮焉,毀其宗廟焉,遷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滅而國滅。」而今則代之以「新法」,「苟真欲滅人國者,必滅其全國,而不與一人一家為難」,「不寧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滅國之手段」。在列強的「滅國新法」中,專制政府不是被滅的對象,而是列強用來「助其滅國之手段」。他進一步比較滅國新、舊法的手段、表現與特徵,指出:「故昔之滅人國也,以撻之伐之者滅之;今之滅人國也,以噢之咻之者滅之。」故而,昔之滅人國者「驟」「顯」「如狼虎」,「使人知之而備之」;而今之滅人國者「漸」「微」「如狐狸」,「使人親之而引之」。其手段,「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滅國「新法」與「舊法」的區別,也正是「有形之瓜分」與「無形之瓜分」的不同。
梁啟超的這一認識是在觀察、研究世界各弱小國家被滅歷史之後得出來的。他一一列舉了列強滅亡埃及、波蘭、印度、菲律賓的手段、途徑,指出通商、放債、練兵、鐵路、顧問乃至挑起內亂,都是列強「滅國新法」中的利器。而今中國已是列強的囊中之物,必然要用這些利器對待中國,其結果必將是:其一,「二十行省之路盡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其二,「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猶假強盜以利刃」。其三,「無如商權、工權、政權既全握於他人之手,此後富源愈開,而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於彼族」。其四,奴隸之奴隸教育將遍及全國。這裡梁啟超對列強「滅國新法」的手段、本質與危害揭示得淋漓盡致。
從「有形之瓜分」到「無形之瓜分」再到「保全即瓜分」「滅國新法」,梁啟超對列強侵略方式、手段的觀察無疑是準確的,已經觸及到列強殖民擴張的本質特徵,即保留傀儡政府,用經濟、金融、鐵路、教育等手段而不是分割土地的方式控制殖民地的主權。這是中國知識界對歐美列強推行多年的海外侵略擴張行為的理論闡釋,系統且深刻,與歐美知識界帝國主義論的建構幾乎同步,但由於立場不同,雙方面對列強擴張的同一實踐卻作出了全然不同的理論分析。不同於為列強侵略擴張正名的帝國主義論,梁啟超站在被侵略、被瓜分民族的立場上,對列強擴張的侵略本質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充分揭示了「無形之瓜分」與「滅國新法」的表現、特徵與危害,戳穿其隱蔽性,意在警醒國人,為中國尋找一條生路。正是基於對列強侵略方式轉變的深刻認知,梁啟超才調整思路,目光下移,將中國的出路寄託於四萬萬國民,這是一條不同於「保皇」的新路。國民、「新民」遂成為此後梁啟超思想的核心所在。
梁啟超的「瓜分」話語,深刻影響了清末十年的輿論,翻閱當時的各大中文報刊,「無形之瓜分」與「保全即瓜分」的論說比比皆是。馮斯欒在《清議報》發文,剖析列強的對華政策,他說:「東西報紙議論紛騰,總不出保全、瓜分之二者。無知之輩,聞保全則喜,聞瓜分則憂,對唱瓜分之國則怨,對唱保全之國則諂……嗚呼,實不思耳。其保全之與瓜分又何別焉?」基於此種認識,他提出的對策與梁啟超如出一轍,即:「今欲破保全瓜分之問題,莫善於我國民提出獨立之問題。」其實,不僅《清議報》的論說深深打上樑啟超「瓜分」論話語的印記,包括革命派報刊在內的諸多輿論都深受其影響。《湖北學生界》談及列強庚子後「保全領土、開放門戶」的侵略政策時稱:「今外人之對我中國,曰勢力範圍,曰特別利益,為各國獨營之政策;曰國債,曰教務,曰商務,曰開礦築路,曰內河航行,為各國公同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輸入文明……無形之瓜分更慘於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萬萬同胞於此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政策之下。」從各種「瓜分」手段到「無形更慘於有形」,這些話語都深深打上樑啟超的烙印!

1903年1月在日本東京創辦的《湖北學生界》
「無形之瓜分」—「國民獨立」,這是梁啟超為應對列強侵略進行的理論思考,不同於西方的帝國主義話語,卻已經觸及到列強殖民擴張的本質內涵,故而成為中國知識界認識、理解西方帝國主義論的思想前提。
二、「帝國主義」的理論輸入
正當梁啟超以「有形—無形瓜分」論對列強的侵略活動作出理論分析之際,產生於歐美的帝國主義論也開始在全球蔓延。身處日本的梁啟超很快關注到這一與中國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理論,並迅速通過《清議報》將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輸入國內,這也成為其認識進而闡釋帝國主義論的重要知識來源。
1899年6月,《清議報》刊載一篇來自英報的譯文,題為《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單從譯文題目,我們看不出該文與帝國主義論的關係,但從內容可見,這的確是一篇宣揚西方「帝國主義」論的文章,如文中認為歐洲「二十餘年來,產物饒溢,苦銷路之停滯,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爭求世界新市場」。正是在生產過剩的驅動下,各國向亞、非兩洲「曠大未辟之方域,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而時至19世紀末,列強在完成了對非洲的掠奪之後,集體轉向亞洲,把瓜分中國作為頭等大事。「伯林、伯德堡、巴黎、華盛頓、倫敦,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稱為新綱領新格訓。」其掠奪手段,「或曰佔領,或曰勢力範圍,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雖異,而其實則皆滅人之國以自廣耳……列強亦執互益協商,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蓋不約而同矣」。這裡對列強分割中國手段的認識與梁啟超沒有太大的區別,不同的是,被梁啟超等人視為狐行、強盜之行的列強,在此卻被賦予了文明、正義的價值評判,其聲言:「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而其事決非可恥也。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脫從來腐敗之苛政,免抑壓之苦海,得統治於公平正義之政,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並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這就是西方的帝國主義論,是赤裸裸的侵略有理論,其中的生產過剩、尋求市場、武力競爭、公平正義等都是西方帝國主義話語中的關鍵詞。
該文是梁啟超等人在《清議報》輸入西方帝國主義論之始,對文中的「帝國主義」概念,譯者注釋道:「帝國主義者,謂專以開疆拓土、擴張己之國勢為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但隨後譯者對該文的解讀並沒有太多涉及「帝國主義」,而是在「保全即瓜分」的思路下進行的,附言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對於譯文中標榜的分割支那是為了中國四億人脫苛政、免苦海,譯者在列舉了列強強佔旅順、大連、九龍等地時擄掠婦女、炮擊人民、燒毀村鎮、肆殺搶掠的野蠻行為後,抨擊道:「雖古之盜跖,不足以比其殘虐。非洲野蠻之族,不足以例其瘏痛,猶自稱曰文明,將誰欺耶?抑謂中國無人,將可盡欺耶?」站在被瓜分民族的立場上,譯者直斥列強的行徑為「盜跖」「野蠻」,一針見血,戳穿了自視為「文明」「公平正義」之西方帝國主義論的欺騙性及其本質。譯者進一步分析了列強瓜分中國之法非直接瓜分,而是藉助滿洲施行,「列國之欲瓜分中國,而慮其民之難治也,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而滿洲又「恐有內訌之禍,又借外人鐵血之威以殄滅之」。因此,中國的出路,惟有「自立」之一策,「同胞君子,其先合群以聯成自立之團體,而後可脫外人之縛軛」,不然,「彼奴隸屈辱於碧眼紅髯兒之下,安有窮期哉?」該文沒有註明譯者,但從譯者附言的內容來看,其對列強侵略的分析與梁啟超的思想一脈相承。可見,此時《清議報》對列強侵略擴張的解讀仍然延續「無形之瓜分」的思路,尚沒有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論的影響。這種立足於中國,對列強瓜分中國高度警惕與強烈譴責的態度自然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理論有着本質的區別。
《清議報》真正系統輸入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則是兩年之後了。1901年11月,該報刊出日報譯文《帝國主義》,譯自日本的《國民新聞》,作者署名為「獨醒居士」。據石川禎浩的研究,該文是作者依據美國芮恩施和基丁格斯的帝國主義理論改寫而來的,且與浮田和民發表於《東亞同文會》第19期(1901年6月)的《帝國主義》「基調相同,甚或即可視為同出一人之手」。不過,他認為「獨醒居士」並非浮田和民。「獨醒居士」依據當時美國的帝國主義論改寫的文章,觀點又與浮田相同,說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直接來源於歐美。《清議報》選擇此文進行翻譯,正說明它具有代表性,不僅反映了歐美帝國主義論的核心內容,而且代表了日本帝國主義論的一般觀點。
該譯文在梳理歐美帝國主義政策、海外擴張歷史的基礎上,對帝國主義產生的原因、表現、特徵及貢獻進行了理論歸納與總結。對照《清議報》的《帝國主義》與芮恩施的《十九世紀末世界政治》,可見兩者在內容上高度一致。其一,在追述帝國主義的起源時,該文即採納了芮恩施的「民族帝國主義」說,認為20世紀之帝國主義與以往不同,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而是「民族膨脹」「國家膨脹」的結果,「不伴民族之膨脹,徒以征服侵略之不可以奠國家於磐石之安也」。其二,對於帝國主義的特點,該文認為「劇烈競爭」是「帝國主義時代之一大特色」,且「其競爭之標準大為高尚」。這也與芮恩施的認識相一致。其三,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事業的關係,該文認為二者決非同一,但殖民確為帝國主義的重要手段:「列強為將來得領土之故,必儘力於殖民政策,國民生息之地,必向未開之地而膨脹,以擴張本國之活動舞台。」芮恩施同樣強調「帝國擴張的最激進方法是直接奪取領土或控制保護領土」。其四,對於帝國主義的前途,該文認為:「世界之統合,固有兩法,即一者以強大之力,征服全世界,統一於己權力之下。一者數多強大之國民,相併而存立,不互相侵略,不必相服從,同心合意,以相團結,為協同之生活,協同之進步,而組織世界大聯邦。」這與芮恩施所說:「世界統一可以通過兩種制度中的任何一種來實現:一種是聯邦制,逐漸發展為緊密的團結;另一種是無限制的競爭,最後由一個大國佔優勢,它將吸收和同化所有其他國家。」如出一轍。其五,為帝國主義辯護,該文對於當時流行的批評帝國主義的聲音,加以反駁:「以帝國主義為全無道德、人道之仇、平和之敵,弱肉強食之主義,是知其一不知其他之論也。」因為,人多地少,移民人口稀薄之地;為發達國內工商業、改進國民經濟生活而求市場於國外,謀利益之擴張,都是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而非無道德之事。同時,於世界各地教育訓練野蠻蒙昧之民,是「先進國之責任也」。隨之而來的文明國利用未開發地之資源,造福人類,同樣是「先進國之義務」。未開化民族被吞併同化也不違背道德,因為「彼等既屬劣敗之人種,無憂勝者助力,亦終歸滅亡」。如果起而反抗,征服野蠻更是「不得已之事」。為帝國主義辯護也是芮恩施帝國主義論的重要內容,但該文比芮恩施的言論更為露骨,也比當時日本的其他思想家如高田早苗、浮田和民等人公開發表的倡導帝國主義的言論直白得多,這在尚存在許多批評帝國主義聲音的日本是罕見的。這或許是作者在日本發表時隱去真名的原因,以至於學界至今尚無法弄清「獨醒居士」究竟是誰。《清議報》在譯介此文時,未署作者,大概是不知道「獨醒居士」的真名,故付闕如。
此外,作者還逐一分析了英法德俄美殖民方法及殖民思想的特點,認為這與各國自身的歷史習慣人種密切相關,即如德國「最能發揮帝國主義之特性,及能代表近來世界之歷史者」,「政府或自鐵道政略或自殖民政略或自商業政略,傾全力而求達其帝國主義之目的」。這些也與芮恩施的觀點大體一致。
《清議報》連續於第97—100冊刊發了這篇《帝國主義》,後又收入《清議報全編》第9卷。1902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添加「譯日本浮田和民原著」及「出洋學生編輯所編」字樣。是年1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且不論《清議報》的傳播,單是單行本一年內就再版,也足以說明其影響之大。不僅如此,芮恩施的英文原著也被梁啟超的同門羅普譯成中文,由上海廣智書局發行。這是芮恩施帝國主義論在中國的一次大規模傳播,成為知識界認識帝國主義最早的思想資源。

1898年12月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清議報》
更重要的是,透過此文,國人不僅看到歐美帝國主義的勃勃野心,而且強烈感受到日本人擁抱、追逐帝國主義的迫切心態。1902年初,梁啟超曾描述日本人追逐帝國主義的盛況:「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艷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面對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理論與實踐,梁啟超憂心忡忡,他深知:「今日茫茫大地,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從民族生存的需要出發,作為當時最具世界眼光的中國人,梁啟超不得不對歐美日本盛行的帝國主義論進行研究,作出應對。他著書立說,闡釋自己的帝國主義理論,包括對歐美各國帝國主義起因、特點、表現及中國在帝國主義擴張中的位置與出路等的理解,帝國主義論遂成為梁啟超分析世界大勢和中國出路的重要工具,但他始終沒有全盤接受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而是在吸收其部分概念、語彙的基礎上,將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置於「無形之瓜分」論的框架中進行解讀。
三、「帝國主義」的理論闡釋
早在1899年10月,梁啟超刊發於《清議報》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一文,已經在嘗試用帝國主義的概念解釋世界大勢了。文中雖然沒有出現「帝國主義」字樣,但其用以分析列強擴張的概念,諸如國民競爭、生產過度、尋找銷售之地、膨脹等,顯示出帝國主義話語的影響。
此後的兩年中,日本的帝國主義論甚囂塵上。為應對全球盛行的帝國主義潮流,梁啟超先後完成了《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等一系列著述,將帝國主義論與中國的民族出路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當然,梁啟超之外,還有不少身處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也都關注帝國主義論,如馮斯欒就曾撰寫《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一文,論述帝國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其本質。但梁啟超無疑是當時針對帝國主義論關注最早、撰述最多、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其中《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對帝國主義理論的闡釋最為系統深入。
對於該文的思想來源,梁啟超在「著者識」中說:「篇中取材多本于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而參以己見,引申發明之,不敢略美。」靈綬氏即芮恩施,潔丁氏即基丁格斯,這與上述「獨醒居士」的《帝國主義》一文來源相同。石川禎浩認為,梁啟超實際上沒有直接參考靈綬氏與潔丁氏的著作,而是間接參考了日本「獨醒居士」的《帝國主義》。這一說法並不可靠,如前所述,芮恩施的英文原著被梁啟超的同門羅普譯成中文,由上海廣智書局發行。鑒於梁啟超與羅普在日本共同讀書、著述的事實,我們可以斷定,梁啟超肯定從羅普處參考了芮恩施的著作,而不是間接參考「獨醒居士」的《帝國主義》。因此,梁啟超該文是綜合參考了當時歐美與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帝國主義論著。但在「參以己見」之後,其帝國主義論已不同於歐美日本,是站在民族立場上的中國人的帝國主義認知,他一方面向國人介紹了日本歐美帝國主義論的主要觀點,一方面站在中國民族生存的立場上對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加以批判,進而提出中國的民族出路,與歐美日本人的帝國主義論差距巨大。
首先,梁啟超接受了歐美帝國主義論中的「民族帝國主義」說,認為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膨脹、競爭、擴張的必然結果。他多次強調說:「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台也。」歐美民族主義發達的結果是民族競爭與對外擴張,「夫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於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於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這種內力包括人口幾何級數上漲、生產過剩亟須開闢銷售市場等,這正是帝國主義產生的原因,也是帝國主義論者的共識。梁啟超將帝國主義置於世界發展大勢中進行評判,既看到了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也看到了帝國主義氣勢磅礴、不可阻擋的一面。
其次,梁啟超比較了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不同動力,認為進化論為帝國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他說:民族主義的原動力為盧梭的民約論,而帝國主義之原動力為斯賓塞的進化論,主張天下無天賦之權,惟有強者之權利。在優勝劣敗、強權即公理的邏輯之下,帝國主義大行其道:「雖翦滅劣者弱者,而不能謂為無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則然也,我雖不翦滅之,而彼劣者弱者終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視為蠻暴之舉動,今則以為文明之常規。」這是歐美帝國主義論者的邏輯,而非梁啟超的邏輯。其結果是「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為天經地義之公德,此近世帝國主義成立之原因也」。梁啟超無疑是進化論的忠實信徒,承認在天演公理之下帝國主義的發生不可避免,但必然並不等於正義,當帝國主義論者用進化論公然為其侵略辯護時,梁啟超感到不滿。他一一列舉了帝國主義論者的辯護話語,稱:「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浥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寧惟是,彼等明目張胆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寧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為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為放棄責任也。」這是帝國主義的強權邏輯、侵略有理論。從「此其口實之大端」「明目張胆」等用詞可見,梁啟超並不認同列強的這些歪理。而西方列強正是依據這種邏輯,對外擴張,即便是美國,也放棄其遵守多年的門羅主義,轉向帝國主義:「向守們(門)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非律賓。」帝國主義已成為風靡世界的風潮,「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飈然訇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強權即公理」不只是理論,更是現實,對此,梁啟超除了勇敢面對外,別無選擇。
基於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不同原理,梁啟超對兩者作出價值評判,認為:「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梁啟超看到了民族主義正麵價值,它給世界各國帶來的是獨立,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互不侵犯,而又各自繁榮。而對於帝國主義,梁啟超則認為:「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依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梁啟超的這一分析涉及到帝國主義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其對內是有效的,能確立法治,以保民族全體之利益;而對外則必將導致「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這也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可見,梁啟超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認識是清晰的。但也必須看到,梁啟超對帝國主義擴張給本民族帶來的巨大利益艷羨不已,甚至渴望中國也能具有對外擴張的實力,不惜將中國歷史上的張騫、班超視為殖民人物。他一方面指出帝國主義對其他民族的侵略本質,另一方面又羨慕帝國主義給本民族帶來的巨大利益,兩者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正彰顯了梁啟超內心的矛盾。這說明,此時的梁啟超除了遵循進化論主導下的西方社會發展路徑之外,尚無法找到其他出路。這是梁啟超的局限,也是時代的局限。
然而,梁啟超關注帝國主義的根本目的在於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因為帝國主義的競爭場域,早已轉移到了中國,中國如何在帝國主義的爭奪中求得生存,這恰恰是歐美與日本的帝國主義論漠視的問題。因此,面對帝國主義的勢不可擋,梁啟超沒有日本人那種羨慕、嚮往、坐而言起而行的心態,而是充滿了恐懼與憂慮。當英日結盟、時人為黃白兩種人握手而歡呼時,梁啟超大聲疾呼:「其結果若何?豈非此新世界中民族競爭之大勢,全移於東方,全移於東方之中國,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耶!而立於此舞台之中心者,其自處當何如矣?」作為舞台中心的中國,如何應對帝國主義的侵噬,這是梁啟超關注帝國主義及其理論的終極目的,也是梁啟超的帝國主義論與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論的本質不同。
為了探尋中國的民族出路,梁啟超深入剖析了帝國主義侵噬殖民地之手段、表現、特徵。他指出:「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彼列國之所以相對者姑勿論,至其所施於中國者,則以殖民政略為本營,以鐵路政略為游擊隊,以傳教政略為偵探隊,而一以工商政略為中堅也。」梁啟超列舉事實,對列強在中國實行的殖民政略、鐵路政略、傳教政略、工商政略一一作了分析,說明這就是列強「無形之瓜分」,他深知:「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無形之瓜分則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萬萬國民陷於九淵而莫能救也。」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在進化論的掩護下為文明—野蠻鏈條中的征服與侵略辯護,而梁啟超雖同樣承認進化論,但將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視為滅國之「狐行」,認為其比野蠻人更殘忍,「利用政府疆吏之權,以政府疆吏為彼奴隸,而吾民為其奴隸之奴隸」。
而與殖民、鐵路、傳教政略等擴張手段相比,列強之工商政略更為可怕,僅此一項就可以置中國於死地,因為「二十世紀之世界,雄於平準界者則為強國,嗇於平準界者則為弱國,絕於平準界者則為不國」。所謂平準界就是經濟界,相較於歐洲經濟界資本的擴張,中國之資本根本不值一提,而這種不對等因為歐美資本得到本國及殖民地的政策保護而加劇。作為中國人,「本國人非惟不能得特別優等之利益而已,而與外國人相較,此等利益反為外人所特有」。在「得寸入尺、獲隴望蜀者,眈眈相逼乎前,而政府之懾狐威者,今日許以寸,明日予以尺」的惡劣環境之中,中國之資本必然被制以死命,「更後十年,又當若何?若是乎,吾中國人之真無以自存也」。面對美國托拉斯的世界擴張,梁啟超充滿恐懼,表示:「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於生計上能佔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即興亡亦系此焉。」這與梁啟超所說的「無形之瓜分」論一脈相承。經濟手段成為帝國主義的「滅國新法」,梁啟超大聲呼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不及一紀,而十八省、千百州縣之地,勢必全為歐美資本家之領域……此非過激之言也,二十世紀之人類,苟不能為資本家,即不得不為勞力者,蓋平準界之大勢所必然也。夫事勢至於若彼,則我民族其無噍類矣。」
面對帝國主義的擴張及其理論,處於帝國主義擴張最核心位置的中國究竟該如何應對?梁啟超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認為:「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只有建成民族主義的國家,才談得上與各國競爭。因為,平準界的競爭,從本質上來看是「由民族之膨脹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脹,罔不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來。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於平準界能稱雄者」。而中國只要建成民族主義的國家,前途自然無量,「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建立民族國家遂成為梁啟超為中國開出的應對帝國主義的藥方。此一主張,梁啟超反覆言之,《新民說》開篇有言:「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不過,民族主義只是梁啟超為應對帝國主義提出的最初方案。

梁啟超《新民說·敘論》(刊於《新民叢報》第1卷第1期)
而後,由於「新民」是一個艱巨且長期的任務,而帝國主義的「瓜分」威脅卻迫在眉睫,兩者之間的緊張,使得梁啟超產生中國國民素質低下的焦慮,加之民族主義被革命派用以號召「排滿「革命,他遂放棄民族主義,轉而主張國家主義,其表示:「今日欲救中國,惟有昌國家主義,其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皆當詘於國家主義之下。」但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的轉變,只是其對內主張的調整,是應對帝國主義策略的轉變,其對帝國主義性質及其侵略手段的認知則一如既往。而且,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國家主義,梁啟超用以應對帝國主義的方略都來自於歐美,其核心力量都是現代國民。
分析至此可見,歐美與日本的帝國主義理論經由《清議報》介紹到中國,但梁啟超對帝國主義的理論闡釋則延續了此前的「無形之瓜分」論,立足於民族的立場,在借鑒歐美日本學界帝國主義術語的同時,摒棄了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論中正義化甚至美化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內容,充分警惕並揭示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為中國探尋出一條生存之路——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隨後,梁啟超將其前後兩篇思考列強侵略的文章——《滅國新法》《論民族競爭之大勢》結集出版,名為《現今世界大勢論》,這正反映出梁啟超理論思考的連續性。他在「敘」中明言,他的這些著述「意不在客觀之世界,而在主觀之中國人也」。這也正是梁啟超理論思考的根本所在。
梁啟超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思考是中國思想界的代表,無論從撰文數量還是影響力,他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帝國主義理論最主要的闡發者。他對於世界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大勢及其手段、特徵的認知與中國應對之道的論述,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分析國內外問題的基本話語,帝國主義的經濟膨脹、民族膨脹、軍備競爭、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優勝劣敗等新詞彙,被中國知識界反覆使用,成為論證世界大勢與中國時局的高頻詞。一時間,國內乃至留日知識人所辦報刊都競相談論帝國主義。對於梁啟超思想在當時中國輿論界之影響,黃遵憲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而他的「帝國主義」論即是影響時論的思想之一。如雨塵子在《新民叢報》刊發文章,討論帝國主義,稱:「近日論者謂,十九世紀民族主義之大發達,今日帝國主義亦所胚胎。夫民族主義者,前世紀政治之競爭,其大半皆由此。帝國主義即民族膨脹之結果也。」他進一步闡釋了民族主義膨脹的具體內涵,與梁啟超所說的人口增加、生產過剩並無二致。《浙江潮》刊發多篇論文,論及帝國主義問題,在時間上晚於梁啟超的相關論述,且在內容上也沒有超出梁啟超的論述範疇,即如《國魂篇》一文直接將民族主義視為帝國主義之父,稱:「今日之世界,則孰不知曰帝國主義哉!帝國主義哉!雖然,亦知其發達之由乎?帝國主義者,民族主義為其父,而經濟膨脹之風潮則其母也。」當然,也必須看到,由於立憲與革命的立場不同,儘管革命派的報刊輿論也提出以「民族主義」應對「帝國主義」,但其民族主義的內涵與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全然不同,革命派的民族主義首先是對內的「排滿」革命。這也是促使梁啟超思想從民族主義轉向國家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民叢報》
結語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國家紛紛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迅速向非洲和亞洲擴張,中國很快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的中心。面對列強的瘋狂侵略,作為中國當時最具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梁啟超率先對其作出理論上的分析。
甲午戰後特別是膠州灣事件後,面對列強的瓜分狂潮,梁啟超認定列強很快將對中國實行「有形之瓜分」,中國滅亡不可避免,因此在湖南積极參与變法,以備「亡後之事」。但隨着時局的演進,列強並沒有直接「瓜分」中國,而是通過扶植清政府,間接控制中國的主權。而不明就裡的國人因此放鬆警惕,以為中國可以不亡。為了警醒國人,梁啟超提出「無形之瓜分」論,對列強擴張的侵略本質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充分揭示了「無形之瓜分」與「滅國新法」的表現、特徵與危害,戳穿其隱蔽性,意在警醒國人,為中國尋找一條生路。正是基於對列強侵略方式轉變的深刻認知,梁啟超調整思路,目光下移,將中國的出路寄託於四萬萬國民,這是一條不同於「保皇」的新路。此後,國民遂成為梁啟超思想的核心內容。
梁啟超應對列強侵略的理論思考,不同於西方的帝國主義話語,但它已經觸及到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本質內涵,故而成為中國知識界認識、理解西方帝國主義論的思想前提。當歐美日本的帝國主義論傳來,梁啟超等人迅速作出回應,將其輸入國內,並站在中國的民族立場上,書寫出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解,並提出應對之道。毋庸諱言,梁啟超對帝國主義的認知深受帝國主義話語的影響,西方理論中的民族帝國主義、民族膨脹、經濟膨脹、生產過剩、銷售市場等新詞彙也成為梁啟超分析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重要工具。但也必須看到,梁啟超對帝國主義的思考則延續了此前的「無形之瓜分」論,立足於民族的立場,在借鑒歐美日本學界相關帝國主義敘述的同時,摒棄了歐美與日本帝國主義論中正義化甚至美化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內容,充分警惕並揭示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視之為「無形之瓜分」,比之為「狐行」,並特彆強調其經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危害,進而為中國探尋出一條生存之路,即依靠國民、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其後,由於對國民素質低下的過度憂慮及對排滿革命的畏懼,梁啟超放棄民族主義,轉而主張國家主義,但這只是其對內主張的調整,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知並沒有改變,這正體現了梁啟超相關思考的連續性。
梁啟超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思考是中國思想界的代表,他對於世界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大勢及其手段、特徵的認知與中國應對之道的闡發,構成了此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分析國際局勢與解決國內問題的基本話語,對當時的社會輿論產生了深刻影響。當然,梁啟超的帝國主義論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這集中體現在他雖然認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性,但又反覆強調帝國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帝國主義的罪惡;他將歐美社會從主義到民族帝國主義的發展視為人類社會的必由之路,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模板,這也體現出梁啟超思想的局限性。
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