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八月十八日清晨, 大明王朝的金殿內傳來了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哭聲。
這是大明王朝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朝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朝會將決定着大明王朝的命運。
朝會的主題很簡單:是逃還是戰?

一、
一個月前,明朝接到情報:也先率領瓦剌軍隊來犯。
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煽惑下,決定率軍親征。七月十六日,英宗朱祁鎮命弟弟朱祁鈺留守北京,親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企圖重演其曾祖朱棣橫掃大漠的雄風。
八月十五日,明軍在土木堡遭到瓦剌軍的進攻,導致了一場大敗。英國公張輔以下百餘名高官皆戰死,明英宗本人則成了瓦剌人的俘虜。
將軍樊忠於亂軍中撞見罪魁禍首王振後,掄起鐵鎚將王振的腦袋砸了個稀爛,隨後亦戰死。這場大敗,史稱「土木之變」。

當皇帝朱祁鎮被俘、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回京城後,整個大明陷入了驚恐之中。孫太后和錢皇后趕緊搜集宮中所有金銀珠寶,試圖贖回被俘的皇帝。負責監國的英宗的弟弟朱祁珏緊急召開朝會,商討對策。
朝會上,大臣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個個只會痛哭流涕,無計可施。
大家都清楚,整個朝廷的精銳都葬送在了土木堡,京師只剩下一點老弱殘兵,況且連皇帝都被人俘虜,明軍可以說士氣低落到了極點,又如何抵擋鋒芒正銳的也先大軍?
面對嚴峻的形勢,不少大臣都打好了如意算盤:北京是保不住了,不如逃往副都南京,雖然這麼做會丟掉北方半壁江山,但大家都安全,也不影響繼續做官,享受美好生活。

要是再不跑,等被也先包圍了,那可就晚了!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第一次主持朝會的朱祁鈺也是手足無措。當他向群眾臣問計時,許多官員只會嚎啕大哭,哪裡提得出來什麼建議?
大臣們哭了好久之後,翰林院侍講徐珵終於發言了。他告訴朱祁鈺:「我夜觀天象,發現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遷才可以保住大明氣數!」
徐鋥的話,正中了大多數大臣的下懷,很多大臣紛紛點頭。就在此時,人群中突然響起一聲獅子吼般的怒喝:「誰再提南遷的,應該馬上推出斬首!」

眾人扭頭一看,發出這聲怒吼的,正是兵部左侍郎于謙。只見於謙走到殿中高聲說道:「京師乃天下根本,若一動則大勢必去,難道我們還要重蹈南宋滅亡的覆轍嗎?」
于謙的怒吼,震醒了一些尚有良知的官員。王直、商輅、王竑等大臣紛紛站出來支持于謙的意見,讓猶豫不決的朱祁珏終於堅定了信心:要想不亡國,只有齊力同心抵抗也先這一條路可選了。
於是朱祁珏下令升于謙為代理兵部尚書,由他全權負責北京保衛戰。

二、
明洪武三十一年,于謙生於杭州一個官宦世家。少年時的于謙讀書非常用功,於四書五經之外還喜歡研讀兵法,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當成自己的偶像,立誓長大後要做一個像文天祥那樣的人。
于謙八歲時,有一天穿着紅色衣服,騎着一匹黑色小馬路過一間寺廟前。廟裡一位老和尚覺得這個孩子很有趣,於是吟了一個上聯戲弄于謙:「紅孩兒,騎黑馬遊街。」
于謙卻挺了挺胸,高聲答道:「赤帝子,斬白蛇當道!」老和尚見這個孩子彈指間便對上了如此工整又如此有氣勢的下聯,不禁嘆道:「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會成為拯救天下的宰相啊!」

永樂十九年,于謙考取進士,從此踏上仕途。上任之時,于謙口吟一詩拜別家人:「拔劍舞中庭,浩歌振林巒;丈夫意如此,不學腐儒酸!」
于謙是幸運的,因為當時掌權的是楊士奇和楊榮。楊士奇十分賞識于謙,斷定他「是難遇之奇才,將來必成棟樑!」
正是有了楊士奇和楊榮的賞識,于謙的仕途還算平坦。「土木之變」發生前,他已坐上了兵部侍郎的位置,成為一名高級幹部。
在這天的這場朝會上,面對即將到來的瓦剌士兵,面對城中驚慌失措的老百姓,面對皇帝被俘、明軍精銳盡失、士氣低落的困難,面對徐珵之流的「逃跑派」,于謙想起了自己的那首《石灰吟》,想起了自己「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抱負,面對一盤看上去解不開的死棋,于謙還是邁出了勇敢的一步:國家興亡,我來擔當!

三、
公元1449年(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率數萬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列陣於西直門外。距也先數百米外的北京城頭,于謙正率領京師軍民嚴陣以待。一切都在表明,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戰鬥打響前,也先派人對着城牆上的明軍高喊:「大明皇帝在此,你們還不放下武器,打開城門迎接?」
也先的這一招十分毒辣,說白了就是他想用俘虜來的明英宗,兵不血刃地賺開北京城門。讓他沒想到的是,于謙早就識破了他這一招,並提前做好了應對之策。

明英宗當了俘虜後,于謙急切感到朝廷必須擁立一個名正言順的皇帝,才能安定民心、穩定政局,才能粉碎瓦刺挾持明英宗,要挾大明的陰謀。於是于謙向孫太后提出國不可一日無君,請太后在「國勢危殆,人心洶湧」之際立朱祁珏為帝,以安人心。
于謙知道這種做法也許會在未來給自己帶來危險,但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他無暇考慮自己的安危。
在於謙的力諫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珏即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是為明代宗。這一重要舉措結束了大明沒有皇帝的局面,粉碎了也先試圖利用朱祁鎮要挾明朝的陰謀,贏得政治上的主動。

雖然于謙破解了也先的陰謀,但北京城的形勢仍然十分危急。
土木堡一戰,讓明朝精銳盡失,留在北京的只有幾萬老弱殘兵,城裡連像樣的馬匹都不多了。這點人馬,顯然無法抵擋也先。於是于謙在也先來到之前,便下令大明內所有可調之兵全部緊急開赴京師,終於搶在也先前面湊到了近十萬人。
也先並不知道這些情況,他想當然地認為北京只剩下了一個空城,只要自己下令進攻,分分鐘便可拿下。在利用明英宗要挾大明的陰謀失敗後,也先城決定在西直門發起進攻。

剛剛在土木堡取得大勝的瓦剌士兵,也沒有把明軍放在眼裡。隨着也先一聲令下,數千名瓦剌士兵發出一聲吶喊,朝西直門沖了過來 。
西直門守將劉聚、高禮、毛福壽也抽出腰刀,大呼「殺敵」,率領明軍向瓦剌兵衝去。
瓦剌兵根本沒有想到,明軍的抵抗會如此英雄。甫一接觸,輕敵的瓦剌軍被明軍一個衝鋒,斬殺了數百人,余者四散奔逃。
也先怒了。他原本以為不堪一擊的明軍,卻讓他的先鋒全軍覆沒。他決心調整策略,將進攻的重點放在北京城北面的德勝門。

于謙也想到了這一點。他意識到德勝門正對着瓦剌人,必然會是對方進攻的重點。因此在劃分作戰任務時,將保衛德勝門的艱巨任務留給了自己。
戰前,于謙下了一道命令 :「戰端一開,即當死戰。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同時他還命令錦衣衛在城中巡查,看見不參戰的士兵格殺勿論。
見於謙都有這樣的血性膽魄,將士們士氣大振,紛紛表示願聽從於謙的指揮,與北京城共存亡。
戰鬥打響了。也先的弟弟博羅茂洛海率領一萬精銳騎兵,朝德勝門沖了過來。但瓦剌人並不知道,于謙早就做好了準備,將明朝最有戰鬥力的神機營埋伏在了德勝門外的民居中(「設伏空舍中」)。

沖在最前面的博羅茂洛海,幾乎能看清楚站在德勝門上于謙的樣子了。他狂笑着舞着馬刀,腦海里似乎看到這樣的畫面:德勝門被攻陷,明軍全部成為自己的刀下之鬼!
就在這時,槍響了。槍聲來自神機營,他們以民房為據點,從各個方向射擊瓦剌騎兵,瓦剌騎兵成了神機營的活靶子,很多人被當場擊斃。博羅茂洛海本人也死在了神機營的槍下,一萬騎兵幾乎被全殲。

遭遇慘敗的也先不肯放棄,又轉攻西直門、彰義門,但全部失利。在這些天中,于謙每天衣不解帶地來往於北京各個城門之間,不顧自己的安危,鼓勵士兵們奮勇殺敵。士兵們見主帥如此捨生忘死,士氣大振,將北京城守衛得如同鐵桶一般。
相持了五天後,也先見討不到什麼便宜,用明英宗要挾明朝的陰謀又無法實現,再加上打探到各路勤王軍正在朝北京方向疾進,怕被斷了退路的也先只得挾持英宗向北撤退。至此,北京保衛戰結束。

四、
要說起來,單論戰鬥力明軍絕對不是瓦剌的對手,但于謙和明軍身上有一樣東西,是瓦剌人所沒有的。
這件東西就是信念,保衛自己家園的信念。有這種信念的人知道,自己是為了保衛身後的父母親人而戰,他們的奮戰和犧牲都是有價值的,所以他們總是有着無盡的勇氣。
今天看來,北京保衛戰一旦失敗,明朝,甚至中國的歷史都將會改寫,北京一旦失陷,明朝北方的半壁江山必然難保,大明王朝的歷史也將被改變。
在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于謙像一塊磐石,用一個力挽狂瀾的奇蹟,讓大明王朝轉危為安。他的功績,歷史早就有了定論。

北京保衛戰勝利後,也先的許多部下也不願再戰,提出與明廷議和。也先見那位被俘的皇帝明英宗也失去利用價值,於是將朱祁鎮送還給了明朝。
明英宗的到來,現任皇帝朱祁珏自然一百個不樂意,因為剛剛當上皇帝的他,豈肯輕易讓出位子?
所以他將哥哥軟禁在南宮,又把哥哥的兒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廢去,立自己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朱祁珏的真實想法是巴不得這個哥哥早點死,好讓皇位在自己這一脈傳承下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多後,新太子朱見濟就病死了。由於朱祁珏沒有其他兒子,于謙便上奏朱祁鈺,請求復立朱見深為太子。但朱祁珏就像沒聽見似的,根本不予理會。
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一病不起,大將石亨勾結太監曹吉祥和幾年前建議南逃的那位徐珵(此時已改名徐有貞),發動「奪門之變」,擁立被軟禁在南宮的明英宗復辟登基。
明英宗復辟後,石亨和徐有貞馬上羅織名,逮捕了于謙,並堅決主張殺掉于謙。徐有貞對英宗說:「不殺于謙,我們的政變就沒有了正當理由!」就這樣,在幾個陰謀家的共同策划下,最終將于謙送上了斷頭台。
徐有貞口中的所謂「正當理由」,指的是明英宗成為瓦剌人的俘虜後,是于謙擁立明代宗坐上了皇帝的寶座。
英宗復辟後,自然要給明代宗的上位找一個不合法的理由,表明當年明代宗是于謙這種「大奸臣」出於私心擁立的,是不合法的。既然于謙是「大奸臣」,那麼他就必須死。

五、
于謙被捕後,朝野上下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可由於他平日里性格剛直,從不結黨營私,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所以真正肯站出來為他辯解的人並不多。
即使有些官員上疏為他辯解,可皇帝和石亨、徐有貞一心要于謙死,這些官員人微言輕,他們的辯解又有什麼作用呢?
作為一名武將,石亨在北京保衛戰期間表現得很英勇,是立了大功的。但于謙性格耿直,石亨手下將領犯了錯,于謙處理起來毫不留情,讓石亨很不高興,認為于謙是想搶他的權力,所以早就想幹掉于謙。

至於那位徐有貞為什麼恨于謙,就更好解釋了。當年英宗被俘後,徐有貞建議遷都南京,被于謙厲聲怒斥,要將他斬首。雖然有人講情保住了性命,但卻成了天下人的笑柄。他怎能不恨于謙?
甚至那位太監曹吉祥,也有恨于謙的理由。明代宗登基後,有王振這個太監的前車之鑒,于謙自然會打壓太監,不讓太監干預朝政。而擁立英宗復辟,可以讓曹吉祥有重新出頭之日,所以他也想置於謙於死地。
于謙自己也知道這些,所以在被捕後,他一句也沒有給自己辯解。在接受廷審時,有位參與庭審的官員同情于謙,為他不為自己辯解感到奇怪,于謙笑道 :「亨等意耳,辯何益?」

就算徐有貞一心想要于謙死,可能給於謙定罪的證據卻很難找到。最後徐有貞只得撕破臉皮,將「迎立藩王」這樣一個殺頭的大罪強安到于謙頭上。
負責主審于謙的官員雖然是徐有貞的死黨,可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于謙「迎立藩王」的證據,只好向徐有貞彙報。
徐有貞給了一個令他遺臭萬年的回答:「雖無顯跡,意有之。」
按照徐有貞的這個指示,用一個毫無證據的「意欲」,給於謙定了死罪。這不禁讓人想起另一個被冤殺的民族英雄岳飛,他的罪名也是毫無根據的三個字:「莫須有」。

憑着這句「意欲」,徐有貞也和秦檜一樣,成為遭人唾罵、遺臭萬年的奸臣。
奪門之變後的第五天,公元1457年2月16日,于謙在北京遇害,時年60歲。史稱「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
于謙死後,被葬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三台山麓,距離民族英雄岳飛的墓地不遠。這兩人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能夠結伴長眠在這種山清水秀之地,也算是不負平生了。

六、
于謙被殺後,徐有貞還不打算放過他,派出了錦衣衛來抄于謙的家,想在於家找到點可以污陷于謙的東西——比如找到大批的金銀財寶,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宣布,于謙是個大貪官,自己殺于謙,那可是「替天行道」了。
抄家的結果狠狠打了徐有貞的臉。錦衣衛來到于謙家中翻了個底朝天后,依然空手而歸——因為于謙家根本就沒有錢!
在於謙家,錦衣衛發現了一間鎖得緊緊的房間,以為裏面有財寶,馬上向徐有貞彙報。
徐有貞大為興奮,親自率人破門而入,卻發現裏面只有朱祁鈺賞賜給於謙的一件蟒袍和一把寶劍。顯然是于謙把它們鎖了起來——因為他從來沒在其他同僚面前拿出來顯擺過!

看到這一切,徐有貞只得灰溜溜地溜走,錦衣衛也將翻得亂七八糟的於家整理得整整齊齊後,安靜地離開了。不用說,于謙用他的清廉感動了所有的錦衣衛,讓錦衣衛們認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一種人,他們的心中只有天下,只有百姓,唯獨沒有自己。
于謙從被捕到被殺的時間很短,短到住在深宮的孫太后知道此事時,于謙已經被殺。得知于謙被殺的消息後,孫太后十分傷心,氣得幾天沒吃飯,捶胸頓足地罵英宗說:「于謙有功於國家,不用當放歸田裡,何必置之於死?」
于謙死了,也先高興了。接下來的幾年間,瓦剌人屢次進犯明朝的邊境。接替于謙擔任兵部尚書的石亨的黨羽陳汝言對此束手無策,明英宗為此十分發愁,向恭順侯吳瑾詢問什麼好辦法抵擋瓦剌人?

吳瑾倒也沒有客氣,對英宗說:「如果于謙還在,一定不會讓瓦剌人這樣猖狂!」聽了這句話,明英宗羞愧地低下了頭,無言以對。
善惡到頭終有報,陷害於謙的幾個人都沒得到什麼好下場。天順四年,石亨因罪入獄,後死於獄中;同年徐有貞被貶為庶民;天順五年,曹吉祥發動叛亂,事敗被處死。
朱祁鎮死後,明憲宗朱見深繼位,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給於謙平反。此後明朝歷代皇帝對於謙多有追封。
明孝宗弘治二年,明孝宗追謚于謙"肅愍",並在墓旁建祠紀念,取名"旌功祠"。明神宗上台後,又授予于謙「忠肅」的謚號,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績。

前幾年我去過一次杭州。在一個冬天的傍晚,曾去拜謁過於謙的墓地。那天天氣有些陰沉,于謙墓前人不多,但香槽里卻有不少燒着的香,說明就算在這種惡劣天氣里,拜祭于謙的仍然在有人在。
在於謙的墓地前,我禁不住吟誦起了他那首著名的《石灰吟》:「千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正是于謙一生的寫照。

參考資料:
《明史·第一百七十卷·列傳第五十八·于謙傳》
陳文敏:《土木之變中的于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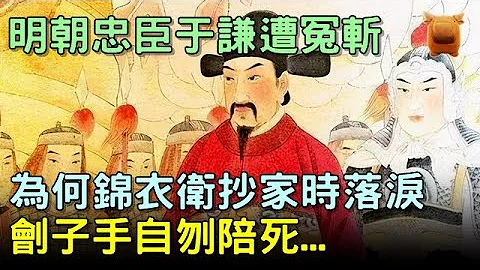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