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不久,我就厭倦了丈夫的「刻板」,不自覺地陷入了與其他男人的感情漩渦中,從此開始背叛了愛情,背叛了婚姻……
可是,當我把出軌的事情告訴丈夫想與他分手時,卻豁然發現,所謂的轟轟烈烈的愛情只是那個男人「設計」的一場「愛情遊戲」。她頓時變得一無所有,幾乎痛不欲生……
婚外的愛情觸動了我渴望浪漫的心
1996年3月,念大四的我在畢業實習時,突然接到鄰居的電話說我母親突發心臟病,正送進醫院搶救。
等我兩天後趕回家時,母親已經脫離了危險。我10歲喪父,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所以對挽救她性命的主治大夫張揚非常感激。尤其是母親,她曾以為自己是沒有生存希望的,結果張揚卻使她很快康復。
住院期間,母親了解到張揚是河北人,在南方一所著名的醫科大學畢業後分在了該醫院,尚未成家。這樣一來,母親就有意撮合我們,張揚立即表示很喜歡我。

張揚大我4歲,性格內向而刻板。念中文的我內心卻非常渴望浪漫,可為了不傷母親的心,我還是答應了。我畢業後分到一家報社做編輯,半年後就與他匆忙結了婚。那時張揚剛被提拔為科室副主任,和他結婚相當的理由是我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有體面的丈夫和裝飾氣派的家居。
1998年9月30日是我們結婚周年,我做好晚飯等他回來,看見他兩手空空,便忍住心頭的失望對他提醒說:「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你去樓下花店買束花送我吧!」他脫掉外衣笑道:「我今天連續做了兩個大手術,人都累死了。你難道不能改改那點小兒女情調么?」然後他看出我有些氣惱,無奈地轉身出去了。
過了一會兒,他拿了一束紅玫瑰進門,遞給我時甚至還輕輕吻了一下我的臉,可我卻清楚地感覺出這只不過是他的一種應付。我的心一點一點地下沉。
到晚上睡覺時,他察覺出我的悶悶不樂,便說:「我們要個孩子吧,那樣你就不會閑得胡思亂想了。」我沒有回答他,在心裏暗自嘆了口氣。我開始厭倦這種乏味的婚姻生活,於是,在做編輯之餘為一些報刊撰稿以排遣抑鬱。
1999年年初,一個叫蘇嶺的浙江作者連續給我寄了幾篇山水隨筆。從優雅的行文上我感覺到這位作者的儒雅博學。我很快編髮了他的文稿,又特意寫了封信希望與他加強聯絡。
過了不久,他回信表示熱烈的感謝,並希望與我做文友。他告訴我他是浙江一家傳媒的文藝編導。從那以後,我們開始了每周一封的通信。
6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他打來的電話,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他的聲音,那是帶着些捲舌音的普通話。他說:「我做的一個節目剛獲了個大獎,我想讓你第一個分享這份快樂。」我笑着對他表示祝賀,心裏忽然對這個遠隔千山萬水的陌生男人有了種莫名的親近感。
1999年11月初,我被領導派往煙台出差。啟程的頭天中午,蘇嶺打通了我家裡的電話,說:「我早上打電話到你編輯部,你同事說你明天要出差。」我問:「你有事么?」他語氣溫和地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就是想問你有沒有帶上厚衣服,那邊天已很冷了。」我聽着,心裏感動得竟連謝謝也忘了說。
下午張揚回家,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他卻像平時一樣吃飯、睡覺。第二天早上臨上班前遞給我一些錢說:「你今天打的去車站吧。還有,你的行李箱有點舊了,在那邊看見好的自己買一個。」
我接過他的錢攥在手裡,幽幽地說:「你拿出關心病人的一半來關心我就好了。」他道:「又來小孩脾氣了,我這不算關心你嗎?」說著他匆匆離去。
在火車上我的手機再次響起,是蘇嶺。他說:「我了解一個人在旅途上的孤單,所以就打個電話問候你。」以後每天他都打我的手機,這份體貼令我不由自主地在內心裏對他和張揚作了強烈的比較。
終於一天晚上,在孤寂的旅館裏,我忍不住主動撥通了他的手機,向他敞開心扉述說了自己對婚姻的不甚滿意以及我在異鄉的孤獨。我發覺我對他已經不自覺地產生了信任和依戀。
等我從煙台回來,蘇嶺的來信已經放在我的辦公室里,內里薄薄的一張淺藍色信簽上龍飛鳳舞地寫着七個大字「恨不相逢未嫁時」。我的心怦怦亂跳起來,慌忙地將信鎖進抽屜。事情的發展讓我有些手足無措,我暗自說服自己趁一切來得及時斬斷和蘇嶺的往來。
那天回家我找了個機會對張揚說:「我們生個小孩吧。」他看了看我,說:「現在恐怕不行,醫院可能馬上要派我去上海進修一年。」我不好再說什麼,但在心裏覺得他太缺乏像蘇嶺那樣的溫情。
浪漫的香格里拉之門突破了婚姻的底線
我開始刻意迴避蘇嶺。他寫信給我,我忍着兩次沒回信,然而這樣的堅持沒有一星期便被他的第三封厚厚的來信打破了。他很詳細地敘說了自己當年因為要一份電台工作和一個並不喜歡的女人結合的經過,他們的婚姻竟然也是消沉地過了這麼多年。
他寫道:「從你對我的迴避里可以清楚地了解你在壓抑着自己,我們有相似的痛苦。可是在守住婚姻底線的基礎上,為什麼不能有柏拉圖式的情感呢?」
2000年3月,我應邀去雲南參加一個筆會,剛住進飯店,就有人打我的手機,是蘇嶺。他說:「我就在你房間門口,也是來參加筆會的,你覺得驚喜嗎?」我的心激烈地跳動着,一時猶豫着該不該打開門。
門開了,門口站着的男人高挑俊朗,顯出而立之年的沉穩和親切,他比我想像的還要富於吸引力。而他則搶先開口說:「你和我想像中的一樣可愛。」
整個筆會我們根本無心別的,總是尋找機會單獨相處,我們面對面的交談非常融洽。
筆會第六天組織大家去永勝縣的梓里遊覽,那裡有被譽為長江第一橋的金龍橋。這古老的鐵鏈橋被西方學者稱作「香格里拉之門」,意思是說走過橋去便會到達美麗的伊甸園。
我站在橋頭,眼前兩岸峭壁入雲,下面是飛湍急流,由幾根粗鐵鏈鉤連的橋在風中輕微搖晃。我正遲疑,蘇嶺走近我說:「我扶你一起過這香格里拉之門。」說罷他拉緊我的手,帶我小心地踏上橋中央的木板。好幾次我害怕得不敢動彈,可他一直在鼓勵我說:「我們一定要過去,那邊是我們的伊甸園呀。」
我恍惚着跟隨他過了橋。在橋口才發覺自己整個人都靠在他懷裡,他的手也攬着我的腰。我下意識地退開來,他微笑道:「你看,我能給你力量和依靠。」

那天晚上,他來到只有我一個人的客房。我以為他又是像前幾天那樣來談心,可是沒說幾句話,他用手輕輕拂了一下我的臉。我稍微躲開一點說:「別,你說過要守住婚姻底線的。」他用更溫柔。更有說服力的聲音對我說:「可我們是真心相愛的,我們為真情放縱一回吧!為真情,懂么?」
我再次被他的話語打動了……
那天晚上,他離開我房間後我輾轉難眠:張揚的面容不停地閃現在我眼前。
翌日清晨,我獨自走到飯店的小花園裡徘徊良久,蘇嶺不知何時也來到我身邊。他洒脫地說:「我猜到你一定在這裡,所以我來了。」說著他走近前抱住我,他的擁抱很溫暖,而且充滿柔情。我猛然看見他身上穿的一件米灰色毛衣,細密的針線一看就知道是手工編的。
我問:「毛衣是你太太編的吧?」他不解地點點頭。我的心痛了一下,順勢比較堅決地推開他。他說 :「你在乎這毛衣?」我看着他道:「我在乎你穿着太太編織的毛衣和情人親熱,既然我們是真心的,那這樣又算什麼呢?」他站在對面,臉上顯着尷尬的神色。
從雲南回來,我越發感到在筆會期間的行為欠考慮。我打電話給蘇嶺,告訴他我有些後悔。他頓了片刻,問:「那你是什麼想法呢?」我說:「我們向家裡攤牌離婚吧。」蘇嶺的語氣立即慌亂起來:「不不,這樣太草率了。」我對他的反應有點意外,便問:「你不願意?」他支吾着說:「我只是希望能考慮周全。」
過了一天,他寄給我一封特快專遞,通篇寫滿了對我的真情厚意。可末了,他又強調自己要考慮5歲的兒子,並且他還說自己做中學教師的妻子不久前查出得了乳腺癌,他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提出離婚。我的心涼了半截,同時也對他產生出一些怨尤。
「五一」節很快到了,張揚興沖沖地從上海回家休息,他好像變得比以前開朗了許多,甚至還專門為我買回了漂亮的衣服。見我詫異,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解釋說:「進修班裡有個上海醫生和我很要好,太太是搞文藝的,他們一起批評我對你缺乏理解和關心,想想他們說的蠻有道理的。我以前恐怕是有些冷落你,現在我得改,我還學了點哄太太開心的招數哩。」
我拿着他買的衣服,忽然抑制不住地轉身哭着跑進卧室。張揚還以為我是感動了,他走進屋,伸手環摟住我的腰。我驚慌地掙脫了。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朝他哭道:「你要早點學會哄我開心多好!」他的臉慢慢陰沉起來,不太相信地試探說:「我在上海時你、你非常孤獨么?」我望着相貌平常、性格沉默的丈夫,羞慚得恨不能鑽到地底下去。縱然他千萬般地不合我的心意,可我也沒有理由背棄對婚姻的坦誠。
於是,我跪倒在他面前,向他說出了一切。他的臉由青灰轉為煞白。等我講完,他伸手拉起我,然後狠狠扇了我一記耳光切齒道:「假如你真心愛他,你就該挺直腰桿告訴我,別這樣作踐自己。」說完他推開我,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家。我獃獃地聽着家門重重的關閉聲。

「愛情遊戲」之後的苦痛欲語還休
張揚的離家使周圍的熟人朋友開始紛紛猜測,我逐漸感覺出輿論的壓力。這期間我給蘇嶺打電話寫信,希望能從他那裡得到支持和安慰。可是他明顯地退縮了,起初用工作緊張、孩子生病等理由敷衍着我,後來他甚至更換手機號碼以減少和我的聯絡。
7月中旬,我在與他幾次電話商談沒有什麼結果之後,終於請假前往浙江。他接到我直接打進單位的電話非常吃驚,中午趕到我住的飯店,一進門就緊張地問:「你跑來這裡幹什麼?我們這個小城市一點點風聲會傳得很快的。"我不滿地望着他道:「如果我獨自能夠承受住壓力,我是不會麻煩你的。」
他見我不高興,於是語氣軟了下來。我也緩和了口氣說道:「我到現在都是愛你的,我之所以對丈夫坦白一切,是因為我覺得隱瞞下去對每個人都不公平,我們相愛是沒有錯的。」不想他忽地站起身說:「可錯的是你的幼稚和衝動。」我辯解說:「我沒有。」
他惱火了:「沒有!你破壞了遊戲規則,你莫名其妙的內疚來得不合時宜,所以才搞得現在無法收拾。」
我頓時目瞪口呆,這個口口聲聲說真心愛我的男人竟然跟我談「遊戲規則」!過了半天我才回過神問他:「什麼遊戲規則?是做情人的規則么?」他瞥我一眼說:「你要知道我們的愛情即使再純真,可從開頭它就是有條件限制的。」我的心此刻沉落到最底谷,原來他這一切不過是他「編導」的一段「愛情遊戲」,我卻像傻瓜似的認了他甜言蜜語的「浪漫之戀」。
我死死盯着他滿臉的怒氣問:「其實你不過是要點所謂的艷遇,對不對?」他沒有回答,卻想息事寧人地拍我的肩。我一閃躲開,低聲跟他說:「你走吧。」
第二天下午,我找到蘇嶺的家,將蘇嶺寫給我的一疊情書當面交給他妻子。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瘦小的女人並沒有驚訝或者惱怒,她只是隨意翻了翻那些信就將它們丟到一邊說:「他又舊戲重演了。」
我反倒驚訝起來。她用平淡的語氣告訴我這已經不是頭一次了。她說:「每次他都會熱切地給對方海誓山盟,然後又回到我這裡來發誓痛改前非。別的女人當他是寶,可我早就見怪不怪了。」我問:「他說你生病其實是謊話對不對?」
她苦笑一下:「他對誰又有過真話呢?當初在大學裏追我時也是要死要活的,結婚後還不是拈花惹草。如果是一個月前挑到一個好情人倒有可能和我離婚,不過上月我舅舅有筆加拿大的遺產讓我去繼承。從前我要考慮面子和孩子,可這次我想徹底解脫出來。」
我愣愣地聽她說著,原來計劃中對他的報復在此時變得既無聊也無趣。轉身欲走時那個女人又說:「你怎麼會這麼輕信他呢?以前都是些不諳世事的小姑娘被他迷住,可你……」我羞愧地跑出了房子。
在巷子口我迎面碰到騎車回家的蘇嶺。他看見我,臉上立即驚慌起來。我本來想等他走近譏諷幾句,可他飛快地四處張望了一下,竟隨即騎着車遠遠地繞開我溜掉了。那是個我從未見過的狼狽不堪的蘇嶺,我幾乎要辛酸地笑出聲來。
回到家我生了場大病。病癒之後我辭職離開了報社,閑居了幾乎整個夏天。
9月下旬,張揚進修完畢,他沒有回家而是到醫院單身宿舍住了一星期,到周末他打電話約我到一家茶店面談。我去到那裡,他見到我,說:「你憔悴了很多,」我沉默了一會兒道:「你不是為說這句話找我的吧?」他點頭說:「我想是我們討論離婚的時候了。」
「真對不起你。」我望着他同樣有些憔悴的臉說,顯然這些日子他也備受煎熬。他卻將一份草擬的離婚協議書推到我面前:「你看看還有什麼協商的,家裡物質和金錢上的要求先考慮你。」我又一次在他面前感到無地自容,和他做了幾年的夫妻,我似乎從未好好掂量那沉默外表下的品性。
我們無言地坐了一會兒,張揚站起身。那一刻我突然懷着奢望叫住他:「張揚,我可以求你給我一次機會么?」他注視着我,低聲道:「你知道,我的職業關係生死,所以一直以來我不自覺地將嚴謹帶入了我們的生活。等我意識到這樣做冷落了你的感情時我決心改變自己。本來『五一』節回家我想跟你說剛才這句話的,可沒想到你卻給我那樣的打擊。」
我痛苦地說:「對不起,張揚,我們重新開始吧。」他慢慢地但堅決地搖頭道:「我知道你會痛定思痛,可是我對我們重新開始的婚姻感到害怕。」我的眼淚霎時流了下來,事情看來不會再有緩解的希望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和張揚離了婚,在一個朋友的幫忙下決定遠走北京做文化打工者。令我意外的是,蘇嶺居然寄了封特快信給我,他以無比誠懇的語言述說了對我的抱歉,最後他求我與他和好。
我放下信,直接打通他寫在信尾的新手機號碼,冷冷問他說:「你去加拿大的太太是不是決定把你甩了?」說完,我扔下電話,在空蕩蕩的大房子里放聲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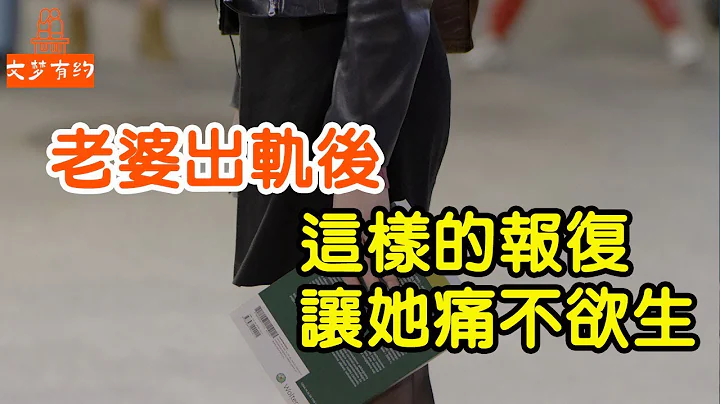
















![[ 要搞事情的節奏啊!誰的聲音讓導師無比熟悉、無比期待 ] 《夢想的聲音》第7期 預告 20161216 /浙江衛視官方超清/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wbbOzIOma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tjukvX-Un3PIiu-clOExy3Upr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