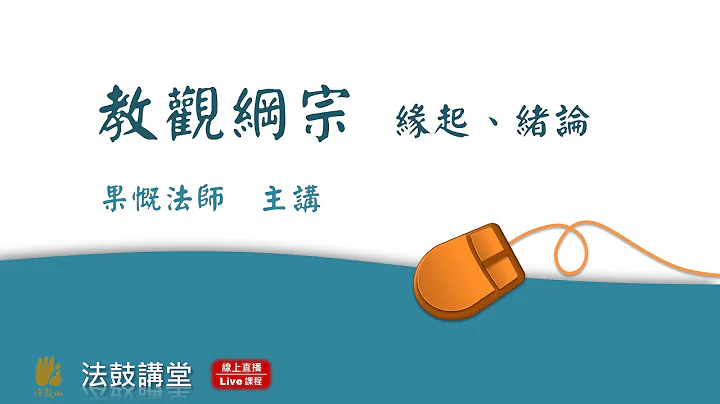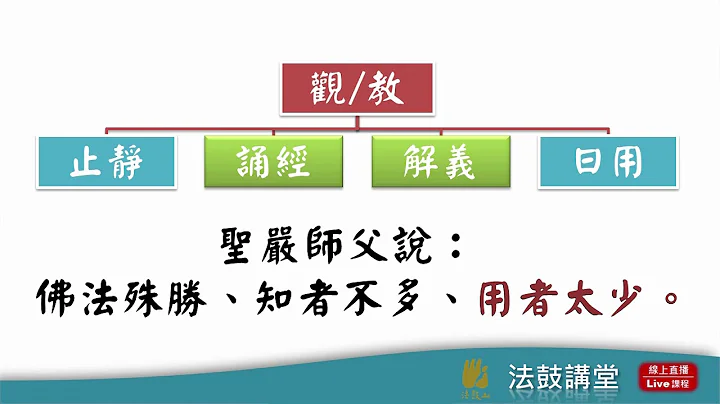實叉難陀(公元652~710年)梵名Sikshananda 。又作施乞叉難陀。譯作學喜、喜學。
為唐代譯經三藏。于闐(新疆和闐)人。善大、小二乘,旁通異學。
武周時,則天后聽說于闐有完備的《華嚴經》梵本,即遣使訪求並聘請譯人,實叉難陀便以此因緣,帶着《華嚴》梵本來華。
他於證聖元年(695)到達洛陽,住在內廷大遍空寺,與菩提流志、義凈等,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重譯《華嚴》,是即新譯華嚴經八十卷。
武后很重視,開始還親自參加。

難陀後來又在洛陽三陽宮、佛授記寺、長安清禪寺等處續譯諸經。
長安四年(公元七○四年),實叉難陀因母親年事已高,欲回家探視,上書兩次,終於准奏,敕御史霍嗣光送至於闐。唐中宗即位後,再次邀請他到長安來,景龍二年(公元七○八年)再次來到長安,唐中宗屈萬乘之尊,親自到開遠門外迎接他,整個京城的僧侶,都上街參加歡迎儀式。皇上下敕,讓他騎着青象入城,止住於大薦福寺。此次再到長安,還未來得及進行翻譯工作,就身染重疾,於景雲元年(公元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世壽五十九。皇上下詔,依外國儀式安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燃燈台火化,薪盡火滅,其舌尚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敕使歌舒道元,護送其遺骸及靈舌還歸於闐,起塔供養。後人又於火化處,起七層寶塔,號稱「華嚴三藏塔」。原典釋實叉難陀,一雲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蔥嶺北於遁①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羣,善大小乘,旁通異學。

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並請譯人。叉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凈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歷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叉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複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侖、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恆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

長安四年,叉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勑御史霍嗣光送至於闐。暨和帝龍興,有勑再徵。景龍二年,達於京輦②,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緇侶,備旛幢導引。仍飾青象,令乘之入城,勑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邁疾彌留,以景雲元午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台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勑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於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荼毗之所,起七層塔,土俗號為華嚴三藏塔焉。

實叉難陀所譯的《華嚴》和《楞伽》,都是時人公認的要典,以前雖有譯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義不備,不能令人滿意,所以須得重譯。
其中,先出的晉譯《華嚴》,經本亦來自於闐,但全經只有八會、三十四品,而新譯的《華嚴》則為九會、三十九品,就更覺完備了。
此新譯開初會二品為六品,又《十定》一品,重新集會於普光明殿,連以下十品開為第七會,故較舊譯增多一會、五品。另外,新譯經的文頌也增加了許多處【據澄觀《華嚴疏》說,晉譯梵本三萬六千頌,唐譯梵本增加九千頌,但仍未備,法藏後又將中印沙門提婆訶羅於垂拱三年(687)所譯《入法界品》內「文殊伸手摩善財頂」一段文補入】。

新經譯出後,法藏未及詳註,但其後慧苑、澄觀、李通玄等都依新經發揮經義,特別是澄觀從新經文義上理會到理事法門的重要,而大暢其說,乃將《華嚴》理論更推進了一步。
又新譯《楞伽》,梵本的來源不詳,與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四卷本對勘,經首多出《羅婆那王勸請》一品,中間開出《無常》、《現證》、《如來常無常》、《剎那》、《變化》、《斷食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羅尼》、《偈頌》二品,計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詳盡得多了。
據武后所作經序說,此譯「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似乎所據梵本還不止一種,或者隨處對舊譯有過比較研究。

經序又說「三十九門,破邪見而宣經旨」,這指經文的章段,似乎也是參考了印度的經疏而大分段落(藏文譯本經疏,即作三十九章)。
因此,這一經本是比較完備的。其他如《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為第四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和《妙臂印幢陀羅尼經》同為第二出,《文殊師利授記經》為第三出,都屬於重譯的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