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友出事後,我拿了他的股份,承諾會好好照顧他的兒子。
現如今,我看着枕邊的小狼狗陷入深思――怎麼就把人照顧到了床上?
1
老何死得挺難看的。
研一的時候他眉飛色舞,摟着剛大二的我說:學文物鑒定,還不如去買賣玉石。
“咔嚓”
他沖我擠眉,手立着砍下:“學妹,這麼一刀,富貴在天了!”
現在他剛從ICU被送出來,已經是不行了。
老何不是沒有家人,但最後只願意叫我來送他。
他老婆劉沁在醫院給老何下了病危通知後,再沒來過。
她和老何婚前做了財產公證,聽說正四處找律師諮詢想多撈點。
偏我還是個心硬擠不出半滴淚來的,好不尷尬。
肝癌晚期的老何當時渾身籠着股腐臭味,眼已對不準焦,攥着我衣角:“我,我兒.……”
當年剛高考完的老何,和初戀擦槍走火,造出個何昱來。
結果初戀一走了之,老何還在上學,小孩只好丟給父母養。
那時四年級的我因為隔壁院子小孩吵鬧學不進去。
跟我媽抱怨,我媽摸着我頭嘆氣,罵老何作孽。
一晃十六年,無數流言蜚語下,何昱不負眾望從個糯米糰子順利長歪,見誰都恨不得咬兩口。
現在老何死死瞪着我,萬語千言哽在咽喉中。
“我會好好照顧他到成年,待他成年就把你的股份還給他,讓他回公司,我發誓。”
我說完這句,老何眼中閃了瞬亮光,又轉瞬黯淡。
外面落了很大的雨,拍打着窗戶似女人哀鳴。
我看着醫生給他蓋上白布,推出去。
有點出神:我不能虧待何昱一根汗毛。
不然對不起我和老何七年情分。
電話打來,是詢問我老何身後事規格,我壓着煩躁一項項回答完。
出門看見一道高瘦身影立在雨里。
四目相對。
他沒有動,甚至後退一步。
“何昱!“
他轉身想跑。
我踩着高跟鞋,衝過去一把拽住他。
他兩耳一排的鑽石耳釘閃了下我的眼。
“別動我!“他吼道。
語氣和他指着老何鼻子罵'我沒你這個爹,你他媽少管我時一樣惡劣。
那天我去送合同,就看一臉血的何昱帶着蠻不在乎神情,大步走出團團亂的何家。
老何手裡拿着打折的棍子,幾乎不知所措立在原地。
他老婆劉沁趕緊扶他坐下,蹲下給他擦汗,溫聲細語地安慰。
老何兒子恰巧放學,嫌惡看了眼何昱背影。
想說什麼,被劉沁使眼色制止住了。
見我來,劉沁儀態萬千起身,笑着給我倒茶。
我在她眼中望見濃重的算計。
叫我這個商人都不寒而慄。
何昱和老何鬧成如今地步,她“功不可沒。”
現在何昱喘息着,像破風箱呼呼響着。
耳上雨水成串流過分明凸出的鎖骨,隱沒在起了毛的深色衣領處。
像是從水裡爬出來的鬼。
頭髮粘在他消瘦臉側,一雙眼黝黑對上我,飽含暴戾。半分不像老何初戀的溫柔似水。
老何只是向我隱晦提過,初戀後來回來找過他。
我好奇接了句。
老何咬着唇哭了。
“我不是個東西啊! !!”
那段老何剛剛走出事業的低谷期,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開心。"“"他呢?”
何昱垂着頭,啞聲點醒了我。
“死了,今晚就安排火化。”
我留意了下他神色,卻發現他一臉木然,只余嘴角可疑抽搐着。
我心頭火起,扔下他憋氣上了車。
姝姐,他不會出什麼事吧,"上車後,助理小染問,“他還站在那裡...…”2
我疲憊揉了揉眉心:
“找人給他弄回學校,每月生活費翻倍,他缺什麼就弄給他,不必問我。”
若不是老何,我根本不想和何昱有任何瓜葛。
“姐姐姐!“小渠驚呼,"何昱暈倒了!!”
什麼!
我衝出去,連傘都來不及打。
醫生翻着病曆本:“受外力衝擊,胸部閉合性骨折,貧血營養不足,誰是家屬?”
我不顧何昱要殺人的眼神,站起來:“我是他姐姐,您說。”
醫生白我一眼,給我臉整火辣辣的:
“怎麼當的家長....”"
恰巧這時他手機震動起來,醫生蹙眉停頓。
何昱掛斷數遍,那邊仍是催命般不停。
我走到何昱身邊,伸手:“給我。”
何昱唇抖着,藏到身下,吐出一個:“不。”
他抬眼,濃密眉峰下是一雙陰鷙眸子,似是含了冰碴:
“你算什麼東西,管我?“
我沒等他說完,搶過接通。
還未等我開口。
“你媽個腿,你小子把我車撞壞就這麼扔下跑了?你工資別想了,等着蹲局子吧..……
無數腥臭話語喋喋吐出,我回眸看了眼何昱。
他焦慮舔了下唇,沖我吼:
“手機給我!“
我一個不留神,便被何昱從手中奪過。
他跌回床上,顧不上疼出冷汗,就沖手機那頭低聲下氣道起歉來。
我瞥了不遠處他脫下滾滿污泥的工服,心頭止不住煩躁。
外面傳來一串喧囂,起身,只見幾個面容凶煞之人大咧咧闖進來。
何昱呢!!“
為首那人揚起眉毛:
“我要找那狗患子,你是誰?“
情況基本了解差不多,我放下手機:
“你們是捷豹拉貨公司的,何昱給你們打工,半路出了車禍,他棄車走了,是不是?”
他們互相對了幾個詫異眼色,語氣和緩了些:“對,你知不知道何昱今天毀的貨物價值多少!?“
他就是把自己賣了也賠不起!“一男子吐出口濃痰,用腳捻着。
我冷笑:“何昱工傷費用我還沒找你們結,你們還好意思跟我要錢?”
“你放屁,明明是他不規範駕駛,干我們屁事!還想訛老子!”
那人摻胳膊挽袖子就要揍我。
我眼都不眨:“你敢動我一下,等着法院傳單罷,我不接受調解,我肯定把你送進去!”
那人越發火爆,卻被身側男子攔住。
他睨了我一眼:“我們找何昱,不知你是?”
“我是他的監護人,你們僱用未成年人在惡劣下天氣加班,安全係數低不說,還沒有加班費,甚至利用他年歲小,恐嚇於他。”
我推了下眼鏡,面露冷意:“撞何昱的車是逆行。全責,所有損失都應該由他承擔,你們來這,是走錯了門罷。”
幾人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那........那何昱壞了我們的貨,就得賠!”
他吶吶。
他還在堅持,身旁那人使了個意味深長眼色,看我:
“實話我告訴你,撞他的人我們早找過,他是個窮光蛋,賠不起!”
“我們只能來找你,畢競合同里可寫了,工作中造成損失,由本人承擔!!”
這種霸王條款,可下方妥妥是何昱的簽字。
“這小子還在上高中罷,你可想清楚,真要鬧起來,我們可不管那些!”
那人神色陰鬱瞅着我。
我嘆口氣,掏錢包:“你們要多少?私了吧。”
何昱是未成年人,真要維權起來,太費精力。
被小小訛詐一筆後,我剛推門,卻見一雙黝黑眸子自門外驚慌逃遠。
回到病房,何昱沉默良久:“你給了他們多少錢?“
“幹嘛,要還我?”
我脫下大衣搭在椅背,隨口問。
“是!“
何昱翠得像頭牛。
我頭痛得厲害,沒有心思哄他,眼盯住他:
“實話告訴你,我是你爸爸指定的意定監護人,換句話說,你十八歲前,就是手劃破個口,我也得包上,親自看着它長好。“
3
“還有不必還,我不是為了你。”
我甚至都不認識你,如果不是老何,性子寡淡的我,對於這樣敏感倔強的孩子,定是要避而遠之的。
“以後長點眼睛,別什麼合同都簽,把自己賣了都不夠。”
許是我話太直白,叫他呆住,張了幾次嘴,不知說什麼好。
“關燈,睡覺。”
我"啪嗒"摁滅電燈。
他受傷第一晚,我買了個摺疊床,睡得極不安穩。
半夢半醒間,我聽見病床上傳來極力壓抑的抽噎聲。
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哭起來像啞嗓的烏鴉。
我欲裝睡,腳卻踢到床架。
哭泣聲戛然而止。
病房裡靜如墳墓。
我沒有睜眼,不久,竟真的睡了過去。
過了幾天,何昱吵着要出院。
我知道他不想欠我人情,索性由他去。
但他要保證自身安全。
他冷笑幾聲,認真打量我:“你也是他的小老婆?”
“他給你多少錢,演得倒挺投入。”
那眸子滿滿惡意,我竟有種無力感。
恰手機陌生號碼閃爍。
是劉沁。
我看了眼后座的他,按滅。
“我和老何就是合作夥伴,金錢利益總比其他牢靠。”
我瞥見他消瘦肩胛時,問:“老何不給你生活費的嗎?“
“我不要!那種人的錢,我嫌臟。"何昱立刻道。
一路無語,何昱偶爾打量我,只目光一對上,他就移開眼。
找他住的地方很曲折,導航偏軌數次,終於拐進一陰暗小巷。
陽台上曬着汗衫、被褥,甚至小孩尿布,花花綠綠像劣質旗幟。
越往裡走我面色越難看,堆滿垃圾的兩側樓道惡臭衝天,地面骯髒,還在頂樓。
何昱習以為常抬腳。
我:“你就住這種地方?”
“不願意待就走。”
何昱頭也不回。
上樓後,他卻遲遲打不開房鎖,裡面卻傳來女人說話走動聲,他詫異大力拍門,吼道:“開門! !”
“幹什麼!小流氓!“
良久,門被猛地拉開,髒水盡數潑在何昱臉上,女人眼底滿是嫌惡:
“再敲我報警了,趕緊滾!“
我站得遠,眼見手裡攥着鑰匙的何昱鬢角滴下,頭上還頂着片菜葉。
許是我同情目光刺痛他,他鐵青着臉找到房東,還未開口,房東沖他努頭:
“啊呀,你東西都在那了啊,拿了趕緊走。”
“憑什麼?“何昱抖着唇問,“我每月房租都是按時給.....”
房東輕蔑看他眼,不屑吐出三字:
小赤佬。”
何昱呆了下,眼看着門要拍到他臉上。
我扯回他,蹲下幫忙收拾東西,卻見何昱臉色慘白,手直發抖。
“"回學校住,以後不必兼職打工,我給你錢。”
我看向他:“別覺得我是在可憐你,老何留下的東西,只有你有資格拿。"
許是對何昱的愧疚,老何留下的股份,除了額外分我10%外,剩餘全留給何昱。
當然這股份得他成年後我才能拿到。
“我不希望之後的合伙人,是個腦袋空空的廢物。“我直言。
何昱沉默。
自老何父母去世後,老何發覺這個半生不熟的兒子很是棘手。
劉沁看似溫柔可人,一旦老何提出要將何昱接到家中。
她便開始垂淚心痛,苦着臉委婉提出自己受不了家中多個外人,不如給雙倍的錢養在外面。
加上二兒子何念欽要考高中,何昱偶爾到何家,都能和他掐得不可開交。
老何也不敢冒這風險。
我看着他消瘦側臉,鬼使神差伸手給他摘去頭上葉子。
“回學校罷,別吃苦了。”
我輕聲。
“算姐姐求你。”
許是我長得親和,又或是走投無路,何昱沉默許久,點頭了。
“我會還給你的。”
他低聲。
我揀起行李,只當沒聽到。
4
何昱上的私立高中,是老何拿錢給他砸出來的。
裡面凈是拼爹的主,老何不常露面,何昱性子又倔,受欺負是難免的。
這些我能想到,劉沁也能想到。
我本想和班主任聊聊,卻在她連環奪命call下,被迫出來和她見面。
她嘴角挑出的每一寸弧度都叫我噁心。
寒暄幾句後,她推給我一張銀行卡。
我沒動手,用眼問她。
劉沁開門見山:“萬總,我想看看遺囑。”
""遺囑並不在我手中。”
我放下咖啡,微笑。
是在撒謊,又怎樣。
遺囑是做了公證的,是何昱的保命符。
劉沁挑了下唇,笑容寸寸僵在臉上。
“就算我知道,我也只會尊重他的遺願。”
我將卡推回去,雙手交叉:“讓您失望了,告辭。”
“何昱就是個野種,“劉沁站起來,聲音驀然尖起來,她見我神色冷下來,慌忙變了臉。
“萬總,您家大業大,志向宏大,我都懂,只要給我和念欽留一點過日子就好啊!”
這話幾乎把話挑明,現在知道遺囑的只有我,如果我和劉沁聯手造假。
何昱一根毛都得不到。
我和劉沁分贓,我拿大頭。
低風險,高回報,好划算。
沒有商人能輕易拒絕。
實話說,我猶豫了片刻。
眼前忽閃過何昱慘白面容,和隱沒最眼底的惶惶。
“除了“萬禾"股份,老何剩下的產業、房車,都是你的,"我心底嘆氣,望向劉沁,“做人不要太貪了。”
恰巧助理來告訴我和何昱班主任約的見面時間到了。
到學校後,我巧妙塞了個紅包,老師臉色轉晴幾分。
“你們家裡人怎麼才來管啊,孩子都被耽誤毀了。”
這話聽得蹊蹺。
我才想問。
便見一堆學生嘻嘻哈哈簇擁着一高大男生,諂媚笑着:
“狼哥,我剛才把何昱那小子打了一頓,給那小子臉都疼紫了哈哈哈哈。”
“他爬都爬不起來哈哈哈,抽抽像條狗一樣。”
“走,去看看。”
被叫做"狼哥”的男生翹起嘴角。
我沉着臉跟過去,男保鏢一路跟着我小跑。
眼見狼哥在眾小弟簇擁下,走進怪叫聲此起彼伏的男廁。
貫穿耳膜的慘叫猛地炸起,周遭人群面面相覷。
我推門衝進去,地上,何昱被人打得鼻青臉腫,血蜿蜒流了滿臉,眼都腫了半隻。
可他死死咬着狼哥的手,血滲出來,滴在刺目瓷磚上。
狼哥大驚,扭得似活蝦。
誕水自何昱嘴角流出,他目眥欲裂,最後活活拉下他兩道肉。
狼哥臉疼得扭曲,叫罵得破了音。
何昱挑起唇,哈哈大笑,卻只陰森得叫人起雞皮。
他唇角翹着,連着半邊臉抽搐,疹人無比。
恰風起,吹得門扇晃動。
我二人對視瞬間,他笑聲戛然而止。
甚至怒氣翻湧的猩紅眼底,都恢復幾分清明。
我別過臉,不想泄露我的同情神色。
報警了! !!”
“干甚?“
男保鏢衝過,他本就人高馬大,加上老師也懶洋洋來說了幾句。
他們蜂擁而散。
只剩何昱搖搖晃晃站起來,他校服沾滿污漬,就連臉上也未能倖免。
“轉校。”
我回身對班主任道,閉了下眼,可話還是不禁帶了冷氣。
“今天就走。”
班主任許癟了下嘴,點頭:"“"您也知道,這種事我們老師管不了的,這裡都是什麼身份,我們哪敢..…"
男保鏢扶起何昱,被他猛地推開,自己踉蹌站定。
我沒聽老師啰嗪完,回身看何昱。
他滿頭冷汗。
可從始至終盯着我,審查我有無露出半分鄙夷神色。
可我只是淡淡給他揩去了面上的污漬。
他本能躲了下。
見他野性未消,我索性單手捧起他下巴。
瞥見其中尖尖虎牙,笑道:"挺不錯,怎麼沒把他咬死呢。”
何昱猛地掙開。
我眼中笑意散去:“他叫什麼名字?“
我摸摸他側臉:“別怕,姐姐給你做主。”
“我沒怕過。“何昱瞥我,聲音啞了幾分。
我記下那人名字,敷衍嗯嗯幾聲。
“先去醫院。”
何昱去包紮時,我頃時冷了臉。
要是照顧不好何昱,死了都沒臉見老何。
“老師,麻煩請一下徐朗的家長,我要面談。”
在會議室等待的時候,助理打來電話:
“姐查到了,那男生的家長叫徐克,是我們公司的合作夥伴,半個月前才簽的合同。”
竟然是他,
我搖頭,嗤笑了聲。
良久,門被推開,女人進來只是白我,活像眼睛進東西了。
直到徐朗父親推門,我起身微笑,伸手:“徐總,好久不見。”
他懵了下,緊接下意識伸出雙手:“萬總!”
5
徐朗瞳孔放大一圈,頗有些如芒在背,偷偷睨我們。
知曉事情原委後,徐克一言不發,臉色垮下去。
我:“我要求徐朗當著全班同學面道歉,到何昱滿意為止。”
女人站起來,厲聲:
“想得美,他被打是他活該,誰叫他賤的來惹我兒子..…”
何昱盯住女人,眼底冷似冰碴,拳頭慢慢攥起。
徐朗跳起來:"怎麼看我媽的,你他媽又想挨打是吧。”
老師在一旁喝水的手都抖。
"坐下!“徐克扭頭怒喝自己兒子,“真沒教養!”
他看我:“萬總,我兒子就是衝動了點,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何必鬧到這步。”
他舉起茶杯:“這樣,我代犬子認個錯,不好意思了小兄弟。”
“"你的醫藥費我全包,要什麼...…”
我沒動,冷看着徐克手慢慢落空。
“我不接受。“何昱淡淡道。
我給了何昱個讚賞眼神。
徐克勉強笑了下,拿眼瞥我:
“萬總可是忘了我們尚有合作,要是因為我們私人恩怨,導致合作取笑,不知萬總...…”
“取消吧。”
我微笑打斷他。
“能教出這樣孩子的家長,我也不敢和他合作。”
“那違約金...…”
“我們公司雙倍賠。”
我簡單道。
徐克臉臭得像生吃了豬大腸。
我貼近他耳邊:“徐總,慣子如殺子,我也是好心。”
徐克的手抖得不成樣子。
我知道,他不敢。
徐家公司規模小,斷流等於破產。
徐朗臉色煞白,尤其在挨了他爹幾巴掌後,狼狽逃竄:
“爹!我們有何應欽怕什麼!他都告訴我了,以後"萬禾"都是他的,何昱算....…”
徐朗被打得抱頭鼠竄,直到喊出這句。
我瞥向何昱。
他神色不改――徐朗是為了討好何應欽,才處處針對他。
看來他早知道。
“你錯了,"我接話,所有人目光皆移向我。
我:“萬禾未來的二股東只能是何昱。”
按遺囑走,何應欽半分插手萬禾的資格都沒有。
徐克眼猛盯住我,面色幾變。
最後徐克還是力壓著兒子道歉了。
在全班面前,徐朗臉紅得要燒起來,舌頭打了幾次結。
何昱唇邊淤青未消,他掃視徐朗許久,眸色複雜。
我以為他要動手打回去,正想按住他。
卻見他驀然一笑:“我原諒你,因為你只是叫別人當槍使的廢物。”
給何昱新換的學校在我一套房產附近。
乾脆叫他搬過去。
我偶爾過去時,能望見他俊朗小臉漸漸有了笑意。
他對我的態度也不似開始抗拒。
偶爾休假,他學習,我靠在床頭看書。
多少次我睡着,醒來發現書已經被整齊擺在枕邊,薄毯蓋在身前。
“學什麼呢?“我湊過去。
“三角函數,“他看都不看我。
“好好學,姐姐給你買大G。”
面對我的大餅,何昱無奈翹了翹嘴角:“好。”
最後高考競考了個本科,已經是不錯。
我帶他出去吃飯慶祝。
旁邊的服務員竊竊私語,我睨了眼何昱,只見他身材勻稱高瘦,臉頰輪廓明顯,眸如點漆。
這小子比老何出彩啊。
我便吃邊走神,直到何昱伸手過來,要給我擦嘴。
我下意識接過,他卻不鬆手,我握住他關節,手感似釉玉涼潤。
“幹嘛?“
何昱挑了下眉,掙了下,靠回去,垂眸玩手:
“沒什麼。”
服務員羨慕道:“姐,好福氣啊。”
我失笑:“這是我弟。”
服務員捂嘴笑:“對對對,都叫弟弟。”
何昱來勁了,托腮看我:“姐姐~”
我: “"...”"
“要不要去看看老何?”
吃完飯後我問。
他沉默片刻答應了。
墓園很黑,冷風浸透我衣角。
我剛想識趣走開,一胳膊攬住我。
何昱將頭埋在我肩頭,他比我高半個頭多,帶着濃厚鼻音道:“靠會。”
我瞥了眼墓碑上笑得燦爛的老何,閉眼。
老何你忍忍罷。
6
何昱衣服間是清冽的洗衣液味。
他自己挑的,莫名勾着我的鼻尖。
“這幾天有時間去趟公司。"回去路上,我看他。
何昱已經成年,也該叫他接手公司事務了。
他只是沉默。
剛到路邊,上車後,剛啟動,車卻發生異響。
“怎麼?“何昱隨着我轉身往後望。
強光閃得我們睜不開眼,
輪胎與地面尖酸刻薄的摩擦聲,在寂靜山間似是突兀十倍......
"走!“
何昱大喊。
他猛地推開車門,一手給我解開安全帶,一手將我扯下車。
我從不知他力氣如此大,被他扯得滾進路邊草叢同時,巨響在我耳邊炸起,幾乎貫穿耳膜。
我的車在重卡下變成豆腐渣,零件四散,火光衝天。
"別抬頭。”
何昱趴在我身上,葳蕤野草劃得我心尖微顫。
他伏在我身上,身子緊憚,似伏擊的野豹。
那重卡停頓一霎,許是見我們躲得刁鑽。
他立刻逃之夭夭。
何昱攙起我,同時望了眼盯着貨車遠去的方向:
我蹙眉:“沒事吧?“
他沒回答。
我發覺他手抖得異樣,艱難吞咽着口水。
他猛地回神,死盯着我,神色甚至有些駭然。
“你怎麼樣?“
他按住我肩頭,上下掃着,幾乎被捏痛的我哼道:“輕點。”
他沉着臉不說話,蹲下就要掀開我褲腳查看。
我欲按住他,沒攔住。
早知就不該穿這麼薄,小腿被尖銳荊棘勾破,血流進我腳跟。
何昱手慢慢扯出荊棘時,疼得我淚流滿面。
真的忍不住啊!!!
何昱手頭一滯,仰頭時眼中戾氣,卻比之前洶湧萬倍。
我終年不見陽光,腿白,一流血更顯得疹人。
我想安撫他:“我血小板少,受傷不容易好,其實沒那麼嚴重...”
何昱解下我圍巾,蹲下給我嚴嚴實實纏上。
隨後沉臉,蹲下,示意我上去。
我還欲推辭下,何昱冷臉偏頭:“就把我當成木樁,別矯情。”
最後何昱背着我走了三四里的山路,周遭聳立的山峰浸沒在淺藍的煙雲中,草木影綽如人影,偶有鳥鳴。
何昱深重的呼吸落在我耳側,似圓潤珠子在我耳中碰撞滾着。
我咽了下口水,想幫他擦汗,聲音不禁軟了幾分:
"把我放下來,我能走。”
“走廢你。”
何昱不耐煩回道。
我被噎得不再說話。
他累得青筋綻出,口中呢喃着:
“別怕,我發誓一定把你帶出去,”
“我要保護你,絕不像他那般無用...”"
我偏頭疑惑看他:“他是誰?”
“老何。”
我氣笑,老何也是他叫得!
最後何昱將我放到最近的鄉鎮醫院時,渾身被汗水浸透,癱在牆角,還強撐着喊道:“醫生!”
許久,一圓滾身子扭出來。
看見一地的斑駁血跡,女人頓時手足無措:“"啊呀,我老公不在家,出去給母牛順蕙了。”
我因為本就貧血,這下連指尖都涼了,頭暈到看見何昱長了三個頭。“不在?“
何昱鼓着眼睛問她。
農婦後退幾步,連連擺手:“真不在!!俺不會治人啊,你們走...……”
“麻煩大嫂有紗布碘伏嗎,先把血止了。”
何昱踉蹌爬起來,單手攙扶起我。
“求您了。”
女人道:“我看看哈!!”
最後她抱來大堆瓶罐,何昱坐在床邊,挽起袖子,小心給我剪下褲腳。
把各色藥水在手背傷口上試了遍。
我才瞥見他半邊手上皮開肉綻,手腕結着紫紅血痂,眼一下直了。
“沒事。”
何昱先我一步答道,他低頭,濃密睫毛在眼瞼處投下淡淡陰影。
“不疼。”
“先處理你的。“我往後縮了下,堅決道。
他還是個小孩。
我還要照顧他的!
何昱盯着我半秒,笑了下。
他拒絕我的幫忙,倒出半瓶蓋,我才發現―-他不僅是手上,就連鎖骨處也有擦傷。
太陽上來了,屋內暖陽遊走窗框。
剛一接觸酒精,何昱手臂線條突兀綳起,汗珠顆顆滾圓滑落。
我從小就怕疼,見狀不由驚駭往後縮。
何昱深深看我一眼,他的眼幽深,莫名給人壓迫感。
“上藥。”
他扯過我腳踝,身子向前貼,帶來股莫名熱氣。
解開圍巾帶着血痂破裂,疼得我渾身戰慄。
我大口喘息着,手緊攥成拳。
何昱動作頓了下,低聲:“酒精是會痛點,不用忍。”
他伸手覆住我眼睛,淡淡汗味竄進我鼻腔。
下一刻,傷處似被撕裂百倍般,我嗚咽一聲,小腿綳直,掙紮起來。
何昱按住我腳踝,像按住不聽話的魚。
冰冷酒精棉球遊走在在腿側處,帶起火灼般的疼痛,我猛地抓住何昱的手,咬牙忍着。
他的手骨節分明,死物般任我抓着。
不知過了多久,痛意於麻木中漸散。
我巍巍顫顫睜眼,房中異常憋悶,只聞心激烈跳着。
他睨我:“你還真下死手啊。”
他衣衫松垮,額上頭髮因汗貼在臉側。
手還被我攥在手心。
我只覺臉皮微燙,移開目光:“鬆手啊。”
“不敢。”
何昱看我――我指甲較長,差點嵌進他肉中。
我觸電般甩開。
他眸子盯着我,深不見底。
忽而伸手,手腕一轉,將眼鏡推到我鼻樑上:“戴好,再丟不幫你撿了。”
小兔患子,反了天。
話在嘴邊卻不知為何說不出口。
今天他背着我走的三里山路,每一步都踩在我心尖。
我再沒辦法那麼輕鬆和他打起哈哈。
“他們是沖我來的。”
今晚和主人商量好留宿後,我聽着窗外蟲叫正要睡。
何昱給我打電話,開頭一句話便是。
我頓了下,老實道:“我死了,劉沁她照樣開心。”
何昱根本對付不了她。
“不管怎麼樣,是我拖累了你。”
何昱嗓音啞得不成樣子,說完,他局促笑了聲:
“我從生下起就一直在拖累別人,要不是因為我,我媽也不會出事...…”"
“現在又牽連你,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就是個掃把星哈哈。”
“說的什麼話,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心頭一陣異樣,甚至話也尖銳起來。
若是之前他急着同我撇清關係,我自是無所謂。
只是想到今日他背着我走在山間,畫面縹緲,好似電影時時在我眼前閃現。
能碰到患難不扔下你的人,幾率何其之小。
我心底隱痛起來,口是心非道:“這點事算什麼,這次不成,我量她也不敢再...…”
何昱艱難蹦出幾字,頭次打斷了我:
"“你別管我了,你離我遠一點,等回去我就搬走。”
我簡直笑出來,捏着電話字字句句:
“告訴你不可能!我答應了老何,千金一諾。”
“我不能虧欠死人,要遭天罰的。”
我直起身,心底竟然有幾分緊張。
何昱那邊沉默了。
只有夏蟲清脆鳴叫。
“再說,姐姐捨不得你嗎。”
我惆悵說了句真話――養條狗也是有感情的。
更何況何昱比狗帥多了。
我聽那邊呼吸亂了幾分,良久,
“滴....…”"
掛了。
小子還會害羞。
我垂眼,按下心底淡淡漣漪。
只想――劉沁是不想活了。
對我們下手。
次日剛換完葯,恰好我電話響起,離何昱較近。
我示意他開免提遞我。
8
“萬姝,怎麼樣?打電話怎麼不接。”
一清潤焦急男聲傳來。
何昱看我一眼,我關了免提,只報了位置。
“這下有人來管我們了。”
我舒了口氣。
卻見何昱頭頂亂糟糟,不由想幫他捋順。
誰料到他躲開,睨我:“他是誰?”
我""哼哼幾聲:“小孩子別問那麼多。”
“我不是小孩了。”
何昱盯着我。
我不是很想接他的話,打哈哈說著窗外絲瓜長得真綠。
何昱盯了我許久,眉頭又擰起來了。
我裝看不見,低頭玩手――不是小孩,又能是什麼呢?
—小時,唐風急匆匆走進來,柔聲:“我來了。”
看到何昱瞬間,唐風腳步一頓:
“這便是你弟弟罷,幸會。”
何昱不作答,沉沉望唐風。
“這孩子叛逆,不用管他。”
我欲起身,唐風一把攬過我腰身,橫打將我抱起。
我臉皮有些臊,垂眸何昱:“走吧走吧。”
何昱獃獃看了眼我們。
唐風很自然低聲問我話,我選擇性回答――我們曖昧半年,誰也不願先捅破那層窗戶紙。
回公司後,何昱非常主動提出要搬進我家。
說是劉沁喪心病狂,一定是要弄死他的。
他害怕。
我拒絕的話轉了十八個彎,想想等先收拾了劉沁再安頓他不遲,終是答應了。
在準備起訴劉沁時遇到了麻煩。
何昱倒是記了卡車車牌號,可惜民警查過後,確定他和劉沁沒有任何關係。
意外只是因為疲勞駕駛。
何昱在警局表現得很激動,甚至連"放屁"都說出來了。
“意外不意外我能不知道嗎!!”
惹得周遭人紛紛探頭,民警臉色越發臭,指着他就要發作。
我揉着太陽穴,不耐道:“你清醒點!發什麼瘋。”
何昱才訕訕閉嘴。
出警局時,一車正常拐彎,卻驚得何昱臉色大變,猛地將我推進警局。
毫無防備的我踉蹌幾步,還是跌了個狗吃屎。
見那車載人後就走了。
何昱意識自己搞錯,連忙奔過來扶我。
民警勸他冷靜下,他回頭怒吼民警:“滾!別碰她。”
“你幹什麼!你想襲警!”
警官疾聲厲色,手摸到腰間。
我看失了神志的何昱,怒上心頭,抬手給了他一巴掌。
“別在這發瘋!”
扯着他出了警局,挨了打的他顫着唇,好似提線木偶。
回家後,他一言不發,我逼自己冷靜下來,恰巧唐風來電。
說是給我談了個大項目,叫我立刻過去。
我睨了何昱一眼,他果真緊緊盯着我。
"別去。”
他聲音悶悶傳來,似是隔了層深海。
我沒理他。
拿包準備出門,何昱欲要攔我,被我閃身躲過。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很煩人,“我蹙眉。
本來就沒什麼帶孩子的經驗。
他一鬧,我就只想跑。
他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唇失了血色。
唐風那邊又來催,我接着電話要走。
何昱將手機從我手中抽走,定定看我:“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危險?”
"給我。”
我脾氣上來,盯着他冷聲道。
何昱充耳不聞,直接按滅屏幕:
“你就那麼喜歡他,非要出去見這一面?”
何昱嗓音在顫抖。
我卻盯着燈火投下他模糊的輪廓,帶着青澀細小絨毛。
他的手雖大,卻白嫩。
還是個孩子啊。
我惆悵得原諒了他。
“乖,姐姐出去給你掙飯吃。”
我摸摸他臉頰,他頭次沒有拒絕。
我:“放心,我馬上回來。”
何昱沒說話,可影子倔強立在玄關處。
不知為何,我心頭微動。
上車後就開始扒拉手機,要不給他帶一雙aj回去。
他們男孩是不是都喜歡?
唐風帶我進了片景區,樹木薪郁遮天蔽日。
“老闆都愛住這裡,空氣好。"唐風解釋道。
我不安的心在推門看到劉沁瞬間,只化作平靜。
唐風還叫我入座。
我沒動。
劉沁的首飾被燈光映得華貴,臉卻憔悴,像籠了層不相稱的殼子。
她直勾勾盯我,挑起一詭異微笑:“萬總好。”
手機上彈出何昱短信一條接一條。
“在哪?“
我剛想回。
“是他在擔心你?“
劉沁帶着噯昧微笑打斷了我。
她從包里掏出一份遺囑,在我眼前閃了下,笑得更艷。
“屬於我和應欽的東西,我遲早要拿回來的。”
“你就跟着那個雜碎一起去死吧!“
她猛地朝我撲過來,我毫無防備被撲到窗下,腰斷了般疼,被劉沁騎在身上。
纏鬥間,被她扯走了手機,腿上也挨了幾腳。
她起身厲聲環顧:“看好她!“
唐風想衝過來,卻被保鏢一腳踢彎腰,呻吟着跪在地上。
大門緊閉,從外面""咯噔"落了鎖。
“該死!“
我臉色慘白。
她把我困在這,是想引何昱來?
我越想越心驚,那樣的瘋子什麼干不出來。
她不敢動我,我死了,會有無數人找我。
她脫不了嫌疑。
可何昱呢?
他無依無靠。
我強忍着痛爬起來,喉中腥甜,隨手一措竟滿目血紅。
“萬姝!”
唐風想跑來扶我,我看他便心煩,閃身躲過。
他懊惱道:“我也沒想到,不過沒關係,我們在這待到明早....…”
我沒理他。
順手扯下窗帘,打成結成長長一道。
三層樓,摔不死,只是多層保障罷了。
他按住我的手,驚道:“你要幹什麼!”
""明天就來不及了! !”
我低聲。
我脫下高跟鞋就要踩上窗欞。
“萬姝!“
唐風不可置信看我,沉默良久,看我的眼神似要刺進心底:
“你那麼在乎他嗎?為他甚至冒這種險!”
“那我呢?我算什麼。”
他上前一步,激動控住我肩頭。
我偏頭,頭一次覺得看到他都令我噁心。
“"你什麼都不是。”
我在他眼中望見自己異常冷淡的面容。
他卻聽懂我沒有說出來的話那般。
手無力滑落。
我系好繩子在腰間:“別礙事。”
我想到何昱出門前的異樣神色。
我不敢想象他整晚聯繫不到我會怎樣。
唐風笑得比哭難看,唇都顫了:
“萬姝,你之前不是這樣的...…”"
“今日過後,不必聯繫。”
我扔下一句話,沒再看唐風。
剛落在軟綿草地時,便聽見頭頂傳來喧囂。
我拔腿就往樹林深處跑,為了躲避保鏢,我越走越偏。
我原本舊傷未愈,林間草木洶湧,雖能隱藏蹤跡,但走得我汗透衣衫。
好在劉沁應該是帶着假遺囑搞事去了。
我正想着,猛地聽見遠遠說話聲。
我悄悄潛伏過去,卻聽見劉沁:“既然如此,就把字簽一下。”
何昱穿着黑色衛衣,身形瘦削,只能瞥見側臉。
"她呢!“”
“你簽了我自然會放了她!!“劉沁眼睛深深凹陷,死死盯住何昱。
“不然我不確定我會幹出什麼來!”
何昱毫不猶豫就要簽字。
我瞪大雙眼,立馬就要跳起來。
下一秒,何昱扔下筆,猛地伸手勒住毫無防備的劉沁。
他比劉沁高一個頭,又有力。
劉沁臉色發紫,拚命拍打着他手背。
“你怎麼算計我都可以,你動她真的惹到我了。”
合同紙頁在風中瑟瑟抖着,何昱神色木然,胳膊愈縮愈緊,衣料摩擦聲似紙錢翻飛聲。
“我我......”"
劉沁已經喘不上氣來,腳尖慢慢綳直,眼凸出充血。
何昱還沒有鬆手跡象,他眼底閃着詭異光芒。
“你知道他創建公司的錢是怎麼來的嗎?”
他沒看劉沁,話卻飄零在空中。
“是買我媽命的錢!!"何昱悲憤似啼血,又勾唇笑起來,"那人酒駕,拿三百萬來私了,哈哈哈他竟然同意了。”
他喃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我媽,那天我有多開心,我現在就有多恨他。”
“這公司,我看一眼都嫌噁心!你們還要爭。”
他指縫中閃出亮光,刀鋒斬斷絲縷霧氣。我心底發涼,他是真的想殺了劉沁。他瘋了嗎?
“住手!“
我跳出來那刻,何昱像是從積年的噩夢中驚醒。
臉上甚至帶着絲迷惘。
“萬姝..…”
下一刻,他如夢初醒,甩下劉沁,立刻向我奔來。
劉沁癱軟成泥,渾身發抖。
我看他:“先走吧。”
要落雨了,山裡不安全。
彼時天雷滾滾,雨點隨風飄落。
我很快被淋得濕透,寒意滲進骨子裡。
何昱脫下外套給我,自己只留件短袖。
雨越來越大,我們深一腳淺一腳。
我很快沒力氣,牙齒都在打顫,就連眼前景象也模糊起來。
何昱看起來要急瘋了,入目皆是延綿山脈。
“對不起,是我連累你。”
他抱着我,話尾都帶着顫音。
該死的是我,我早,早就不想活了!”
"胡說什..…我剛張嘴,便被風雨嗆得咳嗽不止。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我們終於尋到守林員的小屋。
老人好心地幫我們燒了鍋熱水。
我洗漱完,望着屋外瓢潑的雨,覺得方才一切恍然如夢。
他下意識就要來摸我額頭:“沒發燒,難受嗎?”
我握住他的手,仰臉看他。
“你媽媽的事為什麼從來不告訴我?”
何昱神色閃爍下,打哈哈說著劉沁的話他都錄下來了。
我:“我問你話!“
何昱嘆口氣,將我碎發挽到耳後。
“我不想提,“他看我,相距不過咫尺。
“我當時才七歲,看着我媽腦漿在地上冷卻,而我爸拿錢後,一遍又一遍保證說就是意外。"
“我只恨我保護不了她,“何昱手指划過我下顎,帶着異樣的溫度。
他悶聲:“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害怕嗎?我...…”
他將頭點在我肩頭,灼熱呼吸燙着我心尖:“真的想殺了劉沁!”
我仰臉看他,他眼底洶湧着莫名情感,似是再也壓不住。
索性手撫上我後頸,盯着我乾澀道:
“你知道,我除了你,再沒有在乎的人了!”
"你要是出事,我...…”"
何昱一路走來的坎坷,我看在眼裡。
像在荊棘中跋涉千里的旅人,滿身的血痕逶迤。我主動吻住他鼻尖。
他僵住,下一刻,他眼亮起來,手指插入我發間,用力吸吮着我的唇。
“萬姝。”
他理了下我凌亂碎發,手撫上我臉頰,欲要說什麼。
卻喉頭滾動,只擠出一聲笑。
我睨他:“你都想和劉沁一起死,還留錄音做什麼?”
“我不想再叫你受別人的牽制,也不想叫你忘了我。"何昱油嘴滑舌道。
最後從房中出來時,我幾乎不敢看老人,用頭髮蒙住臉。
老人笑眯眯喊住我,說再呆會吧。
“山中雨水大呢。”
後來我們何昱手機里的錄音也沒用上。
那天雨出奇的大,那處又是窪地。
我和何昱在木屋看着遠處渾濁洪流一瀉千里,心裡都隱約有了預感。
劉沁出了意外,最後屍體都沒找回來。
塵埃落定後,何昱和我簽了股份轉讓協議。
我成為萬禾最大股東。
何昱全程在玩我的頭髮。
你就這麼把股份交出去,不怕將來我把你趕出去?”
何昱連忙表示――趕出公司可以,趕下床不行。
氣得我想踹死他。
晚間,纏綿過後,他吻着我脖頸:“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不能總是站在你身後仰望你吧。”
“那個唐風還在騷擾你?“他押着脖子。
我沒好氣將他頭按下:“早叫你拉黑了,還問還問。”
“明天我有時間去看電影吧。”
我扒拉着手機,問。
“你要看什麼?”
他隨口:“《我愛你》”
我指尖一滯,彼時,天邊稀星皎月,雲層暗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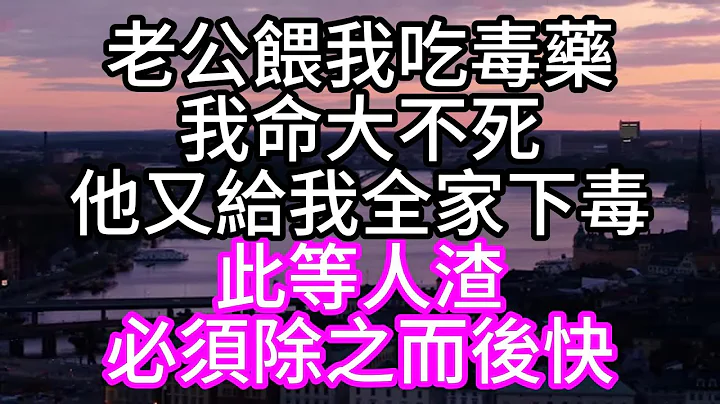








![【搞笑】虧成首富從遊戲開始 [EP176-255] #小說 #繁體中文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lx1W-xi5aE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Qfu9hgfmB9IOhrITD1fLKK0Rf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