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京房山區修建文化硅谷工程時,無意中挖出了一座唐代夫妻合葬墓,經專家考古證明,墓主人叫劉濟,是唐朝的幽州節度使。

從考古發現可知,這座墓葬極其豪華,光墓道就有34米長,墓門、前庭、前甬道、耳室、壁龕、主室、側室、後甬道、後室一應俱全,棺床由6層漢白玉構成,形制如同帝王。
一個地方官員哪來這麼大膽子,就不怕帶來滅族之災嗎?
僭越這個詞,對中唐以後的節度使們來說,那就是個笑話,因為他們就是土皇帝,一不高興就“薅龍鬚”。
比如這位劉濟,他的節度使根本就不是朝廷任命的,而是從他爹那裡繼承的。他死後,其子劉總又接班,朝廷只能幹瞪眼。

這就是安史之亂後的後遺症——藩鎮割據。
劉家三代人割據幽州36年,卻在巔峰之際發生了父子兄弟相殘的事件。誰知,害人者被“鬼魅纏身”,嚇得出家避禍,卻離奇暴死。
劉家是如何走上割據之路的?為何會發生骨肉相殘的事?結局又如何呢?
☞忠義豪傑,劉怦折服幽州,被推為首領
幽州這個地方,原本屬於李懷仙的。

李懷仙是安史叛將,後來他歸降朝廷,為平定“安史之亂”立下大功,因此獲准出任盧龍幽州節度使,與成德、魏博兩鎮一起,形成最早的割據藩鎮。
不過“幽州土皇”可不好當,五年後李懷仙被部下朱希彩幹掉,四年後朱希彩又被朱泚幹掉,兩年後朱泚又被親弟弟朱滔驅逐,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城頭變幻大王旗”。
朝廷也曾經發兵征討,可是基本上都以失敗而告終,最終淪為橡皮圖章,誰上台就給誰發一道任命書,以顯示朝廷的存在感,像極了東周時期的周王室。
朱滔這個人很狡詐,但卻是有能力,他左右逢源,一會兒沖朝廷拋媚眼,一會兒又勾結成德、魏博、淄青幾位節度使,始終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唐德宗時期,他還搞了個“四國相王”,並被推舉為盟主。

朱滔對朝廷的背叛讓一個人很不滿,並且多次對朱滔提出批評,他就是劉怦。
朱滔可是個活閻王,劉怦就不怕被殺了嗎?劉怦還真不怕,一則他的母親是朱滔的親姑姑,二人是表兄弟,二則劉怦雖然話難聽,但對朱滔確實很忠心。
一個好玩的場景出現了,劉怦盯在朱滔身後不停嘮叨,朱滔一面嬉皮笑臉地表示“你批評得對”,一面我行我素。
這就是朱滔的過人之處,度量大,識人。他每次出征,總是任命劉怦為節度留後,將身家性命都交給這個大他19歲的表哥。
劉怦也沒有辜負朱滔,曾經有一次朱滔輸光了人馬,劉怦也沒有趁火打劫,而是出城二十里將朱滔迎接回來。

出於感激,朱滔在彌留之際,將幽州的軍政大權都交給了劉怦。朱滔去世後,將領們也一致推選劉怦為新任節度使。
屁股決定腦袋,當劉怦坐上幽州老大的座椅時,考慮問題的角度就發生了偏轉,他並沒有對朝廷表現足夠的忠誠,而是選擇了繼續割據當土皇帝。
三個月後,劉怦也病逝了,他將節度使大權交到了兒子劉濟的手上。
☞希望之星,劉濟誤中圈套,致父子相殘
傳說劉濟是黑蟒投胎,他出生時母親出現難產,折騰半天生出一條大蛇,周身黑氣升騰,嚇得接生婆和丫鬟們嗷地一嗓子,集體逃出產房。

不過,這條“大黑蟒”長大後一點凶煞氣都沒有,反而文質彬彬,又聰明伶俐。後來他還去長安參加科考,中了進士,28歲就官至刺史。
按劉濟的晉陞速度,未來封爵拜相是遲早的事。而一旦接老爸的班,就等於走上了對抗朝廷的不歸路。那麼,劉濟為何要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走險路呢?
這個問題觸及到了藩鎮割據的核心,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以豪門集團為核心的王朝,在那個體制下,豪門集團壟斷了所有的政治資源,寒族集團很難有出頭之日,科舉雖然緩解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但依然不能從根子上解決。

而藩鎮正是寒門庶族階級的天堂,這裡沒有豪門集團跟他們爭奪資源。因此藩鎮之亂本質上是代表豪門利益的中央,與代表地方利益的庶族階級之間的矛盾大爆發。
劉家不是唐朝的豪門家族,即便劉濟能靠科舉入仕,能靠自己的才華謀取高官厚祿,但永遠成不了豪門家族。但在幽州,他就是土皇帝,是所有資源的壟斷者,他至少有機會變成地方豪族。
兩相對比,你會選擇哪一個呢?反正劉濟選擇了接班。
劉濟跟父親的想法一致,既不願意跟朝廷鬧翻,但也不願意放棄根本利益,因此他選擇了最大限度地聽命於朝廷,只要朝廷認可幽州割據的局面就行。

本着這個思想,劉濟對朝廷輸貢不斷,言辭極為低調恭敬,朝廷有所派遣,他也義無反顧地去執行。
為此,他被譽為是大唐“開元復興”的希望之星。在我看來這很扯淡,他們根本沒看清事情的本質,否則劉濟為何不放棄割據?
不過,對朝廷來說,節度使們如果能像劉濟那樣聽話,那就燒高香了。很顯然,劉濟只是個案,幽州不會長久太平。
唐憲宗的削藩行動將劉濟帶進了旋渦,也斷送了劉濟的美夢。

由於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的反叛,朝廷給劉濟下旨,命令他出兵討伐。劉濟當然責無旁貸,他留長子劉緄為副節度使,留鎮幽州,自己和次子劉總一起,率領七萬大軍南下。
幽州軍勢如破竹,先後攻克饒陽、束鹿、瀛洲等地,斬敵數千,卻在進攻樂壽、博陸、安平時,劉濟病倒了。
主帥生病,幽州軍便停止了攻擊。同時,其它幾路友軍的進展極其不順,唐憲宗為了集中力量對付淮西叛亂,便同意赦免王承宗。
這場討伐就這麼虎頭蛇尾地結束了,劉濟拖着病體回到饒陽休養。

不料,城裡突然傳出一股流言:朝廷不滿劉濟裝病怠工,要任命副大使劉緄取代劉濟,使者已經到太原了。
劉濟不辨真偽,但心裡卻是慌了。朝廷削藩的態度很清晰,自己雖然夠忠心,但早晚也會上黑名單,說不定這個傳言就是真的。
流言越傳越真,過了幾天又說朝廷的使者已經到了代地,越過太行山就到幽州。
劉濟病糊塗了,他認為一定是劉緄勾結朝廷,背叛了自己,試圖趁自己不在幽州搶班奪權。於是他一怒之下,下令將身邊那些與劉緄交好的將領們屠殺殆盡,同時派使者勒令劉緄到饒陽來報到。

劉緄真的背叛父親了嗎?當然沒有,這一切都是劉總做的局。
劉總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一直覬覦着老爸的節度使之位。可問題是那個位子輪不到他,於是他便勾結黨羽想出了個陰損的招數。
劉濟上套了,氣得血壓上升,加上有病在身,因此口乾舌燥,不停地喝水。劉總趁機在父親的水裡加了點料,毒殺了父親。
弒殺父親後,劉總隱匿死訊,並以劉濟的名義,派人半途攔截劉緄,將他杖殺於涿州。做完這一切,劉總宣布劉濟病故,並順利接管了節度使大權。

☞窮途末路,劉總落髮自保,卻離奇暴死
朝廷對這一切渾然不知,還為劉濟的死而痛心,宣布輟朝三日以示哀悼,並按慣例同意劉總擔任盧龍幽州節度使。
劉總可不像劉濟,他對朝廷沒有半點忠心,更沒有大局觀。不久,王承宗再次反叛,唐憲宗又二次對成德軍發動圍剿。
劉總也接到了出兵的命令,不過這傢伙大耍陰謀,他蛇鼠兩端,兩邊撈好處,就是不動真格的。

隨着淮西叛亂的平定,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憂懼而死,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被殺,加上主動入朝的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河北藩鎮僅剩劉總一人孤零零地戳在那裡當靶子了。
這夥計怕了,部下譚忠也勸他說:天下分久必合,河北已經亂了六十年,該到了統一的時候了,那幾家都完了,咱怎麼能獨保呢?
於是劉總給朝廷上書,提了兩個建議:其一,放棄割據,自願入朝為官;其二,將盧龍幽州節度一分為三,分而治之。
這個代價是不是太大了?變化也太快了吧?完全不符合劉總亡命徒的性格嘛,他在搞什麼鬼?

咱還真是冤枉劉總了,人家確實是誠心誠意的,因為他被冤魂纏身,再不悔過自新就性命難保了。
咋回事呢?原來劉總弒父殺兄後落下了心病,總覺得父親和哥哥的陰魂纏着自己不放,搞得他坐卧不寧、寢食難安,幾乎被嚇出了精神病。
劉總給劉濟修那麼豪華的大墓,估計就是想求老爸手下留情,可惜沒管用。
沒辦法,他只好厚着臉皮請來數百名和尚做法事。法事沒少做,效果也見到了,只要和尚在他就覺得很安心,和尚一走他就又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夜間,別說睡覺,連獨處都不敢。

就這樣,劉總被折磨了幾年,終於無法忍受了,他決定釜底抽薪——出家當和尚。在保命的前提條件下,權力已經不重要了。
朝廷接到劉總的上書都被整懵了?咋回事呢?誰家倒貼錢嫁姑娘?這夥計吃錯藥了?還是耍什麼花招?對,一定有陰謀。
劉總急了,咋還不相信呢?誠意不夠嗎?那行,再加碼,他又給朝廷一下子送去一萬五千匹馬。
朝廷要是再推諉就顯得眼眶太淺了,於是嘗試着派人前去落實。沒想到使者到了幽州一看,人家劉總已經剃了個光頭,穿着一身僧衣,一副慈眉善目的樣子。

幽州的軍頭們不幹了:俺們不願意跟朝廷干,你不能走。劉總人生中最後一次舉起屠刀,他下令將帶頭鬧事的十幾個將領咔嚓了,然後將節度使符節交給了使者。
使者都被感動了:陛下欽賜你法號“大覺”,並在長安迎接你。
劉總擔心部下再次阻攔,於當天夜裡偷偷上路離開了幽州。不過,唐穆宗並沒有等到活着的劉總,這位誠心皈依的“大覺”,半路上真的“大覺”了,一點徵兆都沒有。
讓人汗毛倒立是,護送劉總靈柩抵達長安的“健男子”譚忠,也莫名其妙突然死了。史書說到這裡戛然而止,欲言又止,您覺得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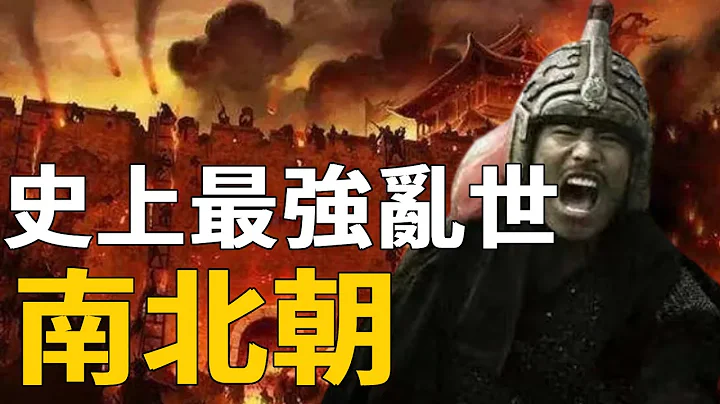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