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拖待變
日本侵華之初,蔣介石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和日本單獨對抗。九一八事變發生次日,蔣介石便在日記中寫道:“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
一.二八事變之後,面對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實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蔣介石認為必須爭取時間,以拖待變。一方面可藉此加緊增強自身國力,另一方面,隨着日本侵華的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勢必會引起國際上的干預。

▲一.二八事變中,進攻上海的日軍
尋求國際干預,這是從日本侵華開始,蔣介石一直想要達到的目的。但這個目的,直至1941年底,日本自尋死路般的挑起了太平洋戰爭,才得以完全實現。
蔣介石此時的處境:戰不能戰,和又不能和
1933年3月至5月的長城抗戰,以一紙屈辱《塘沽協定》而結束。對於此結果,蔣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蔣的“我屈”,已見諸事態,而“國伸”,則沒有看到任何痕迹,日軍仍在一步步加緊侵略中國。
一個《塘沽協定》,便能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對之聲。更不用說主動對日講和,承認其侵略行徑,臣服於日寇了,這是蔣介石所不敢做的。他知道,一但這樣做,國民政府必定倒台,他也必將成中國的千古罪人。

▲《塘沽協定》簽字儀式上的中日軍方代表
為“促倭方之醒悟”,蔣介石以徐道鄰之名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
在這種戰又不能戰,和又不能和的情況下,為打開僵局,“促倭方之醒悟”,1935年1月中旬,由蔣介石口述,陳布雷記錄,最終形成《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

在當時情況下,此文肯定不便以蔣介石或陳布雷之名發表。此時陳布雷想到了一個人——徐道鄰,他認為:“徐道鄰者,徐徐的與鄰邦道來也,名字具有‘深意’”。於是此文便以徐道鄰之名發表於1月下旬出版的《外交評論》上。
徐道鄰是誰?他是北洋政府時期要人徐樹錚第三子,1931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學博士,1932年返回中國,並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
《敵乎?友乎?》,充滿了中日親善的幻想
文章一開始就表示:“日本人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渴望與日本親善友好。
隨後先指出“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比如判斷對方的錯誤、內部凌亂的錯誤、感情用事的錯誤等。接着又指出日本方面的錯誤,比如對中國認識之錯誤、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自造錯覺的錯誤等。並指出錯誤更多的應是日本。
文中還告誡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國或蘇聯為預想敵,則中國為其側背。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內滅亡中國,要施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時間,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
其後又寫道:“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日本要想“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以它國力,顯然是做不到的。
文中還講明了中國方面的要求,即要求日本“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 泥。”
其實蔣介石明白日本人是決不會自動放棄東北的,“余知日人對我東北之心理,寧使其東京或日本三島全毀,決不願自動退出東北也。”這點蔣介石心知肚明。
文章最後拋出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
這個“上段所說的途徑”,就是日本“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對於日本來說,這可能嗎?
《敵乎?友乎?》所提“解鈴還須繫鈴人”雖不現實,但至少向日本釋放了一個和談信號。

▲早在1927年6月的東方會議上,日本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已明確提出了侵華方針
中日關係看似緩和
文章發表後,日本方面看明白此文即便不是蔣介石親自所寫,也為蔣介石授意所作。於是各刊物相繼轉載,一時間和平談判的空氣散布四方。
2月14日,蔣在江西牯嶺接見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談中日親善問題。蔣認為中日提攜,“首當以道義為出發點。”對於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華政策的演說,蔣則認為“至少可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再次表達了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
此時正好王寵惠準備前往海牙赴任國際法庭法官,於是蔣命王為其私人代表。1935年2月19日,王寵惠在去海牙前先抵達日本,並兩度與廣田弘毅會晤。對於這次日本之行,王寵惠在離開日本時表示“結果圓滿”。
蔣介石在2月28日日記中寫道:“……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贊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字裡行間表露出對時局發展的滿意。
之後5月間,中日兩國使節升級,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中日關係看似有了緩和。
幻想的破滅
但蔣介石顯然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從1935年5月開始,日軍在華北製造一系列事件,並以此為借口,企圖推動華北五省自治。當年10月,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對華政策新方針,即"廣田三原則",使日本的野心赤祼祼的暴露在世人面前。

▲1935年11月,日軍在華北扶植了中國內地第一個傀儡政權: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在蔣介石這一時期內的日記中,字裡行間已沒有了之前的從容與自信,更多的是憤恨和對時局的失望:
“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此次事變,實等於九一八鉅禍。”(1935年6月30日)
“倭寇橫暴狀態,已無和平之望。”(1935年11月28日)
華北事變使蔣介石深感中日戰爭已無法避免,加之此時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被迫開始長征,這讓蔣認為“內患”已除。雖然之後蔣仍沒有放棄對日和談,但國民政府的國防建設與對日戰爭準備,從此開始加速付諸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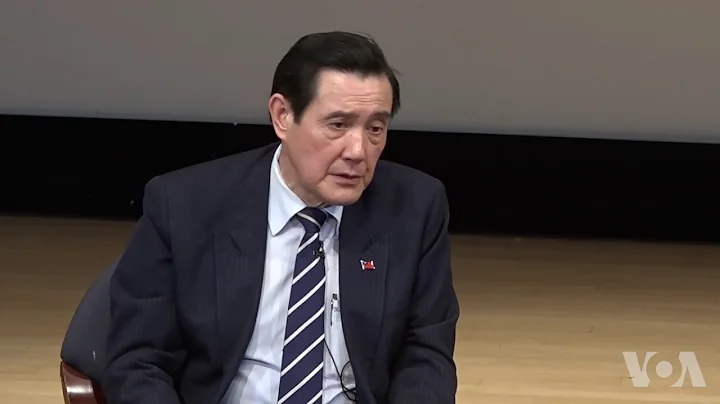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