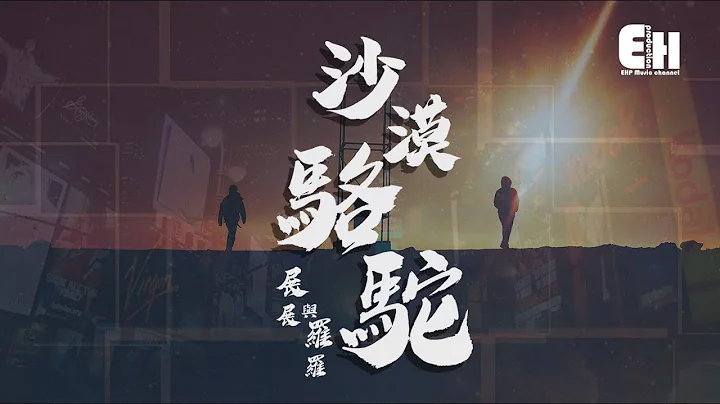新京報記者從西藏浪卡子縣人民醫院、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獲悉,8日凌晨3時許、7時許,中國著名藏族導演、編劇、作家萬瑪才旦因在拍戲時出現高原反應,先後在這兩家醫院接受搶救,搶救無效後離世,享年53歲。8日19時許,新京報記者又從萬瑪才旦弟弟處獲悉,萬瑪才旦繫心臟病突發逝世。

在萬瑪才旦的短篇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中,收錄的第一篇便是與書名同名的短篇小說,小說里講到“我”來自一個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機構,主要工作以搶救整理出版一些將要消失的民間文學作品為主。有一天,“我”請假來到村裡找一位老人把之前沒有採錄的最後一個故事給錄完。老人給他講了一個“故事”,但講到一半,老人突然劇烈咳嗽起來,因為身體原因沒有繼續下去。結果,凌晨的時候,“我”接到老人女兒的電話,“阿爸剛剛走了”。在談到這種開放式的結尾的設置時,萬瑪才旦表示,他覺得故事講到一半突然停下可能會更加有意思,小說的故事內容和講述形式都很重要,他執導的一些影片也是如此,比如,《塔洛》為什麼要用黑白影像?《撞死一隻羊》為什麼要用四比三的畫幅?現實和回憶為什麼要有色彩上的區別?這些都是萬瑪才旦在電影表現形式上的探索。他還有太多探索要嘗試。

萬瑪才旦在影片《陌生人》開機儀式上。
對萬瑪才旦來說,他熱愛的電影故事也只講了一半。去年11月,他編劇的愛情故事片《祝你旅途愉快》正式立項;由萬瑪才旦編劇、導演,黃軒主演的新作《陌生人》今年3月底剛宣布殺青;在今年4月底舉辦的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萬瑪才旦擔任了“注目未來”單元國際評審團主席一職;在他去世前一天,他還在朋友圈“祝賀年輕的電影人”。他還有太多故事要講述。
創造了藏族電影和小說雙子座的高峰
這些年,萬瑪才旦在電影方面得到的肯定比較多,《靜靜的嘛呢石》(2005年)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處女作獎,《尋找智美更登》(2007年)拿下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委會大獎,《塔洛》(2015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撞死了一隻羊》(2018年)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氣球》(2019年)獲得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椰獎……
不過,萬瑪才旦最開始是文學出身,這也與他之後執導的電影作品有很強的文學性有很大關係。他很小就喜歡電影,但當年高中畢業去專業學校接受系統的電影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的經歷就是先讀文學,文學的愛好一直沒間斷過。他十幾歲開始自發地寫了一些小說,完全不是為了發表或者其他目的,也不知道寫下來要幹嗎,有了表達的慾望衝動就寫。他中專上的是師範,讀的是藏語言文學專業,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藏文化,而漢語是通過大量閱讀文學來掌握。那時候上大學還是說方言,大家都不說普通話。
畢業後,萬瑪才旦當了三年的小學老師,當時讀了比較多的中國近代現代文學作品,比如魯迅的作品等。他還接觸了一些比較大眾的作家,比如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回憶,在那個年代讀這些書很是激動,一口氣就讀下來,有閱讀的快感。他還通過一些國內作家的作品了解不同的創作方法,比如說荒誕派、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等。
不論是之後創作的小說,還是電影,萬瑪才旦創作的源頭還是來自藏地的自然環境和宗教文化。
萬瑪才旦閱讀了大量藏族文學,包含歷算、梵文等很多學科。經典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讀僧侶文學和民間文學,他受這兩方面的影響很大。比如民間文學喜歡重複的寫作方法,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而藏族文學的經典作家很喜歡奇幻化或魔幻化的表現,它後面有很強大的佛教文化做支撐,比如經典的《米拉日巴傳》就是這樣。可能跟自己所處的文化宗教信仰有關,萬瑪才旦對荒誕派或象徵主義的作品很感興趣,更有親切感,也更喜歡馬爾克斯、卡夫卡這樣的作者。
所以,萬瑪才旦的小說和電影在寫實的基礎上,往往也會有一抹超現實的筆觸和濃濃的宗教意味。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司機金巴和殺手金巴在茶館的同一個場景同一個位置坐下,畫面反映出兩人的關聯。
《撞死了一隻羊》將拍攝地搬到了海拔5500米高的可可西里無人區,用鏡頭記錄生命個體的情感和處境。該片用4:3畫幅,並且用三種色彩對應三個不同時空,關於回憶和夢境的處理讓影片十分寫意。萬瑪才旦設置了三個時空,現實時空、回憶時空以及片尾的夢境。現實部分用了彩色,回憶部分則用了黑白,而夢境則用了一種類似油畫的色彩。茶館那場戲,每次老闆娘回憶殺手金巴的時候,黑白鏡頭都做了虛化處理,故意模糊兩個人的身份,製造一種夢幻、虛幻的感覺。影片《阿拉姜色》的藏族導演松太加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對記者說:“這部片子可能是他以往所有的片子裡面,最接近他文學氣質的一部。”
電影《氣球》中,兩個藏族孩子將父母的避孕套當氣球玩耍,母親卓嘎意外懷孕,爺爺突然去世,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認為是突然去世的爺爺的轉世,在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孩子到底“生還是不生”,一家人陷入了尷尬而又難以抉擇的境地。
而他在小說中更是多次重複“生死輪迴”的宗教命題。比如在小說《水果硬糖》里,一位藏族母親養育了兩個兒子,一個成為醫生,一個成為活佛。在另一篇小說《特邀演員》中,一個劇組來到藏區拍戲,想邀請一位老藏民做特邀演員,但藏民以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將來死了靈魂得不到解脫為由拒絕了,但之後因為妻子生孩子需要錢,又同意作為特邀演員。

《塔洛》全片用黑白影像拍攝。
這些年,萬瑪才旦一直用文學和電影兩條腿走路,文學滋養了他的電影,電影又反哺了他的文學。他執導的電影《塔洛》《撞死了一隻羊》等都是由他的小說改編而成,而《氣球》則是先完成了電影劇本,又改編成的小說。
西藏自治區文聯主席、藏族著名作家扎西達娃曾稱讚萬瑪才旦“創造了藏族電影和小說雙子座的高峰”。
對藏族電影人來說,萬瑪才旦是導師和伯樂
藏語電影的真正發軔之作,還是當時36歲的藏族導演萬瑪才旦於2005年執導的《靜靜的嘛呢石》,此後十餘年,萬瑪才旦扛起了“藏地電影”大旗,還培養了一眾“後輩”,松太加和拉華加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於2011年導演了自己的處女作《太陽總在左邊》,隨後又執導了《河》《阿拉姜色》,後者於2018年導演了處女作《旺扎的雨靴》,藏族導演的群像逐漸顯露,開始形成一種氣象,甚至已經有人將萬瑪才旦、松太加和拉華加等導演和他們的作品稱為“藏地新浪潮”。但即便如此,“藏地題材電影”在目前的國內電影市場仍然處於投資少、題材過於單一的困境。
萬瑪才旦以“傳幫帶”的方式發展了眾多“後輩”,將藏地題材電影從人跡罕至處和仰視符號化逐漸拉回到大眾視野,令觀眾從平視角度更接地氣地了解到藏地文化及藏民的精神生活。
萬瑪才旦先後就讀於西北民族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他是中國導演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員。萬瑪才旦就讀西北民族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其作品曾經獲得多種獎項。他的很多電影都改編自個人的小說,有很強的文學性。從2005年執導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開始,他先後憑藉《尋找智美更登》《塔洛》等反映現代藏民生活的優秀影片,頻頻在海內外獲獎,為藏地電影贏得了廣泛的關注。而對於松太加和拉華加等優秀藏族電影人來說,萬瑪才旦如同是導師和伯樂。
松太加比萬瑪才旦小5歲,據松太加回憶,兩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認識了。因為都熱愛文學,在地區文聯組織的文學筆會上認識並熟絡起來後,發現都喜歡電影,筆友開大會的時候,他倆就跑出去聊電影。有一年,萬瑪才旦去找松太加,說自己已經去北京電影學院學習了,建議松太加也去。
松太加至今還記得,當時萬瑪才旦領着他坐着綠皮火車到了北京。因為萬瑪才旦學的是編導,他就建議松太加學攝影,將來可以一起搭伴拍一些片子。松太加就在攝影系進修班學了一年,第二年跟着萬瑪才旦到文學系蹭了一年的課。藏地電影人這種傳幫帶式的精神在松太加這裡得到了延續。已經獨立執導了四部長片的松太加,現在有一個18人的創作團隊,全部都是藏族年輕人,有高中畢業的,有大學畢業的,還有出家還俗的。松太加手把手教他們,如何寫劇本,給他們提出建議,“他們很用功,也在關注戛納(國際電影節),在聊這些事,挺有意思的。”

松太加(左)和拉華加(右)兩位藏族導演在創作上都曾得到過萬瑪才旦的幫助。
拉華加在2005年的時候就知道了萬瑪才旦,“萬瑪老師當時拍了自己的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轟動了整個藏區。”那時候電影在藏區還不是很普及,很多人對電影也比較陌生。2010年,拉華加通過哥哥認識了萬瑪才旦,萬瑪才旦建議他去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藏語言文學,“他建議我先去學文學,了解自己民族文化方面的東西”,之後拉華加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專業。拉華加利用假期時間去跟組,最開始做導演助理、翻譯、演員輔導等工作,後來到了萬瑪才旦《塔洛》劇組中就已經成為執行導演。拍攝自己的導演處女作《旺扎的雨靴》之前,拉華加跟了六七個劇組,《旺扎的雨靴》的班底也基本都是萬瑪才旦的團隊,還有拉華加之前跟組時候合作的熟人。
寄希望當代年輕藏族電影創作者,多做類型嘗試
藏語電影作品最近幾年在國際各大影展很活躍,也獲得一些獎項和關注,似乎給大家營造出一種很有國際影響力的印象,但萬瑪才旦認為並不是這樣,“這方面可能有一個誤區,大家就覺得藏族本身的原因,可能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其實這是很難的。我覺得這個跟在中國電影市場裡面是一樣的,放大到國際市場,它還是以電影本身為主。比如說一些電影節,它看重的是你作品的內容和聲音,而不是看你的題材。現在涉及不同民族、各種不同文化的電影作品真是太多了,所以單純靠一個題材想吸引眼球,希望有發行上的優勢,我覺得很難,基本上不可能。很多電影節的標準肯定不是以題材為準,不會因為你是藏族題材就去選你。”
萬瑪才旦說,其實藏地電影很晚才出現,跟他們的整體處境有關係。好些少數民族地區有電影製片廠,比如內蒙古有內蒙古電影製片廠,新疆有天山電影製片廠,但整個藏地就沒有一個電影製片廠,青海、西藏都沒有,只有譯制廠。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一些漢語電影譯成藏語,在藏區發行。這裡的電影工業基礎比較薄弱。

萬瑪才旦所著短篇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封面。
萬瑪才旦認為藏語電影因為處於剛起步階段,它在內容的豐富度和類型的多元化上還比較欠缺,導演在創作的時候選取的題材就相對比較單一。比如《阿拉姜色》與《岡仁波齊》都有去拉薩朝聖的劇情,《皮繩上的魂》和《撞死了一隻羊》都涉及了“復仇”與“救贖”的主題。
萬瑪才旦導演認為,首先要做一些類型上的嘗試,這可能要寄希望於更多當代年輕的藏族電影創作者,因為他們年輕,在學習電影的過程中,會呈現出對不同電影類型的興趣。他從這兩年的一些藏族學生短片中看到了這種希望。其次,要在題材挖掘的廣度和深度上加強,可以找一些既涉及藏地,又涉及內地的中間地段題材。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作者的轉向,很多人也會問到萬瑪才旦導演將來有沒有可能做藏族題材以外的電影,萬瑪才旦導演表示,“如果將來條件成熟了,也有感興趣的題材,可以去做”。
2020年,萬瑪才旦在一次演講中分享了自己學習電影、拍攝電影的一些經歷,“時間的力量讓我們成長,讓我們逐漸明白很多的道理,逐漸成為你想成為的人,但在這個過程中你必須得耐住寂寞,必須得在時間中等待,等待機遇的到來。”
新京報記者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海報設計 劉曉斐
校對 劉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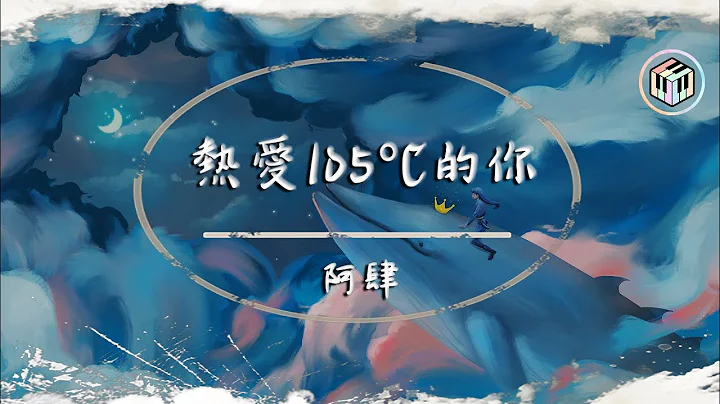
![[TOP7]數個令人傻眼的究極料理法 | 對Toyz批評米其林餐廳的看法 | 20萬火柴超高效燒雞法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kiX4acKSFA/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CvxZbd-PqTybEDKJnkD2UB61OF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