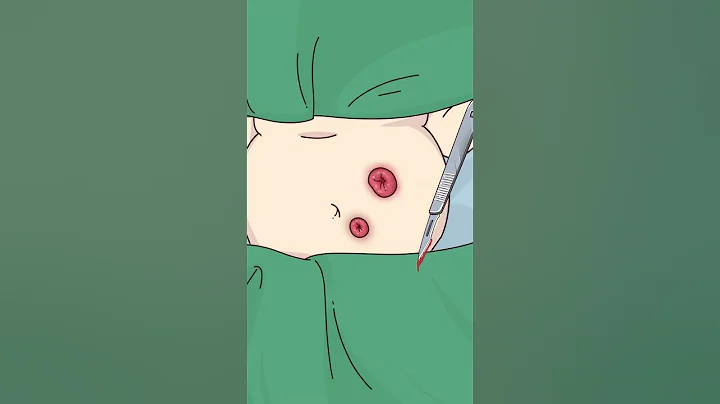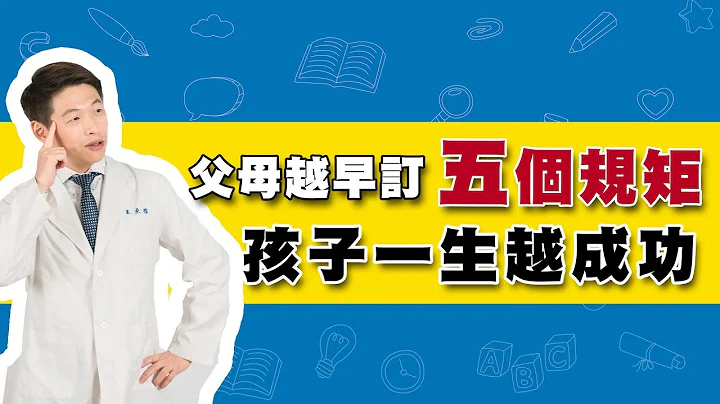昨天講了兩個版本的《孩子王》,還沒有介紹是個什麼故事。
就是講知青老稈(因為瘦,得了這麼個綽號,電影是謝園演的,那時他的全盛時期),被安排到農場的學校教書,教的是初三,老稈很忐忑,畢竟他只上過高一。雖然當老師也要帶學生搞勞動,但畢竟要輕鬆很多。
學生程度不一,每天學的都是一些口號,課文里講的也是階級鬥爭,語文課上毫無文學性可言。前任老師的教法都是給課文分段、寫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等,連學生都會的流程。
老稈與學生磨合一段,覺得雖然他們初三畢業也沒有高中可上,但既然來了學校,總要實實在在學到點本事,比如能寫信、寫文章,將來能用得上。
他就先教生字,再讓他們寫作文,唯一的要求是,老老實實記下發生的事,不許抄,就算流水賬,也比抄一些套話要好。
初三的學生,頭一次寫自己“上學”,寫出來是這樣的:
“上學,走,到學校教室,我上學走。”
全班鬨笑。但老師說寫得好,至少說了一個“走”,就有了獨特的內容。
第一次作文,寫得最好的是王福,他寫的是:
“我家沒有表,我起來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臉,我去伙房打飯,我吃了飯,洗了碗,我拿了書包,我沒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霧,我到學校,我坐下,上課。”

王福是班裡最認真的學生。他認得三千多字。只是閱讀資料過於缺乏,如果不是抄報紙或複述老師的話,他們基本上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而認得三千多字的王福寫的這一篇,電影里謝園念出來,差點把我看哭了。
有人說,如果你不知道寫什麼,就起身出門走二十分鐘,把看到的寫下來。大約就是這樣的訓練。
電影里有很多簡筆畫,猙獰的面孔,頭大,軀幹小,但筆觸純熟,老實說一看就是美工畫的。而阿城幫學生們寫的這兩篇“作文”,有開天闢地的樸拙,比“紅旗飄揚,戰鼓震天”好。

畢加索十幾歲的時候,素描就可以畫得跟拉斐爾一樣好,但是他一輩子都在追求像孩子一樣畫畫。
阿城要求的文字,也是講究一個真心誠意和返璞歸真。
說到畢加索,想起《少年凱歌》里陳凱歌講過,他出生前不久,北京召開“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會標就是畢加索的鴿子。於是父母就給他取名“皚鴿”,皚就是潔白。他十三歲時長到一米八,覺得自己已經與鴿子無任何相似處,於是改名“凱歌”。但“皚”的讀音是“挨”,用的他父親名字“陳懷皚”中的一個字,會不會這個字在表示“潔白”的義項下,還有一個“凱”的讀音?另一種可能性,是按照他父親老家福建長樂的閩南語發音,“皚”與“凱”相近?總之,這是一個問題。

說回阿城教孩子寫作文。
王福下回交上來的作文,讓老稈“吃了一驚”。他寫的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世界中力氣最大的人。他在隊里扛麻袋,別人都比不過他。我的父親又是世界中吃飯最多的人。家裡的飯,都是母親讓他吃飽。這很對,因為父親要做工,每月拿錢來養活一家人。但是父親說:“我沒有王福力氣大。因為王福在識字。”父親是一個不能講話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隊上有人欺負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學文化,替他說話。父親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後來慢慢爬起來,還要去幹活,不願失去一天的錢。我要上學,現在還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陽,父親在山上走,走進白太陽里去。我想,父親有力氣啦。
真是又樸實,又有故事,有反轉,還有詩意,一個字一個字似乎都是從心裡流出來的:“早上出的白太陽,父親在山上走,走進白太陽里去”,是極好的詩。

老稈寫了一首歌,其中有兩句:
腦袋在肩上
文章靠自己
有點民國老課文的味道。
但老稈終於因為沒有按教學大綱教學,又與學生打賭的事,被學校退回了生產隊。
這麼多年過去,在“寫作”這一項上,進步還是有限,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高校學生普遍寫作能力偏低,近來這許多的學術造假,以及前不久爆出的留學生作弊被國外名校勸退等,都是腦袋沒長在自己肩上,要到老稈的課堂上去回爐的。

畫家劉小東筆下的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