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我常常見識到這樣奇怪的現象:
有家長開車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把汽車隨意停放在校門口,根本不顧造成交通擁堵;有家長牽着孩子過斑馬線,旁若無人地闖紅燈……就是他們,諄諄教導自己的孩子要有規則意識。
有人在酒桌上口沒遮攔噴這噴那,然後轉頭叮囑身邊的孩子:你出去不要亂說哈。
有人一邊在桌子上打麻將,一邊高聲斥責孩子:快去做作業。
有人對工作極不負責任,已經混成單位的賴皮,卻在對孩子進行責任感教育……

作為父母,我們不僅孕育孩子生命,還承擔著哺育他成長,養育他成人,教育他成才的責任和使命。這是人類的遺傳密碼,是生物進化論,是天性使然。
無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這一職位無需上崗證,無需考核,無需年檢,與學歷、金錢、地位關係不大。孩子無法選擇,父母也無法選擇。但是,做好第一任老師,卻需要智慧。愛的智慧,教育的智慧,成長的智慧。
我們在成為父母之前,除了接受自己父母的教育,也已經接受過正規的九年義務教育,大多數還接受過高中教育,現在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也不小。走上社會後,我們還接受了社會教育,職業教育。
但是,一旦為人父母,所有的人還需要從頭學習一門“教育孩子”的全新課程。它包含從愛情到肉體,從懷孕到分娩,從遺傳學到營養學,從胎教到新生兒保育等宏大課程體系的學習和實踐。我書櫃里至今還存放着幾大本“育兒大全”之類的書。看到這些書,便想起當年初為人父時刻苦鑽研,以致照本宣科的笑話。
怎樣才能做好第一任老師呢?我的答案是:在教育孩子的同時,不斷向孩子學習,讓孩子成為自己的最後一任老師。
初生嬰兒躺在搖籃里,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他的眼睛閃着金子般的光芒。我凝視着孩子,反省自己已然銹跡斑斑的靈魂。如果我不向孩子學習純潔,我有什麼資格以腌臢去教育明凈?
童年時代,孩子天真爛漫,無憂無慮。而我已經在社會中學會精於算計,善於虛應,如果我不向孩子學習簡單與快樂,我有什麼資格用陰暗去教育明媚?
少年時代,孩子積極陽光,努力上進,而我已經滿身疲乏,安於現狀,如果我不向孩子學習奮發,我有什麼資格以懶散去教育勤勉?
不用擔心孩子永遠生活在童話里,與我們所謂的現實比起來,憑什麼非得讓孩子認清現實,而不是我們回歸童話?
孩子長大了,我們需要向孩子學習的東西更多。比如他所具備的新知識新觀念新思想,比如他的待人接物與為人處世,比如他的抗壓,比如他的堅持,比如應對複雜局面等能力。
即便在一些細枝末節的處理上,孩子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舉我孩子的例子:孩子遠在他鄉,且與他老子已數年未見面,卻常常打電話清候我:“這周回老家看爺爺奶奶沒有?”孝順我當然懂,但孩子的嘮叨簡直如老師的教誨一樣親切。這樣的孩子,你哪裡會擔心其有家不歸?
比如當我在網上掛文章時,想到他常常要發表讀後感,便油然而生學生交作業的感覺。因為他會告誡我:寫作怡情,不要虛假,不要違背常識,不要低俗,不要胡說八道,不要為老不尊。
至於涉及家國情懷的大是大非上,我也選擇相信年輕人的判斷力和定力。比如我孩子在讀大學時,有一年參加一個國際性質的支教活動,與日本、印度、美國等學生組成支教團赴菲國支教。剛到學校時,校長對國際學生一視同仁,安排宿舍,陪同參觀,布置任務……但在當晚舉行的歡迎會上,在自我介紹環節,當他介紹來自中國時,剛剛還笑臉相迎的校長立馬換了冷麵,而且會後把他的寢室從美國大學生那裡調出來。
那晚,他在電話里向我報告這一嚴重不公事件,稱是遇到了奇恥大辱。他激動地說,你可以羞辱我個人,但你不能輕蔑我的祖國。
聽罷這句話,作為他的父親,已可寬心:我不會培養一個白眼狼。
顯然,在如此重大的關節面前,以我的經歷已經無法給予他具體的指導。最後,孩子選擇了不卑不亢迎接挑戰,把支教工作做到最好……十幾天支教工作結束後,偏見而高傲的校長終於真誠地向他道歉。
爸爸,這是向中國人道歉。他在電話里興奮地告訴我。
對的,孩子,你用實際行動,擦亮了“中國人”三個字的本色。
……
如果我們不俯下身來,建立起與孩子同等的對話平台,我們有什麼資格以權威去教育民主?
當我們以“向孩子學習”的姿態去“教育孩子”的時候,就會發現,在孩子健康成長的同時,自己也會逐漸變得溫潤,大氣,有內涵。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我們和孩子的角色已經互換,孩子已然成為我們的老師,而我們也樂於當個聽話的好學生。
作為孩子的最後一任學生,你會從孩子那裡拿到合格父母的畢業證嗎?

(圖片來自頭條推薦圖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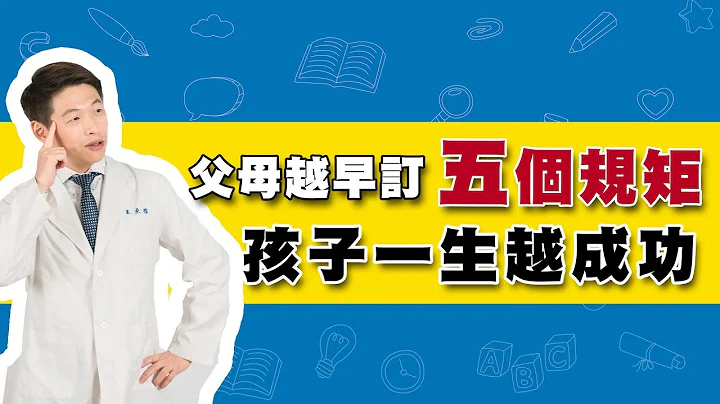








![[Chinese movie 2023]Poor girl helps disabled shareholder, changes fate!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2qSlT5aVHg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zmX0URNZaXthUulfqkBykMpzB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