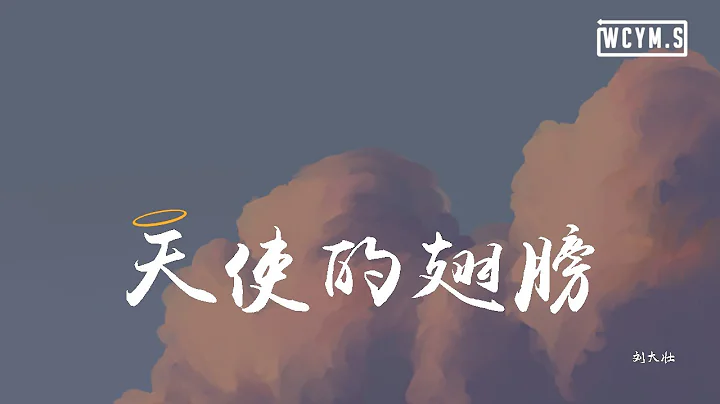这段时间再看《天下长河》,就聊一聊陈潢陈天一。

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名字,是在二月河的小说《康熙王朝》里面,高士奇赠此人外号“水耗子”,说他又黑又瘦,还让康熙的爱妃,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十三阿哥他娘宝日龙梅念念不忘了一辈子,最后也是因为治河累病交加英年早丧。
中国人最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治河这个属于土木工程的,又看不懂又没意思,所以千古下来,能在这上面留下名字的,前前后后都没超过10人。但是因为治河搞得改朝换代,那倒是一数一大串,隋朝和元朝就栽在这上面。
然而治水太重要了,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居世界首位。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最为频繁和严重的有四种:水灾、旱灾、地震灾和海洋灾。这四种大约占全部自然灾害的90%,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占到一半还要多。中国水旱灾害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都有详细的记录,总计发生较大的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平均每年发生一次大的水旱灾害。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由于中国东南部的国土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每年的雨水基本上集中于3~4个月之中,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且时空变异性强,这种水文特性为世界罕有。自然灾害频繁使农业生产容易发生灾荒,如果不能及时救济就会演变为饥荒。
春秋时代齐国的国相管仲曾经有一句名言,“治国必先除五害,五害之中以水为大”,这就是“治国必先治水”的由来。
在这里还必须得提到黄河,黄河不仅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也是最复杂难治的河流。历史上黄河大迁徙共有7次,在4230年间堤防溃决约1580次。黄河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天津,南到南京,泛滥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饿殍满地哀鸿遍野。这是抚育我们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带来滚滚灾害的长河。
所以从古至今,治水这事,没有足够的钱粮,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高瞻远瞩的规划和无比坚定的决心,这根本就是想都别想的事。
是治水,更是治国。不过对陈潢来说,他就只管治水,他的人生他的激情全部都是黄河。他身上有着孤勇者的孤独和坚定,就跟一把利刃一样,一往无前又带着易碎的锋芒。

撇开治水,这人的情商基本就属于马里亚纳海沟,靳辅告诉他要遵守官场潜规则,不要替自己求情,他不,处处逮着机会就要为靳辅伸冤,
跟大家商议开会,他把在场的所有人都diss了一遍,搞得弹幕连连弹出这句话:大哥,你说得很好,不要再说了。或许从那时候开始,就注定陈天一不得善终。

要不是靳辅,我都深刻的怀疑他能不能活到第二十集,还是康老三精明,他让陈潢担任靳辅的幕僚,不给他官做,省的自己天天跟在背后擦屁股。
再到后来,面对着刚愎自用的康熙,陈潢依旧不肯后退半步——这其实是我觉得这部剧拍的很有深度的地方,人是会变得,哪有千古卓绝的圣天子,只有权谋老辣愈发不得见他人挑战权威的老帝王。

哪有那么多的忠臣孝子,只有一大堆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凡人。
于是我忽然想起白起,那位在长平之战立下不世之功的战神,那也是和陈潢一样的头铁,坚定地站在技术层面上,用战场形势,人心变动,士兵伤亡以及国际形势,企图和秦王进行一场技术辩驳,要用技术的正确性,来说服帝王内心的专制。

然而秦王要的不是这个,他和康老三在意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简在帝心,你是忠于你的良知你的道德你的技术,还是忠于我?

我曾经以为,太纯粹的人或事物,往往就是世间留不住的,后来才明白,不是留不住而是不想留。
最终白起自刎,而陈潢也病逝于狱中。史书上对于陈潢的结局写得很清楚:
“陈潢以屯田事,触犯地主豪绅,遭到江南道御史郭琇等参奏,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的罪名被削职,“解京监候”,怀恨而死”。
这部戏的导演是这么说的:历史上靳辅和陈潢的结局是悲剧,但全世界的史诗,永远都在描写失败且死去的英雄。

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成功不是活着赢得什么,这只是最小的成功。诸葛亮北伐成功了吗?岳飞北伐成功了吗?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人格和高贵的精神。我们把成功分为三种:立功、立德、立言。施琅收回台湾属于立功,靳辅、陈潢不能终其功业,但他们的精神永存,人格光照万古。死亡,恰恰是他们成功的开始。能在黄河边,让百姓心甘情愿为之立雕像的没几个人。
还好,时间和民心会还以那些无私者公道,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郁可唯 Yisa Yu [ 路过人间 Walking by the world ] Official Music Video(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插曲)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FMl7GEaYwAE/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C_eDeODE6QsO_epuLU4V3PxWir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