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个炎热的午后,夕阳的余晖,透过破旧的草房窗户洒在地板上,映出斑驳的光影。
房间里飘散着炊烟和一阵激烈的争吵。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穷苦,孩子们一起受罪,你就一点办法都没吗?”
一个消瘦的中年农妇,从炕上跳下来怒吼道。
她的丈夫孔宪权,一名残疾的瓦匠,正沮丧地蹲在炕沿上,一句话也不敢说。

两孩子躲在灶台后面,悄悄地抹着泪水。
孔宪权颓然地看着,妻子嚎啕着跑出屋外,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
残废的腿,不再允许他从事更好的工作,可家里的生计却日渐困难,他该如何是好?
屋外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孔宪权目光落在墙上那张破旧的老照片上,那时的他英姿勃勃。

这一夜,孔宪权难以入睡。
不经意间,想起报纸上一个熟悉的名字——杨勇司令。
一刹那,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一线曙光。
一封满载期望的信寄往远方,没过多长时间,竟然真的收到了令人激动的回信。
梦寐以求的转机出现!

“泥瓦匠”孔宪权,究竟是什么身份?
上将杨勇又给他安排了什么身份?
贫瘠的生活,新的希望
1926年的一个秋日黄昏。
十几岁的孔宪权,背着锄头,独自走在村头的小路上。
落日的余晖洒在他单薄的背影,拉出了无比的长长的影子。
这个年纪的孔宪权,本应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待。
然而他清瘦的面庞上满是疲惫,他那双本该灵动的双眼,此时却无神放空。

他刚结束一天的辛勤劳作,依然填不饱肚子。
这已经是他生活的常态。
为了糊口,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进山,直到天黑才喘口气。
可依然改变不了家里的穷日子,双手和双脚,都已经被劳作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这天,当孔宪权经过村口时,他恰好看到几个陌生人正在村民中间说着什么,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同志们,跟我们翻身解放吧!”
一个身着军装的青年,正宣传着革命道理,号召百姓一起起来反抗剥削。

孔宪权一下来了精神,那无神的双眼中也恢复了希望的光彩。
他情不自禁地跟了上去,终于找到心中期盼已久的出路!
新兵擒获师长
1930年12月的一个清晨,江西永丰县林海山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红军孔宪权所在营地里,战士们正忙着清点武器弹药,整装待发。
今天这里将打响龙冈战役,胜负将直接影响红军的士气和后续战局。

“同志们,这场仗关系重大,务必打得漂亮!”
主帅的命令在山间回荡。
孔宪权握紧手中的子弹带,他知道自己肩负着断后大任,必须死守这座战略要地。
枪声大作,战火燃起的瞬间,敌军主力果然直扑而来。
“以弹还弹,立即开火!”
孔宪权带头冲上前,一颗颗子弹射进敌群。

乌泱泱的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有人应声倒地,有人跌落悬崖,场面惨不忍睹。
就在这时,孔宪权猛然发现,一个军衔最高的师长张辉瓒,正带着几名卫士在山崖另一侧狼狈退却。
“快追!”
孔宪权眼睛一亮,立即带人殿后死磕。
几番鏖战后,孔宪权亲手将师长擒获。
“干得好!”
上级将领忍不住夸赞。
“这个小伙子很有前途,一定要好好培养!”

从此,孔宪权在部队里渐渐崭露头角,前途不可限量。
激战黑神庙
1935年初春,贵州山间洋溢着绚丽的野花香气。
然而红军根本无心欣赏,因为他们正紧锣密鼓准备飞夺娄山关,出其不意反攻敌军。
“给我盯紧黑神庙,那是敌人的指挥所!”
时任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手按地图指点,他亲自带队深入敌后刺探虚实。
入夜后,孔宪权悄然来到娄山关。

月色朦胧中,黑神庙隐现眼前,敌哨兵踱步巡视。
孔宪权立即命令部队突进黑神庙。
“给我拼了!”他高喊一声,亲自带头冲锋陷阵。
枪声炮火中,敌我展开了惨烈肉搏。
一颗颗子弹呼啸着擦过他的耳畔,孔宪权一个滚翻进入路边的土坑,单膝支地瞄准,三发子弹精准击毙三名敌兵。
就在这时,一串枪声骤然响起,孔宪权只觉左腿剧痛无比,整个人重重栽倒在地。
“啊——”他痛苦地惨叫一声,冷汗瞬间浸透了全身。
左腿被击中了六弹,鲜血汩汩流淌。
剧烈的疼痛让孔宪权眼前一黑,命悬一线。

就在这时,更多的敌兵发现了他,拔刀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
孔宪权强忍着剧痛,拖着流血不止的残腿,死死滚进一旁的浑浊泥水坑里,顽强抵抗着。
“子弹还剩最后三发,必须死战到底!”
他双眼通红,把最后的三发子弹全数射向最靠近的三名敌兵。
危急时刻,二营营长邓克明的援军及时赶到支援。

这场惨烈的攻坚战终于结束,全部敌兵被歼灭。
邓克明将奄奄一息的孔宪权,救回了营地。
永远不能再上战场了
由于伤势过重,红军只能将孔宪权,安置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疗养。
一年多后,他的伤势终于痊愈,却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这一年的时间,孔宪权过得很不容易。
他一直卧床静养,宋家人细心照料,才保住了性命。
然而高温与潮湿的天气,使得他的创伤一直难以痊愈,夜里疼痛难忍时,他都会默默地流泪。

终于,他可以下地走动了。
然而左腿的创伤太严重,比右腿整整短了十多厘米,且留下了许多铁片与瘢痕。
“我这条腿......永远不能再上战场了......”
孔宪权双手捂脸痛哭,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仅是左腿,更是作为革命战士的尊严与骄傲。
儿时那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如今却成了一个伤残的军人。
他不禁背靠墙壁,泪水夺眶而出。
红军战友们,此时又在哪里呢?
他们还记得自己吗?
伤残退伍后,孔宪权为填饱肚子,成为了一名小商贩,背着担子艰难地沿街兜售各种杂物。
还学会了瓦匠手艺,开始给村里人盖房子。
轻烟从村头的小瓦房里悠悠升起,孔宪权正忙着为村里一户人家修补房顶。
他双手抓着瓦片和铁钉,熟练地将它们嵌入粗糙的木头框架里。

阳光下,他笨拙地爬上一个又一个房顶,将瓦片一片片打扎整齐。
每天奔波劳累,但收入微薄,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老友重聚,安排工作
时隔多年,杨勇收到孔宪权的来信,惊喜交加。
他们是老战友,从前并肩杀敌,关系十分密切。
但自从孔宪权在战场负重伤,杨勇就一直以为他已牺牲。
“老孔还活着!我必须马上告诉黄克诚!”收信后,杨勇激动得双手发抖。
一个月后,孔宪权来到了遵义,和杨勇相认的一刻,两人泪水盈眶拥抱在一起。
孔宪权被任命为副区长。
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建成,他又当上了馆长。
站在馆内,孔宪权凝视着熟悉的展览文物,那些日日夜夜并肩战斗的场景历历在目。
“我们的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会永远记得。”
他轻声自语道。
1988年11月7日,秋风寒冷,一位伟大的先辈,孔宪权。

在岁月的车轮下静静离世,享年78岁。
这一天,天空似乎也为之失色,阴云笼罩,落叶随风而舞,仿佛大地都在默哀这位为国为民付出一生的英雄。
回首孔宪权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饱受苦难,但他从未将自己沉溺于残疾的阴影中。
身残志不残,一心向党。
恢复党籍后担任遵义纪念馆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敬礼,革命先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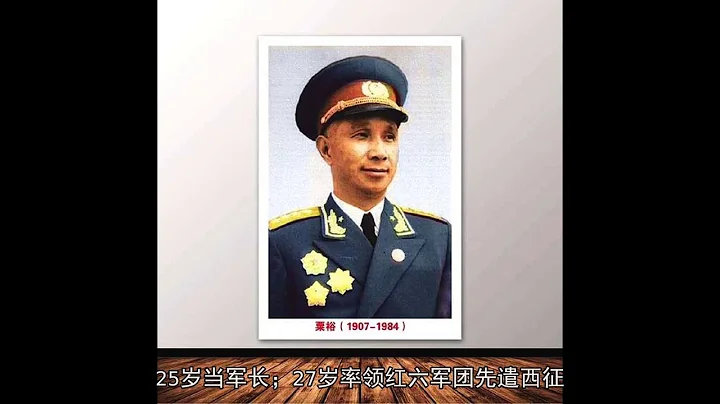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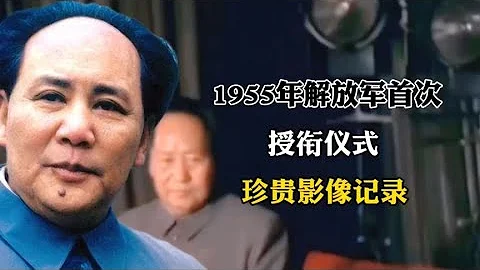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