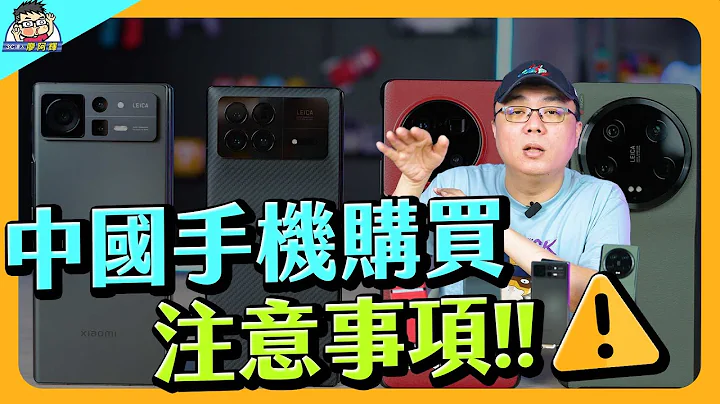购得飞利浦电子管CD机一台,寻寻觅觅很久,不能像丁元英那样玩硬件,只能用套机,挑来挑去,遇到了这台飞利浦。它本就是老牌音响,这台机器的前级用了捷克军工电子管,后级仍是数字功放,这样的组合真是很巧,有着1+1大于2的效果,于是果断入手。开机后,电子管预热10秒,看着那闪闪的红光,好怀旧的感觉。

手上有几套电子管录音的CD,喜欢那淳朴原始的音质,现在又有了胆机,就更配了。音质干净圆润,音量开大也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感觉,听FM时会变得很强大,低音炮的感觉来了,嗡嗡的。更喜欢CD播放的声音,温柔通透声声入耳,很舒服自在的感觉。终于有了能令自己满意的机器。

音乐发烧友中有很多玩硬件的,我不是发烧友,也玩不起硬件,有一个摄影已经够了,如果摄影和音响一起玩,家会被败光的。如今有了心爱的CD胆机,也收藏了几张有价值的黑胶,满足之余又想起一个听音乐的经历。
几年前春寒料峭之时,朋友带我去一个诗社听黑胶。诗社主编是一位老汉儿,自称农民,颜值大约是《白鹿原》里白嘉轩那样的农民。虽称不上儒雅,但也一定是个有趣味的人。他先是让我随意翻看架上的书籍,之后便带我进入他的听音室。

老汉也有自己的一间公司,把挣的钱投到了听黑胶上。他专门为自己安排了一间听音室,功放、音箱、大屏一应俱全且档位甚高,还有专门存放黑胶的房间。我想找一张莫扎特的21号钢琴协奏曲,欣赏一下他的组合音响,老汉儿说没有,只有《春江花夜月》这样的,还有昆曲。老汉儿说他是个“临川梦里度余生”的家伙,酷爱昆曲。他给我看诗社的刊物,里面还记载着他与我这位哥们儿一起打飞的去上海听昆曲的经历,以及他们沉浸在剧中如醉如痴的表情。
我喜欢青春版的《牡丹亭》,老汉儿则最喜欢单雯16岁时唱的“鼓舌如莺黄”的那版,认为深得昆曲的真谛。所以先听了单雯那版,之后又看了青春版的《惊梦》。我喜欢把不同版本的放在一起听,老汉儿拿来了两个版本的《春江花月夜》,听不同版本是很多音乐爱好者的一好,在这点上,我与老汉儿是共同的。我提到我一直没找到《淡水小镇》,老汉儿说“在这儿听吧。”他拿出了《淡水小镇》的黑胶,后来又拿出了鲍比达《关于爱情》的CD 和黑胶,鲍比达的钢琴回旋在幽暗的空间里,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黑胶细细的沙沙声是那么柔美,它仿佛是一种朦胧的空间,包裹着我们的灵魂。
离开听音室,我们一起去老汉儿熟悉的小馆子喝酒,他不仅挑出了自己珍存的佳酿,还把诗社的刊物也带上了。酒过三巡,老汉儿从刊中挑了他写的《鹧鸪声声》套曲让我念,看着这题目我心中一动,鹧鸪声可是有着明确的含义指向的,这声中含着些什么呢?
果然,念了几首我便指着一段词句对老汉说,“这里面有故事”。老汉儿微笑道:“都过去了。”我问:“能过去吗?”他说:“能过去”,并微笑着点头。真的过去了吗?那为什么还点名念这首词?我望着那张微醺的脸,忽然觉得人老了真好,有那么多积淀,有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多可以回首的往事。看着老汉儿脸上的微笑,那就是回首时的一种满足吧?

本来是来见识音响听黑胶的,没想到还听了鹧鸪声声。音乐总是能拓展人的思绪,令人的情感更细腻更饱满。老汉儿说他是“临川梦里度余生”,这不仅是对昆曲的喜爱,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似有似无又刻骨铭心的梦境与真实,让人如何忘得了?黑胶记录的那些“临川梦”,那细细的沙沙声,伴着那些在人心不古、物欲横流中仍坚守真淳情感的人们,在梦境与真实中不断出入,浅吟低唱,始终保有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余生该有多美。回想这段往事,觉得我的飞利浦真好,我的CD架,我的黑胶箱真好,它们带给我的不只是音乐,而是陪伴,是最好的陪伴,它们才是余生不离不弃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