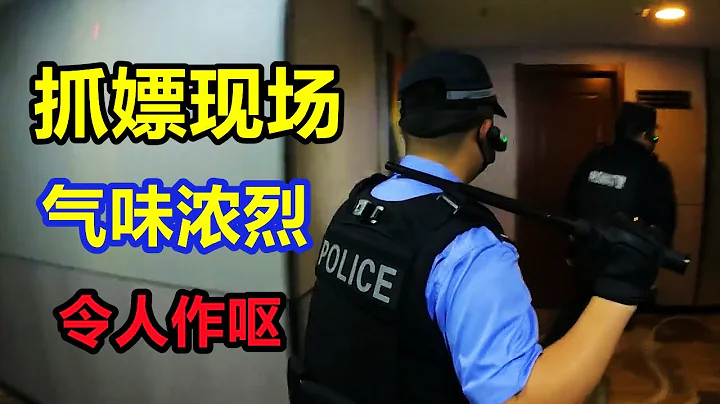加拿大作家梅维斯·迦兰。资料图
最近迷上加拿大作家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的作品。她曾在《纽约客》上发表116部短篇,数量比肩约翰·契弗和约翰·厄普代克。年青一代的杰出作家如裘帕·拉希莉、弗朗辛·普罗斯都为迦兰写过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但是我的沉迷更来自一种不安:
以迦兰最有名的作品之一the remission(《病缓》,暂译)为例,小说开场就点明了其浓厚的象征意味:“当阿莱克·韦伯终于清楚自己的病情远比别人告诉他的更严重时,他舍弃了自己在英国的生活,搬到里维埃拉等死。”但小说所指涉的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韦伯一家住在意大利古堡里,面对蔚蓝的海岸,韦伯夫人仍然请得起厨子和帮佣,虽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但她请了一位贵族后裔教孩子法语。表面上一切并不糟糕,韦伯不需要送医院,虽然他基本不再说话。过了一两年,韦伯夫人交上一位相好:一个经常在法国电影里出演英国人的当地人。韦伯没有抗议,或许也无力抗议,他被送到毗邻墓地的医院,韦伯夫人以及情夫悉心地照顾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那场姗姗来迟的葬礼:当地人早就习惯韦伯夫人和外遇一起,以为韦伯先生早就死亡,所以葬礼的邀请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葬礼上,韦伯夫人那位常年饰演英国人的情夫被误以为是真正的英国人,而韦伯家的两个孩子已经讲不好英语,也完全看不出是英国人了……
与其说小说的情节令我感到震撼,莫若说是迦兰的写法。小说是中篇的体量,按照时间线索进行,有些时候给人一种报流水账的沉闷感,所有戏剧化的事件(比如婚外情)都被漫不经心地带过,反而是更细小的情节(比如韦伯家的两位英国邻居)被更耐心地描绘。我看完的时候非常疑惑,甚至感到一个好故事被怠慢了!要是换作福克纳来写,时间很可能被压缩到韦伯死亡的前一天或者葬礼的当天,我们会得到每个人物更强烈的心理反应,或罪咎或为自己辩护,就连冷漠也会被这个特定的时空染出别样的色彩。我不懂为什么迦兰要用这种反戏剧化的方式来讲述。
倘若有些作品的生命随着阅读的完成而终结,另一些作品则在阅读终结的那刻才诞生。《病缓》属于后者,合上书本后的每一天,我都在遭受来自小说中人物的突然袭击:好好地走在路上,我会突然想起一位里维埃拉当地邻居说她此生还未走进过一栋英式房子;洗菜的时候,我会突然听见韦伯家的其中一位英国邻居自豪地说:“园艺永远不会有过时的一天”。我忽然悟出她们话里的深意,因为现实中的我正在遭遇我所在街区(乃至另一个帝国)的衰落。
简单说,三年前刚搬到这条街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寓楼门口“住”着一位天使般的流浪汉——大卫。每天早晨七点,大卫用房东给的备用钥匙打开停车场的铁栅栏,取走立在垃圾箱旁的扫帚和簸箕。他不仅清扫停车场,还会打扫公寓楼所在的整个街区,等一切完毕,他爬到垃圾箱顶端,把堆积如山的垃圾袋踩扁,而后把垃圾箱盖严实。
某种程度上,街区的衰败发生在他失踪之后——疫情的第二年,洛杉矶偷车贼猖獗一时,据说大卫是在半夜出面阻拦时遭遇了枪击,他没有生命危险,而是在送医治疗后被送到了庇护所,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完全相信这样的叙述,因为我们中再没有人见过大卫。
隔壁的仓房易手,新住户装了更严密的防盗系统,我常常听见警报被误触,反复念叨说严密监控正在进行中。沿街的帐篷像蘑菇一样滋长蔓延,我看到电线桩旁的地砖被撬开,一条条细长的电线跨过马路,通往不同的帐篷。再后来,不仅是人行道上堆满的垃圾不再得到清除,警用直升机的到访越来越频繁,公寓楼里也开始闻到大麻的味道以及狗的尿骚臭——楼里的住户换了一波……
我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缩减”(reduction),我略去了和衰败不符的因素,比如新仓房的生意很不错,又比如我认识了一位好心的流浪汉——乔伊。如果进一步强调戏剧张力,可以把时间进一步压缩,可考虑借鉴美国“黑色(noir)文学”的开山之作《邮差总按两遍铃》:命运之神好比邮差,会登门按铃,第一次你没有听见,第二次你就听见了。换句话说,你逃得了第一次,逃不了第二次。这里的“二”本身就是一种压缩,因为现实中命运之神通常没有这么雷厉风行。如果回到我的街区,故事可以缩减为两位流浪汉的失踪,第一次失踪或被认为是零星事件,第二次则有“寓言”意味。

电影《邮差总按两次铃》(1946)剧照。资料图
某种程度上,《邮差》对时间的重塑经由好莱坞黑色电影的扩大,如今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影视故事的标准样式——更宏大的社会图景被压缩成一个个戏剧单元,我们从突发事件进入,通往另一个突发事件。我一度很崇尚这种“高压锅”式的戏剧加工,未曾想到这种对时间的重塑彻底改变了我对现实的期待:或许和很多人一样,我变相地期待“抓马剧”。我期待衰亡以垮塌的形式全方位地发生,渴望在短时间内掌握群魔乱舞的全景,也期待我的紧张感会在垮塌发生后即刻释放。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戏剧加工反过来影响了现实:只有垮塌才能吸引眼球,但垮塌发生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了看戏的姿态;垮塌前的现实漫长,复杂,信号频布,但我们却对此失去了感知,因为这种时间感只让我们感到无聊,沉闷,并不激发紧张感。
是在这样的当代语境中,我感到了《病缓》的珍贵。迦兰不去夸大戏剧性事件,反而让读者感受现实中绵延无尽的时间感,训练读者对“衰亡”发出的每个细微信号的敏感度。不不,不是电影中常见的老房子出现裂缝或者虫害,这些太明显了,而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衰亡”,是需要读者去推敲潜台词的“衰亡”,好比那个为英国园艺感到骄傲的邻居(她还以为英帝国落幕之后,每家每户还都能像以前一样负担得起一座花园呢!)。
我当然知道在一切都在加速的社会里,阅读不以戏剧感取胜的作品是一种奢侈。我也知道在更多人阅读大部头作品的时代,世界或也一样纷乱。但在被国际新闻搅得心慌的当下,反而是迦兰或其他对社会变化娓娓道来的作品,给了我难得的平和。
钱佳楠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