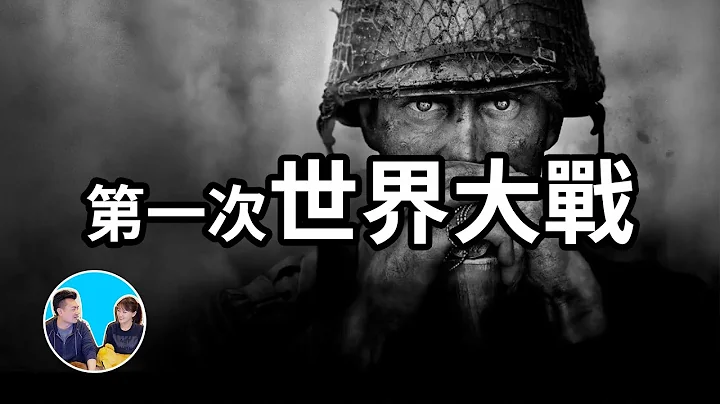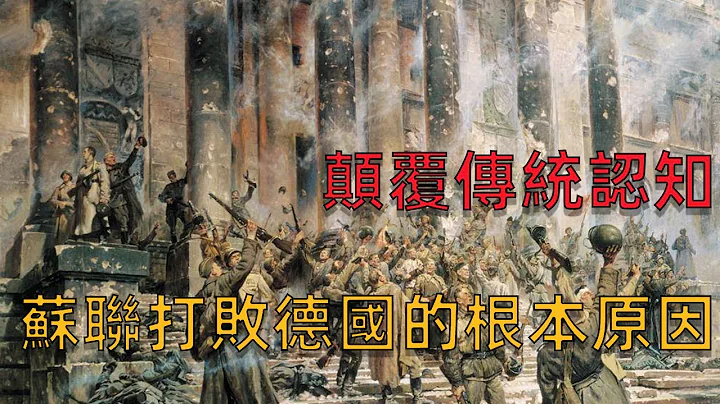閱讀此文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注」,方便您隨時查閱一系列優質文章,同時便於進行討論與分享,感謝您的支持~
戰爭結束後,德國當局放鬆了對修建永久性紀念遺址的限制。只要遵守當地規劃法的要求,就可以修建戰爭紀念碑。為了確保這些紀念遺址遵循了規劃章程以及有著符合規定的質量標準,大部分德國的州都成立了特殊的戰爭紀念部門,用來檢查所有的紀念活動規劃。

「為國犧牲」的說辭
德國猶太社區和基督教會一樣,深深捲入這場突如其來的紀念活動的風暴中。戰爭結束後,幾乎所有的德國猶太社區都在籌劃為前線戰死的成員舉行紀念活動,修建永久性的紀念物。許多德國猶太組織在紀念活動中繼續將其陣亡將士看作是為國犧牲的英雄。
1919年9月,當柏林的猶太改革社團在他們的猶太教會堂修建一塊紀念牌匾的時候,「為國犧牲」的說辭時刻被提及,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的演奏開啟了宗教儀式。

貝多芬的音樂在戰爭時期因為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廣受歡迎,因此貝多芬的音樂有助於營造儀式的愛國基調。之後的演講也採用了英雄主義的語調來強調士兵們為了祖國做出了愛國的犧牲。
社區的拉比公開宣布:「在精神上全體德國人和我們一起哀悼我們的逝者,同時通過這種引以為傲的懷念方式向他們的勇敢的死亡表達敬意。"

紀念物本身遵循著一樣的主題。青銅牌匾上簡單的題詞強調了死者是為國捐軀,而不是為了任何特別的猶太民族的理想:「來自我們的社團,(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國捐軀,1914-1919」。
在略顯不足的熱情洋溢的措辭中,柏林的主要猶太社區也強調陣亡軍人的英雄主義的犧牲。社區的第一個永久性的紀念物是一塊為了紀念在戰爭中被殺害的十六個猶太官員的紀念牌匾,它被掛在奧拉寧堡大街行政大樓上。

1922年12月,死者的親屬和社區的領導一起去見證利奧·拜克選取紀念遺址,他曾擔任軍隊的拉比。這塊牌願試圖去緩和那些通過強調個體身份的複雜性來公開贊項死者的情況。按照這種描述,士兵們不僅僅是作為德國人而戰死,更確切地說是作為德國猶太人而戰死。
石制紀念物的兩個角標有大衛之星,雖然在牌的頂部雕刻的是德國的熟語「光榮榜」。牌匾也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表達了死者無論是出於平民的成就還是軍人的成就都是光榮的。每一個名字的旁邊都列出了他們死亡的地點,以及在社區中的個人的職位。

傳統的社團也力圖確保為德國猶太士兵修建的戰爭紀念碑能夠符合猶太法的要求。曾經,哈雷的一個猶太社團計劃在猶太教會堂的藏經閣上安放紀念牌匾的時候,一些傳統的和較自由的拉比插手干預。
柏林的阿達斯猶太社團廢除了這一提議,因為完全不相稱。該組織聲稱:「這是最神聖的地方,只能用於上帝的榮譽……"它還補充道:「藏經閣不應該被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想法削弱。」

一位菜比錫城的拉比肯定這種觀點,他認為哈需社團的計劃儘管出於好意,但是這一做法嚴重地褻瀆神靈。"似乎這些批判阻礙了哈雷社團的計劃,因為直到1934年,一個戰爭紀念物才在城市的主要猶太教會堂修建。
德國猶太人的紀念活動沒有固定的模式,反而是眾多的相互關聯的活動。在每一個德口城鎮,都市或者地區,總是有不止一個猶太社團包含在紀念活動的過程中。

所有的組織常常在競爭修建戰爭紀念物。他們大多數是由戰爭時期的哀悼社團發展而來,仍然採用「為國犧牲」的說辭。當戰爭結束時政府放鬆限制的時候,這些小的社團大都為他們在戰爭中被殺害的成員修建永久性的紀念物。
儘管一些比較傳統的社團為猶太人的紀念活動制訂了規則,但是沒一個組織在這一過程中都積極地採取不同的方式來紀念戰爭死者。猶太紀念物的最終修建反映出每一個個體組織對於戰爭的解釋,而不是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包羅萬象的猶太人的記憶。
戰時軍事墓園的修建
事實上,1914-1918戰爭年間很少為犧牲的士兵修建紀念碑。一方面是因為在戰爭期間政府極力阻撓修建永久性的紀念遺址,政府害怕德國如此巨大的損失以如此明顯的方式被提醒,造成社會的動蕩。
這種畏懼使得政府將許多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勞動力轉移到更需要的地方。為了這個目的,1916年國內政府發布命令要求全部終止正在進行的紀念活動。在戰爭期間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同樣一切可用的資源都應用於現今最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因為隨著戰爭的持續以及傷亡人數的不斷增長,想要推進永久性紀念遺址的修建工作是不切實際的。
由於在戰爭期間修建紀念物比較困難,所以,關於公墓的選址及外觀設計的爭論成為公眾最關心的事情。大部分設計專家都認為無論是國內的公墓還是前線的公墓,都必須表現出英勇和高貴的價值,士兵顯然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德國猶太人傾向於要求以同樣的標準原則來規劃他們自己的公墓,他們普遍接受了為國犧牲的說辭。因此,猶太人和其他德國人在初期懷著同樣的紀念價值選擇他們自己的公墓遺址。
德國每個州都設立了關於戰士榮譽的國家諮詢中心,他們通過了在德國修建軍事墓地的最新建議。在建造戰爭墓園的過程中,德國猶太社區遵循著諮詢中心以及關於戰爭墓地設計設立的各種委員會的指導方針。儘管猶太社區對於陣亡猶太士兵的埋葬有著事實上的自主權。

在戰爭開始之初,德國聯邦猶太社區給一些小的社區提供了支持和指導,他們從戰時部門獲得了許可,可以在德國為戰爭中犧牲的猶太士兵修建猶太墓園。
儘管在漢堡和柏林的猶太軍事墓園堅持遵循地區諮詢中心制訂的設計準則,但是他們仍然確保他們符合猶太法律的要求。在漢堡和柏林的社區認同軍國主義的題詞以及標誌是不適合猶太軍人墓地的。

1915年遵循來自柏林的建議,漢堡的猶太社區認為猶太墓碑上的鐵十字架象徵是不合法的,但是被斷定為「鐵十字架勳章持有人」的題詞是可以被接受的。
猶太社區可能想要在他們的墓園禁止建造軍國主義的建築,但是他們不得不滿足許多親屬想要他們的愛人英雄主義的業績被永久性地刻在石頭裡的願望。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儘管猶太戰死士兵被安葬在單獨的墓園裡,但是德國一戰猶太士兵仍然是戰爭紀念遺址的主要部分。猶太新聞報道證明在德國社會猶太士兵的葬禮廣泛存在。
1918年5月,科隆盟軍的空襲造成了三十五人死亡。在科隆的南部墓地,為紀念那些犧牲的人市政當局舉行紀念活動。因為在空襲中受難的猶太人是有限的,社區的拉比路德維格·羅森塔爾也被邀請參加儀式。

羅森塔爾指出,超越先宗教界限的德國紀念文化的存在範圍不斷擴大。遍及整個戰爭,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出席無論哪種信仰的軍事墓地葬禮都很普遍。他們聚集在一起更多的不是在分享宗教象徵,而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象徵。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