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孫權攻合肥事件最早見於《三國志·魏書·溫恢傳》,按史料所言,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曾經有過一次進攻合肥的軍事行動。
但可能由於規模較小,這次軍事行動卻沒有被當時的揚州刺史溫恢和兗州刺史裴潛所重視。
溫恢還預料到征南將軍曹仁有可能被關羽的水攻打敗,所以提醒裴潛早作支援曹仁的準備。

孫權在位期間,為了獲得北上的通道,於建安二十四年之前和之後都多次攻打過合肥,原不足為奇。
但按以往學者所言,曹孫已於建安二十二年秘密聯合,雙方聯合的最大成果,就是於建安二十四年擊敗了荊州關羽。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孫權攻打曹操屬地的事件,似乎又昭示著曹孫在建安二十四年荊州之爭之前並未聯合,這就對以往學者的說法提出了挑戰。

以往學者在研究三國史時,對於建安二十四年過多地關注於上半年劉備取漢中和下半年的關羽攻樊城以及失荊州等重大事件,對於這年的孫權攻合肥事件沒有應有的重視。
不少學者對於建安二十四年下半年的認識往往以荊州之爭為主線,進而靜態地以為這年的曹孫關係是早已暗自聯合。
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會改變我們以往對於建安二十四年曹孫劉三方關係的認識。

孫權攻合肥的具體時間
根據對史料的研究,可知孫權攻合肥的具體時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
根據溫恢所言「今水生而子孝縣軍」,可知孫權攻合肥之事發生在漢水大溢之前,而根據《後漢書》記載,「(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我們可以確定孫權攻合肥發生在八月甚至之前。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將此年孫權攻合肥一事寫到七月,並置於關羽攻荊州事件之前。

按司馬光的看法,從時間上來說,先有孫權攻合肥,其次才有關羽攻樊城之事。
而《三國志·魏書·溫恢傳》中的內容應當以「於是有樊城之事」為斷,前面的孫權攻合肥事件以及溫恢、裴潛的談話發生在七月,「樊城之事」發生在八月,後來的「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以及溫恢、裴潛的再次對話發生在十月。
後來發生的呂蒙受命攻荊州之事發生在閏十月。
在關羽未動兵之時,即有孫權攻合肥之事,可見若要確定此次軍事行動的性質,需要明晰建安二十四年七月之前的孫、曹、劉三方關係,而不可被關羽攻樊城之後的孫曹結盟關係所迷惑。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孫權與曹劉的關係
認為曹孫早已聯合的學者,其根據的史料無非是《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的一條記載:「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張作耀先生就由此認為曹孫聯盟在建安二十二年已經建立,「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戰略又一大變,他把劉備作為主要敵人」,「一個以孫權『請降』為前提的各自為用的臨時同盟,戲劇性地形成了」。

何茲全先生也持有與張作耀先生類似的看法,認為「這時,孫權已為與曹操休戰轉而向關羽進攻打下埋伏,只等機會了」,但這樣的觀點或許是已知歷史結果後的判斷。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次孫權請降是有特定背景的,其原因就是孫權防禦曹操進攻的失敗。
面對曹操的進攻,孫權防禦失敗,然而在三月曹操即回師。
觀「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中的「春」字,就已經說明孫權的請降發生在這一年的一、二、三月之中,根據上下文,具體的請降時間當為孫權敗退之後及曹操回師之前,很明顯孫權請降促成了曹操的回軍。
這種情況下的請降乃一時權宜之計,怎能認為是曹孫已提前兩年就開啟了合作關係的標誌呢?

至於「誓重結婚」等,不過是外交辭令,根本不能說明曹孫已經有了實質性的盟約和親善的關係。
況且曹操撤軍之時依然留下了夏侯惇、曹仁和張遼的軍隊屯守居巢前線,比起之前張遼獨鎮合肥,對於孫權的軍事防備反而加強。
而根據史料記載,也可以推斷出,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孫權尚未稱藩於曹操,雙方依然敵對。
孫權開始與曹操聯合的時間,是在此年十月,「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

這說明孫權向曹操正式表明稱臣是在十月,此前未有曹孫表明聯合意向的記載。
而且,當關羽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其鋒時,司馬懿和蔣濟都進行了勸阻。
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
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他們二人在勸諫中評價孫劉關係時用的是「外親內疏」,可見在其他見識較低的魏臣甚至曹操眼中,孫劉同盟關係可以用「親」來形容。
二人對於孫權會不會出兵也依據的是「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這種推斷性論證,而沒透露任何孫權已經摒棄和劉備的同盟或者孫權已暗自結盟曹操的信息,甚至還準備付出一定的代價(給封號和承認領地)來促使孫權出兵,這些可以反證孫權在那時還沒與曹操聯合。
更明顯的證據則是司馬懿勸阻曹操遷都的理由是「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淮水流域為曹操阻擋孫權進攻的前線,沔水(漢水上游)流域為曹操阻擋漢中王劉備進攻的前線,如此類比,更揭示了孫權對曹操而言依然是敵人。

而到了十月孫權稱藩之後,曹操立刻把合肥地區的駐軍派往荊州救援。
從《三國志·魏書·溫恢傳》的描述中可以發現,十月曹操「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的這次軍事調動也包括了布置在居巢的張遼軍隊,而且合肥地區的二十六軍都督夏侯惇也被調動了過來。
可以說,合肥附近的駐軍幾乎傾巢而出救援襄樊了。

如果此前曹孫已經聯合,那麼何必要等到關羽已經圍樊城和滅于禁七軍近兩個月後,才開始派遣合肥的軍隊救援呢?可見,孫權的暗地示好,承諾襲取關羽後方,等於撤除了合肥的戰略威脅,才是曹操可以派合肥軍隊馳援的原因。
因此,在孫權攻合肥的七月以及之前,曹孫之間還是互相敵對防備的關係。
孫劉之間雖然在建安二十年發生了爭三郡事件,但是在聽聞曹操將攻漢中時,劉備已經進行了妥協,以湘水為界讓出三郡,雙方的矛盾暫時化解,呂蒙固然曾獻計攻關羽,可孫權並未計劃何時行動,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可見雙方的關係在表面上還是親善的。

後來關羽攻樊城時,即使之前索婚不成,孫權還曾通書試圖派兵相助。
當然,裴松之引用《典略》時也對此史料表示懷疑,下文即說「臣松之以為,荊、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
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
但無論如何,這些都說明,在關羽攻樊城之前,孫劉聯盟依然在維持,甚至孫權還在一直做著維繫同盟關係的努力。

孫權攻合肥與呂蒙襲荊州沒有聯繫
孫權在主力西征之前,為了迷惑魏蜀兩家,遮掩自己的真實意圖,曾派遣一支部隊北越巢湖去佯攻合肥。
曹魏方面,儘管接到孫權的降書,但考慮到兵不厭詐,有可能是敵人的詭計,為了防止受到孫權的欺騙,仍派遣了鄰近諸州的援軍前往合肥助守。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方最大的軍事事件就是呂蒙襲荊州,懷疑兩次事件有關聯也很合理,但這兩件事並沒有關係。
呂蒙屯軍地點在陸口,合肥方向在其東北,荊州方向在其西。
孫權當時居於建業,既然攻合肥的軍隊是孫權所派出的,那對於關羽來說,呂蒙依然按兵不動,自然不可能放鬆戒備。

從《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可以看出,關羽即使出兵樊城後,依然在荊州布置了相當的防守兵力,導致呂蒙無法制定有效的襲荊州計劃,直到呂蒙稱病、陸遜代任以及陸遜致書關羽等一系列事件後,關羽才放鬆了防守,又將一部分荊州守軍調到樊城前線。
孫權攻合肥並沒有起到迷惑關羽的效果,從結果上來看,關羽的削弱防守和孫權攻合肥事件沒有聯繫,因此筆者認為,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事件是一次有獨立目的的軍事行動,與後來的呂蒙襲荊州並無關聯。

孫權攻合肥有可能是一次小規模掠奪
由於此次事件只存在於《三國志·魏書·溫恢傳》中,從魏書和吳書其他內容中都沒有提到,我們無法知道有吳國哪位將領參與了這次行動,可能吳國在這次進攻中沒有大規模的人員調動。
進而可以推斷,孫吳雖然趁曹魏受挫之時想趁火打劫,但當然也不願損失兵力讓蜀漢漁利,這次進攻也不會是以攻城略地為目的,那麼,就極有可能是一次人口、財物、糧食的掠奪。

大概在西晉成書的《廣志》記載了很多當時南方地區的風土物產,現已散佚,但在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還保留了其部分內容。
西晉之時距三國之時不遠,可以類比得出結論,在長江流域種植的水稻的品種中很多會在七月收穫。
既然孫權攻合肥恰好發生在秋收之時,那麼這次行動目的是掠奪的可能性就極大。
在戰爭時代,兩國交界處出現掠奪人口的事情並不少見。
而趁對方秋收之時奪糧之事也發生過。

在進攻方無法快速奪得敵方屬地時,通過掠奪其戰略資源達到削弱敵方的目的,並且補充自身實力,是一種常見且有效的戰術。
在面對老對手孫權的進攻時,揚州刺史溫恢卻仍然能輕描淡寫地說出「此間雖有賊,不足憂」這句話,也已經暗示了孫權的這次進攻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威脅性,即,孫權的這次進攻雖然會造成損失,卻無傷大局。
所以,筆者推斷,孫權攻合肥是一次掠奪行動,其目的可能是掠奪魏軍在合肥附近屯種的稻糧以及掠奪一部分人口。

結語
孫權在建安二十四年之前曾兩次進攻合肥,分別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二十年。
建安十三年時: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建安二十年時: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即使以軍事角度講,如果關羽能和曹操的軍隊對峙於荊州,彼此消耗,是孫權最期望的局面,便不會有助曹操攻擊關羽的行動。

雖然最後的結果是關羽勝於禁和呂蒙襲荊州,但如果反過來是關羽慘敗,孫權也必然不會坐視曹操的勢力侵入荊南。
因此,將建安二十二年孫權的「請降」和二十四年呂蒙襲荊州聯繫到一起,認為曹孫早已密謀共同行動,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
而在這種背景下,孫權攻合肥的行動既不同於前兩次攻合肥那樣具有強烈的佔領目的,也與之後的曹孫結盟以及呂蒙襲荊州等事無關。
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的軍事行動應當具有兩個性質,表面上可能是一次小規模的掠奪行動,但深層次的性質卻是一種隔岸觀火心理下的向蜀漢表態合作攻曹的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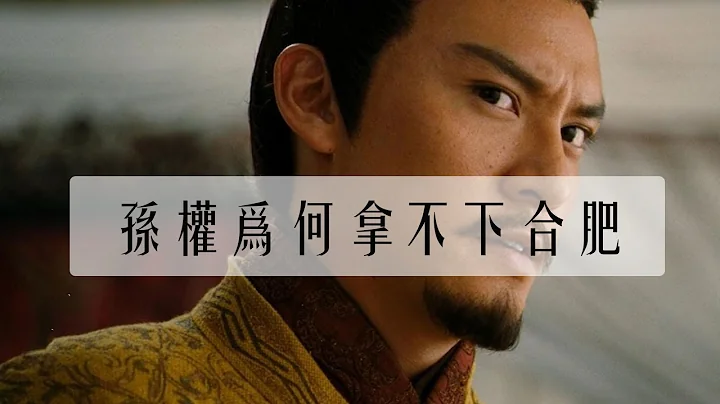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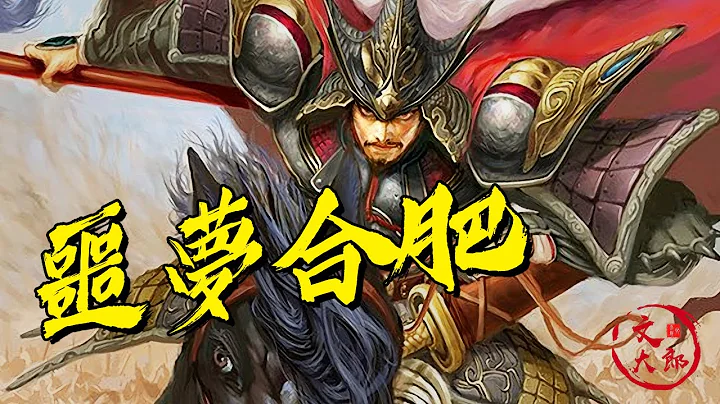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