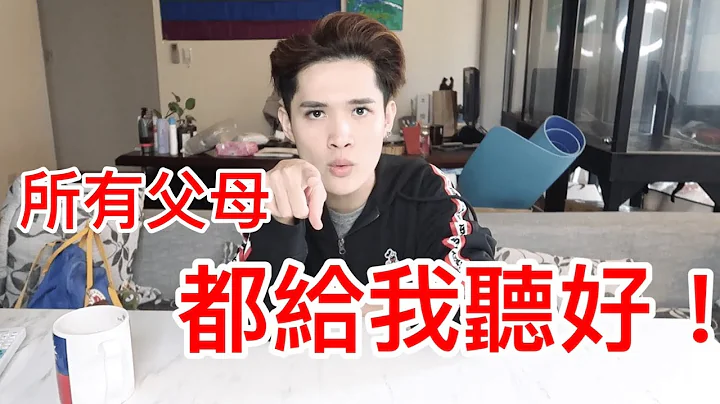近日,在兒科門診區,不時可見小孩邊輸液邊寫作業的「場面」,甚至有網友曬出醫院開闢的「兒童輸液學習區」。

圖片來源:大眾日報
對此,有媒體評論:「保護孩子們在生病時歇一歇、難過時哭一會、什麼都不做發發獃的權利,是和考大學、卷前途一樣重要的事情。」
一時間,「學生邊輸液邊做題」這一事件延伸出了很多熱議話題,其中就包括「學生權利」。
在生病時可以適度「躺平」,是學生的權利。包括之前的課間十分鐘自由、而不是被迫到廁所進行休息、社交等,都是學生的權利。

圖片來源:大眾日報
而實際上,早有老師們嘗試了這樣一堂課:引導學生關注兩個詞——「權利」與「規則」。
這些不同尋常的課,填補了傳統教育體系中的空白,教會學生意識到哪些事情其實是非正常的,以及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
1
「現在我們開始舉報",
舉報加分制下,同學們互相揭發
班長登上講台,攤開一個本子說:「可以開始登記了。」
這時,幾乎全班同學都「蹭」地舉起了手——
「我舉報xx在食堂蹺二郎腿。」
「我建議xx不要把手放在褲子里,還要聞一下,好噁心。」
「我舉報xx在宿舍里裸奔」
「舉報加分制」是由漠寒所在班級的班主任,在學校「操行分制度」的基礎上推出的。
具體的做法是,每天有一名值日生負責記錄同學們舉報的違規行為,晚上其他同學可以補充舉報或者申辯。被舉報的同學會被扣分,而舉報的同學會得分。
一周結束後,班主任會給得分是正數的同學拍一張合照,發到家長群里,作為對他們的表揚。
漠寒覺得這個制度非常不合理,於是用了三節課的時間,向全班講述了舉報制度的危害。
她告訴同學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權,可以拒絕參與舉報,而且在她的課堂上也禁止舉報行為。

但她發現,在老師、家長和同伴的多重壓力下,同學們還是難以擺脫互相揭發的惡性循環。
漠寒收到了很多同學寫給她的小紙條,向她傾訴他們在這個「監獄」里的無奈和痛苦。
而真正讓她下定決心開展權利課的,則是自己的一次「犯錯」。
在一次發現很多同學沒有完成作業,一時沒控制住,漠寒竟然撕掉了學生的作業本。
那天回家的路上,愧疚、不安的情緒瞬間向她襲來,她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的老師?感覺自己好可怕,完全是在以一種羞辱的方式去對待我的同學。」
在撕了作業本的第二天,漠寒在課堂上向同學們公開道歉。學生們卻安慰她說,其他老師都是這麼做的,這是為了他們好。
而孩子們的反應更讓漠寒覺得心痛——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教育方式,並沒有覺得這個行為是不正常的。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這個年輕的女老師漸漸意識到:想要改變這種不正常的教育方式,一開始就要讓學生們明白自己有哪些權利,然後如何捍衛。

於是,她嘗試了一種新的教學方法——開設「權利課」,帶領學生們一起討論師生權利、制定課堂規則,並對教師「霸凌」的情境進行模擬。
在權利課上,漠寒會拋出很多具體的場景來討論,例如:
「老師是否可以體罰學生」、「是否可以言語侮辱學生」、「是否可以沒收學生的物品」、「是否可以佔用下課時間」?
她引導學生在國內法律條文、國外公立學校入學規則和聯合國兒童公約中,找到與師生權利相關的內容,讓他們直觀地了解自己的權利,如人身權、身心健康權、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受教育權等等,破除教師權威的神話。
除此之外,漠寒還設計了一套教案,題目叫「師生共建規則」,用於明確自己班級中「學生和老師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徐莉莉是漠寒的學生之一,「上廁所自由」,是她想到的第一條規則。她說,在學校里,每次課間休息都很短,而且老師還經常拖堂,她想去廁所都不敢舉手說。
在這堂課中,她終於有機會和老師一起制定規則,比如說:可以在得到允許後吃東西;可以提前預定上課時間;如果對教學方式不滿意,可以隨時提出調整。

曾被視為「問題少年」的李濤,在第一次上「權利課」感到非常不適應:「感覺很奇怪,在學校里都是被規定的,第一次讓我自己說。」
但在那節課上某個日子,他心中原本模糊的原則突然有了明晰的答案——師生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相互尊重的。
而為了讓低年級學生更直觀、更具體地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漠寒老師還想出了一個方法——「情境模擬」。
她會在課堂上突然扮演一個惡劣的老師,對某個學生進行「辱罵」:「你怎麼這麼笨,什麼都學不會,你是不是有病。」
面對「侮辱」,學生們學會了勇敢反擊。周圍其他同學也不會袖手旁觀,有人會站起來,指出老師的行為違反了教師規範,有人會走過去,安慰受到傷害的同學。
他們變得自信勇敢、不再害怕權威,而且知道了該如何用合理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2
和小學生們大聲談論女性權利
教給孩子們權利意識的老師,還有北京00後女孩毛毛。
她到河南鄉下支教,在這裡,她所教授的課程名稱是「心理課」,上課內容包括衛生巾的使用、彩禮和第二性等女性權利相關的內容。
之前學校有一個老師在初中班上課,講到青春期,如何使用衛生巾,男生全都在那邊笑;
而她的方法則是讓每一個男生,都上台操作一遍衛生巾的使用。
在她看來,孩子們那種笑和不好意思來自於不了解。而當開誠布公把它談了,把它講出來,孩子們逐漸意識到這和吃飯睡覺一樣,是很平常的事情。
令她驚喜的是孩子們面對性別話題的開放和坦誠,五六年級的同學們,針對課堂上播放的《我是劉小樣》:
以課堂展示的形式發表觀後感,主題圍繞著「婚姻是不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農村女孩被期待成為什麼樣的人」展開。
一個女孩在課堂中就產生了如下思考,「農村女孩被期待成為什麼樣的人」,雖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已經能感受到並表達:好像大家可能被期待著成為賢妻良母。

她還給學生們講生育權,講中國婦女地位變遷史,當然內容和講課方式會根據學生的年級做適當調整:
比如給中高年級準備的課程就是通史,按歷史時間軸的每一個朝代來講述;而給低年級準備這節課的時候,準備的就是人物故事,故事性更強一點。
學生們的女性權利意識開始覺醒,有位家長感嘆道,「我們小時候就沒有這樣的課,這些老師可以站在這裡給你們大大方方談論這些知識,媽媽覺得你應該好好學習」。
而且毛毛老師發現,在討論很多問題的時候,其實不用單獨問男孩子。
可能成年人的社會是有性別劃分的,但是在小孩子們眼裡沒有什麼。作為一張白紙而言,他們很多看法其實反而是不帶有色眼鏡的。
3
「權利意識」的種子
為何需要從小種下?
正如俄國文學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所說的:「你宣布絕對的服從,那你正是消滅了兒童們合理、正確而自由的發展。」
對於教師來說,最應該做的是走進學生的內心,激發孩子權利意識的覺醒,而不是扮演教室里的絕對權威。
而於學生而言,雖然很多重要的感悟,總是比相應的成長階段遲些到來。但完成教育的閉環,更需要從小埋下的「種子」。
回顧自己的童年,有網友分享說:
「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權威的建構是從小時候的教育就開始的,它又以各種形式根植於社會的各個方面。
一旦這種這種對於權威的恐懼在小時候紮根在了心裡,長大後,會需要更多的力氣去面對它。」

漠寒老師在學生心中播下的關於「權利意識」的種子,並沒有隨著課堂的結束而消失。相反,它們不經意間,在別處發芽了。
「面對權利被侵害,個體是有選擇的。」這是陳漠寒常常告訴學生的一句話。
她離開私立學校後的第二年,有一個同學因早自習站著念書的姿勢不太標準,被班主任罵了一頓,說他『不是個東西』。該同學立馬反駁說,「人人都是平等的,你沒有權利罵我」。
無獨有偶,毛毛老師也提到,其實自己不期待於孩子們當下就一定理解到什麼,或者說 get 到什麼很有用的點;
而是希望課堂或許可以成為她們心裡的一顆種子,她們未來可以突然想到,誒,女孩也應該是有思想的。
而種下的種子在當時或此後,真的發芽了。

毛毛髮現自己在講出那些「女性被忽視」的點之後,學生們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甚至自己提出發現的細節;
在課下也用課堂上學到的概念和知識交流,比如一位女孩決定把名字從「迎弟」改成了「迎自」,迎接自己的自。
教育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而持久的,而非短暫的、局限於當下。
如果學生在未來遇到某種情況,會發現:原來底氣早就在內心深處悄悄具備;
而這,大概是這些權利課堂最大的意義。
參考資料:
[1]澎湃深度訓練營-離開體制學校後,我成為了一名獨立教師丨對話另一種生活
[2]搜狐-沒有「上廁所自由」,學生之間互相舉報:一位女教師試圖打破這些不正常
[3]極晝工作室-班主任讓初中生互相舉報扣分 年輕女老師教學生反抗失敗離職
[4]她刊-當一位女老師教學生反抗權威
[5]中青評論-老師該不該是教室里的絕對權威
[6]在河南農村,和小學生們大聲談論彩禮、月經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