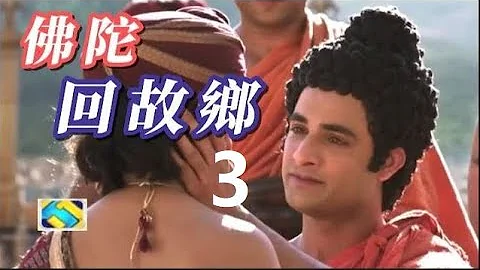閑話少敘,就說說我在實踐的不同階段對「忍辱」的理解吧。
起初,我是強迫自己認同「忍辱」的,必定吃虧是福,忍辱的過程就是消業的過程,忍辱也是一種慈悲;這些句子成了我的座右銘。
遇到別人的苛責和冒犯時要盡量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那段時期的我,為了修好「忍辱」,總是自己給自己挑錯,有時雖然心裡並不認同自己有錯,那也要強行找出錯誤扣在自己頭上,否則無法安慰自己那顆受傷的心。

很多時候心裡是憋屈和壓抑的,不明白如果錯不在我,我為什麼要原諒對方?忍讓對方?這樣長此以往,對方真的會認識到他的錯誤還是會覺得我軟弱無能呢?如果他覺得我很懦弱而愈發得寸進尺,那麼我的忍讓不就是一種縱容和罪過嗎?
按照佛教的因果觀(當然,因果觀並非如我舉例這般簡單直接,它是錯綜複雜的,也非我能解釋的)他欺負我是因為我前世曾經欺負過他,那如果這個人今生是個混賬,他囂張跋扈、經常性地欺辱他人,那麼所有被他欺負的人都是欠他的嗎?因此才要忍讓的嗎?
他前世既然是一個被眾人欺負的人,今生成為一個混蛋就是必然性,只是為了要報仇?如果這樣,他的業障也夠深重的啊,也是不能被大眾所接受的觀點。那麼來世的我也會如今世的他一樣?每每想到這些問題,我就不寒而慄,也無法照此再推下去了。

如果我走在街上遇到一個流氓欺負我,我是應該忍辱呢還是應該還擊呢?如果路見不平時我是該一聲怒吼呢還是袖手旁觀呢……?這些問題困擾著我,攪得我心煩意亂,我懶得往深處去想,因為我知道以我的頭腦是想不出答案的,它最終還是無解。
那為什麼佛教還要倡導人們修忍辱呢?佛菩薩可以包容萬事萬物,是因為它們沒有分別心,沒有分別心就沒有好壞善惡。但我們凡夫則不然,我們生活在這世上,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有標準的,好和壞是有界定的,如果我們見惡行不聞不問,就成為一個沒有良知的人了。

到了第二個階段,我覺得一味的忍讓不是辦法,錯不在我時我何苦讓自己憋屈,見到惡行時我不能視而不見、置之不理,如果長此以往,我沒修好忍辱,反倒會給自己憋出毛病,甚至喪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
更何況佛教當中有句話說得好: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慈悲和怒目是交替使用的,見善行自然歡喜,見惡行心生嗔恨,我不是神仙,我是凡人,那我就按凡人的標準要求自己吧,做個好人,但是要善惡分明。

就這樣我又恢復到從前,沒有修忍辱之前的狀態,一個個性分明的普通人,喜怒哀樂隨性流露,不同的是我心裡有個「修」的概念,我覺得我當前就如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三重境界之中的第二重境界。
在這第二層狀態中,我很自在也很舒服,因為我不用委屈自己了,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善惡來主觀的評斷我認為的是非曲直,並且還有佛教的理論做為支撐。

突然某一天晚上我又開始思索這個令我理不清的問題,我想我已經到了第二個階段,離第三個階段就不會太遠了。
而能夠到達第三個階段,需要我沒有分別心,沒有是非善惡,我能夠欣然地接受所有的榮辱而不為所動,接受忍辱是因為我沒有了惡的概念,我也就沒有了忍的覺知,我清醒的知道一切都是在因果中打轉。

想啊想啊,我突然有些明白了,當我覺得我明白後,我失望了,因為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
歸根結底我就是一個凡夫,今生是,若有來世我還是凡夫,我做不到包容萬事萬物,就像我們能接受鮮花,但是無法容忍垃圾;我們喜歡得到,而無法接受失去。
想到此處,雖失望,但也有些釋然了,那就是我沒有那麼大的心理負擔了,先腳踏實地地做個好人吧,所做一切憑良心、憑良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