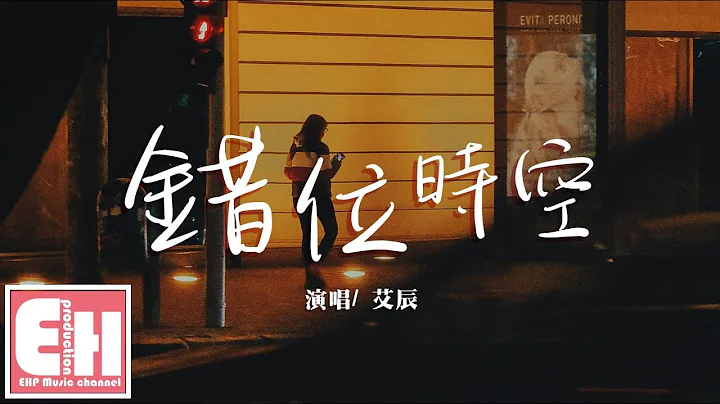《微影海上》新書分享會現場
手機可以拍出好作品嗎?
中秋假日期間,徐明松《微影海上》新書分享暨雅集在大滬聯合藝術空間舉辦。作為國內手機微攝影探索者、人與環境攝影大賽多年評委、滬上知名藝術評論家,徐明松將對於文學、繪畫、哲學、建築等的思考融合在作品裡,不斷打破、重構,在瑣碎的日常、破碎的風景里撿拾著詩喃般散落的情緒,呈現出手機微攝影之美。
藉此新書發表之際,我們跟他聊了聊他與手機微攝影。
- 徐明松 -

1963 年生於上海。
現居上海,滬上知名藝術評論家。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 上海藝術攝影協會副會長,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兼職教授,上海海事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兼職教授, 上海創意設計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上海美術家協會理論與策展藝委會委員,《藝術管理》雜誌執行主編、《藝術當代》《創意設計源》《公共藝術》雜誌編委。已出版《紙上風景》《建築烏托 邦:明天我們住在哪裡》(合著) 等圖書多部,業餘兼事公共藝術理論與實踐。

徐明松2622
Q:上個月《微影海上》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可否介紹下這本書?
A:這本書是我在疫情期間完成的,雖然做了一輩子編輯,但是從海量圖片中遴選作品還是存在困難,不過疫情也給了我沉澱、反思的機會,所以完成的時間不算很長。
它緣起於我在八年前的展覽,叫「三言兩拍」,有記者查證說這是國內第一個手機攝影個展。除了展覽里的作品,書里也包含我的其它手機微攝影作品,內容分為「時間的記憶」、「看不見的城市」、「靜觀萬物」、「生活的漫歌」、「畫里畫外」五部分。

《生活的漫歌之似索題詩句》徐明松

《金秋》徐明松
Q:您曾經提出了微攝影的概念,可否詳述。
A:手機的便捷性和攝影的功能讓我們觀察事物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我把它稱為後攝影時代新的美術現象或者攝影文化現象。
《手機微攝影,一種洞察的藝術態度》一文闡明了我對微攝影的觀念和理解:「『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句博伊斯的名言在當下成為了現實。尤其是當數碼手機旋風式地佔據市場進而佔據人們的心靈之際,這種手機照相直抵人心的魔力,相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攝影生態的改變而呈現得更為廣泛和深刻。因為,如果說照相機只是人們觀察與表現事物的工具和視覺延伸;而手機攝影則堪可看作身體機能(與身體關係最為緊密)的延伸和視知覺智能的延伸。它也從此成為微生活圈的構成部分,諸如通過微信和微博的自媒體發布與分享手機攝影的個人作品,故名之為微攝影。」

《殘忍的四月》徐明松

《都市裡的村莊》徐明松
Q:對您來說,開始手機微攝影也是偶然的過程。
A:是的,我在書里的後記里有寫,大概十年前,我的朋友,《南方周末》的記者、詩人王寅,把在世界各地遊歷的採訪和攝影作品集合出了本書,叫《攝手記》,由北三聯出版,他的文字和影像給我了手機微攝影的初印象,也是誘發我創作的衝動。之後我一發不可收拾,在手機微攝影的領域裡探索到今天。
Q:您的手機微攝影和傳統攝影的區隔是什麼?
A:其實,我也用單反拍過旅行照,不過由於物理負擔和技術要求,並沒有引發我對攝影的熱情。傳統的單反相機常用廣角表達大場面,空間感更強烈。手機微攝影因為畫質的限制,更關注局部、細節,當然隨著科技發展,這可能會得到解決。其實問題的本質不是技術,不管是手機微攝影還是傳統攝影都反映出我的美術攝影理想。它不僅僅是記錄工具,我更在意它的表現力與豐富性,我覺得這種豐富性在手機微攝影時代體現得更徹底。


《看不見的城市之關於海上的N個夢憶》徐明松
Q:您的手機微攝影很多是拍城市,城市中大多數人是奔波的,您的攝影卻有著淡淡的詩意之美,您眼中城市的魅力是什麼?
A:這個世界上有超過5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書里我引用了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作為第二部分的名字,我很喜歡建築,如果用傳統攝影表達感受,可能會出現很多人熟悉的場景表達,但我覺得如果城市像一片森林,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片片樹葉,這些斷掉的細部、稍縱即逝的碎片,恰恰成為城市記憶、城市風景的載體,所以這是非常值得琢磨,不斷深度發掘的城市影像題材。
我拍的很多內容,比如一個爛泥塘、一張斑駁的海報、汽車雨刮器留下的痕迹等。都是一些很具體但是又有象徵性的意象,這也是我在手機微攝影中追求的以虛擬實或是說虛實相生的美,它也是中國傳統美學核心要素之一。

《坐看雲捲雲舒》 徐明松
Q:您生長於上海,也拍上海,如果用幾個意象形容上海,您會選擇什麼?
A: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定義很多事情很困難,它很像哲學中的命題:當你問我時間是什麼,我無法描述時間本身,因為我身處時間之中。就像我們站在城市當中卻看不見的城市,該如何去描繪它。
我願意稱上海為魔都,以為她確實魔幻。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或者新上海人,都能感受到上海很獨立的特質:它的不變就是變化。所以當攝影者面對城市,它有那麼多題材,你可以從中不斷發現最新鮮的東西。
我想起日本攝影家杉本博司的一組拍大海的作品,每個人都能拍大海,但是他拍的大海非常安靜,表達了他對人、生命跟自然、宇宙之間的循環往複的關係。這種哲學關係使我們看影像的時候,覺得它可以不斷被發掘。同樣,我們的前輩拍了很多上海,但是今天的城市永無定式,攝影是流動的,這個城市是流動的,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

《看不見的城市之驚詫》徐明松

《水何澹澹》(組圖之一)徐明松
Q:什麼樣的畫面瞬間讓您有拍攝衝動?
A:如果一個人有敏感的心思,他很容易在很多別人看起來類同的事物中發現情感。視覺的畫面,就是能不能找到跟你共情的人。也有很多作品很理性,但是理性也是一種感動。感動會讓你的視覺對象跟作品建立聯繫,產生再次創作。
Q:您是敏感的人嗎?
A:我認為我是敏感的人,我是雙魚座,心思可能更細膩一點。我有幅作品叫《兩個人的車站》,以前不叫這個名字,不少藝術家跟我講這張作品太好了,其實拍攝時並未觸動我的敏感,但是當別人不斷提醒我,情感效果就會累加。所以我改成了這個名字,為什麼叫兩個人?站台上有個人,還有個人可能在趕來路上。這個文學意向使這個作品與大家的共情之間建立了這種聯繫。所以可能別人七分滿意的作品,我只有五分滿意,也有可能我有七分滿意的,別人只有三分滿意?我們就是在不斷讓人跟你共情,這就是藝術傳播的目的。

《看不見的城市之兩個人的車站》徐明松
Q:這些年您一直在不停拍,日常朋友圈也有大量作品更新,您如何保持創作力?
A:也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攝影跟繪畫不同,它很便捷,沒有那麼長的創作過程。我的攝影類型不拘泥於題材,我關注的是身邊的細節,我的視角不同、構圖不同,任何東西都能納入其中,所以我永遠不會枯竭,只要你有創作的熱情,總能尋找到可能性。那麼你會不會厭倦?我也有過,就是發現自己拍的東西跟之前的創作有雷同。但後來,我想我積累的海量圖片就是我的圖像史。
再者,微信朋友圈是很重要的社交內容,你會被不斷鼓勵、跟別的藝術家溝通,所以我的創作熱情一直沒有衰退。這是迄今為止我還比較自得的一件事。有時候開車,天下雨了,我會把車停到合適的地方去拍雨水、拍擋風玻璃朦朧和模糊的意象。所以要不斷發現周邊,保持一種習慣。保持敏銳的感受力對於視覺或者文字工作者是第一位的事情。
Q:您提到雷同,可以理解為即便跟過去相似也是您個人風格的體現嗎?
A:也不叫個人,我並不把相似看做相似本身,任何一個瞬間都是歷史,而照片是虛擬世界跟現實之間的對話。從個人來講,你拍的場景,哪怕有細微的變化,都可以有不同解讀。就像為什麼有時候我會發一組作品出來,其實每一張都是不同的側面。可能你只要選一張就可以了,但是在我看來這些東西的存在本身就有價值。
林路老師曾評價說我的手機微攝影作品有種禪意,他原話講的是「徐明松的手機微攝影,讓我們看到骰子的第七面」,在很多人倡導元宇宙的當下,骰子可能有第七面。所以,我有個口號就是「將手機攝影進行到底」。

《時間的記憶》徐明松
Q:回頭看,您的微攝影作品同十年前是否有變化?
A:我早期的微攝影稍微粗糙一點,但是我的拍攝方法和理念基本沒變,我喜歡拍折射的反光、虛擬的光影,喜歡用東方美學的東西去表達,可以說其中的脈絡基本是一以貫之、不斷深化的。
但攝影也存在一種可能,就是十年前的攝影作品,你現在再也拍不出來,就像十年前的文章,你今天也寫不出是一樣的,因為它是瞬間捕捉的東西,藝術很多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跟每個人所處的環境、心境都有很大關係。

Q:林路老師評價您的微攝影作品是一種被打破又重建的『秩序』,您如何實現這種打破與重建?
A:我想到兩幅作品,一張是《伸出你的手吧》,它是一本畫冊里很著名的圖像,畫面中女性的手幾乎要伸出畫外,我拍攝的時候就把自己的一隻手伸到鏡頭前,似乎跟圖片里的人有呼應,這就是在解構原作品同時又重新構成了我自己的攝影作品。

《伸出你的手吧》徐明松
這是我在拍攝時使用比較多的方法,再比如我拍了一個人體雕塑的剪影,畫面看上像是大海,實際上是衛生間藍色玻璃形成的意象。我拍了這一逆光的景象後,起了帶有文學性的名字《面向未來的藍色遐想》。

《面向未來的藍色遐想》徐明松

《夕照下》(對話鐘鳴)徐明松
在《微影海上》的第五部分,我給一些上海的藝術家朋友寫的十篇評論,與此同時,我用影像的方式跟他們對話,這是很有趣的。
我舉個例子,何曦有組玻璃的作品,上面有隻鳥在城市中飛,感覺存在無處不在的阻擋,彷彿一層層玻璃把人和城市形成了噩夢般的空間。後來我到了他的工作室,把這幅作品反射的影像拍出來,從視覺上看,好像一隻要飛到重重高牆之外的鳥,我把這幅作品稱為《天邊外》,這也是挪用和重構。

左:《陌生》何曦 右:《天邊外》徐明松

《看見莫迪里阿尼》徐明松
我也通過攝影與歷史上的一些大師們對話。因為日常生活中很多景象跟大師們的作品有某種相似性,我把它們拍下來,我的作品就跟他們實現某種連接,比如有致敬里希特的作品、致敬羅斯科、莫蘭迪的作品,還有致敬愛德華·韋斯頓、曼·雷的作品。這些都是我跟藝術對話的方式,它已經超越了攝影本身,也是我倡導的——手機微攝影要反映創作者內心以及對世界的理解。

《青椒的聯想》致敬愛德華·韋斯頓 徐明松
Q:您剛剛講到一些藝術家和攝影家,除了這些,您也很喜歡文學、哲學。
A:我覺得閱讀跟攝影之間的關聯度,可能不會顯性地反映出來。中國人一直講「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大量的閱讀,特別是讀藝術相關的書籍,會讓你對美的感知力更強。
我是讀中文出身的,從事了30多年的藝術出版,一直在跟藝術、藝術家打交道。長期的積累讓我不自覺形成個人特色。有人覺得我的作品非常有詩意,有人覺得我的某些作品更接近繪畫,我想在全媒體時代,這些都不應該成為問題,你對它的理解也是你的長期的積累、你的悟性。至少從我個人的創作來看,我從不把攝影看作孤立的藝術樣式,它和其它美術樣式都是跨界的、融合的。
這本書里有將近200幅微攝影作品,每幅的題目都想賦於文學色彩,這些文字不僅是對圖片的解釋,有時候讓原先的畫面產生新的可能性。

《蘭馨溢窗外》徐明松
比如,我曾在西班牙拍夕陽西下的教堂的時候,畫面突然抖了,出現了並不逼真的、晃動的影像,可能它對很多攝影者就是廢片,但是我把它取名《聖音》,換成文學意象去表達,有種唱詩班的聲音在空中震動的感覺,就完全不同了。再比如我拍了張宣紙,紙上是一幅蘭花作品,我把宣紙旁邊的窗戶也拍進去了,取名《蘭馨溢窗外》,讓人聯想起蘭花的香味溢出窗外了。
我覺得文學和視覺有很多連接,有時候會反哺畫面,這也是通感,它需要攝影家不斷積累。

徐明松
Q:近些年當代藝術受到推崇,繪畫如此,攝影也是如此,有些作品當然很好,有些看完後卻覺得空有形式,您覺得這兩者之間如何辨別。
A:攝影發展到今天,已經無法被狹隘定義了。1839年攝影剛開始出現,完全是表達世界的一種新的存在。一百多年過去,無論是表現性的攝影還是紀實攝影,無論是把攝影與設計結合的莫霍利.納吉還是現在常提的觀念攝影,都跳脫出我們對攝影的常規理解。在當代藝術中,攝影、攝像已經成為普遍使用的媒介,它是藝術家重新觀察世界的方式。很多人說後期改變了原有的圖像,我不以為然。
很簡單,攝影從開始就存在後期——暗房,隨著時代發展,到了數字時代,photoshop就是新的攝影暗房。中國著名的攝影大師郎靜山的很多圖片也是後期圖像的整合,儘管這棵樹不是拍攝的那棵樹,但它恰恰體現出中國山水畫的意境,所以我們不能用固化思維思考後期。
但是有些攝影作品確實看起來很空洞,比如我們看到很多相同題材的攝影——天光雲影、沙漠大海、青藏高原等等,你會覺得厭倦。問題在哪裡?就是所有的影像,其中也包括繪畫圖像,都存在著藝術家創作的思想性。但是我們現在存在的是什麼?大量的形式美感。我稱之為「糖水片」,經不起推敲。
我舉個例子,就是到了荷花節或荷花盛開的時候,滿坑滿谷都是拍荷花的人。拍出來的作品大同小異,只有光影、線條等形式美感,缺乏攝影者本人的思想認知。上海畫家何曦,他也拍荷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曾出版過他的畫冊,他視覺中的荷花完全不同。攝影家如何尋找它的思想性?數碼攝影成為大眾攝影時,手機攝影是不是意味著新的可能?這是我在尋找的。

《痕迹》徐明松

《迷失的時間》徐明松
Q:您也說過「這是一個後波普的時代,也是一個影像生存的時代」,各種媒介交融,我們表達的形式更多,但是另一方面無論是城市建築還是人的個性都越來越類似,您覺得年輕攝影人如何找到自己的風格?
A:為什麼會有雷同化的存在,某種程度上跟我們傳統文化中集體意識的反應有關。在我們的潛意識中習慣看到別人的好,但是能不能發現自己的好,發現自己的潛力?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創作者,特別值得思考的。你發現了自我才能發現世界的精彩。否則這種精彩是別人的精彩,不是自己的精彩,攝影要發現自己的精彩。
我常說:「我看見的你,就是我自己」,從美學的角度理解就是美是主觀的,美是客觀的,美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你是影像的主宰者,你在那個決定性的瞬間里呈現的是自己。
布列松那張很有名的《帶著酒瓶的小男孩》,一個小男孩抱著酒瓶,在鏡頭前吹著口哨,很喜悅地往前奔。很多人也能拍,關鍵你是不是第一個。同樣,羅中立的油畫作品《父親》,滿臉滄桑的老農民,從寫實的角度講當時很多專業畫家或許能畫,但是藝術家不是技術本身,藝術家要表達對時代的感知力。
在那時,羅中立突破了畫巨幅領袖肖像的束縛,用強烈的視覺張力表達了中國社會的農民,這是他的思想性。我覺得所有的創新都不是空穴來風,它在於你的積累,攝影是一個尋找自己的開始,這很重要。

《時間的肌理》徐明松

《生活的漫歌之秋深的街》徐明松
Q:您覺得未來的手機微攝影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A:我完全不懂技術,所以無法想像未來技術生活的場景。但我曾看到一篇報道,說是手機未來會跟人的身體結合,在這個時候,你的物理空間就跟數字環境融為一體了。比如我們看到鄧麗君在台上唱歌,這就是用模擬影像的方式讓人實現跨越空間和時間的交流。數字化時代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假難辨。
最近有公司來找我做NFT,我也做了嘗試。我覺得它也是探索的過程,就像攝影剛剛出現的時候,花了八個小時才完成曝光,到了上世紀30年代以後,攝影就跟當時的藝術思潮結合,產生畫意攝影、印象派、實驗攝影等等,這些都是跟時代同步的,手機微攝影也在與時代同步,但它的未來不可限量。
Q:最後一個問題,作為第十二屆人與環境攝影大賽的評委,您的標準是什麼?
A:我更關注人與環境攝影大賽的主題演繹,希望糖水片越來越少。我更注重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性的力度。往年評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些人文類攝影,顯得雷同化、扁平化、淺碟化。我認為即便是自然攝影,也要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識。就像我們看杉本博司的大海,會看到久久的平靜一樣。所以,我覺得攝影者要表現他獨特的藝術感受力。
另一方面,我覺得人與環境攝影大賽確實也走到了需要反思和總結的階段,我們積累了很多好作品,如何挖掘它們的人文內涵?建議可以做一些論壇、研討會,進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