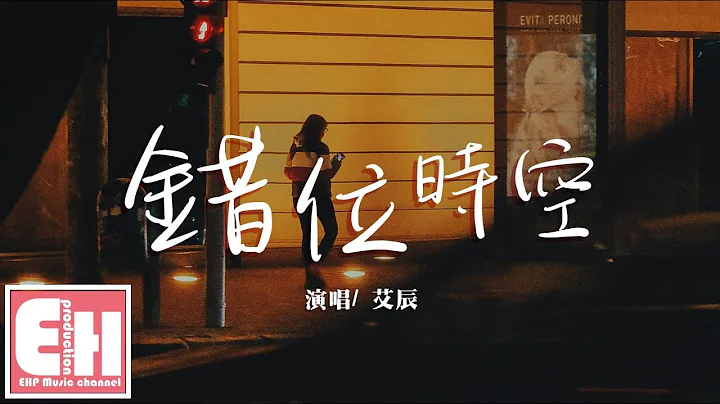布光是電影攝影創作中最關鍵的環節之一。從早期黑白默片中人像和場景照明慣例的形成,到彩色膠片出現後大量使用的彩色光效,不同時期的電影都有著屬於所處時代特點的光影效果。
本文將目光聚焦於當下由於使用數字攝影機而給電影布光帶來的改變,從電影中的人像布光和場景布光中體會創新之處。
自然的膚色
在人像布光中,數字電影大多繼承了膠片中常使用的布光方法和觀念,以三點布光法為基礎,並根據影片整體的風格來決定人物光效的特徵。
使用數字攝影機拍攝對人像布光的影響依舊與膚色的表現有關,如果說膠片已經具備了展現正常人物膚色的能力,那麼通過利用數字感測器捕捉光線以及感知色彩的能力,能夠使人物的膚色呈現地更加自然。


數字攝影機的感測器可以捕獲到人眼無法感知到的紅外光線,有攝影師特意使用紅外線為角色布光探索新的光源下對人物面部的影響力。《謝里》(Cherry,2021)中是一部講述患有戰後創傷應激障礙的影片,謝里從戰場回到女友的身邊之後,精神的創傷讓他開始通過吸毒麻痹自己,最終毀滅掉了自己的生活。
影片中謝里和女友艾米麗二人狀態和關係的變化是故事敘事的主線,在二人少年時期剛剛相愛時,攝影師嘗試探索人物面部細微的變化來表現艾米麗真實的情感狀態,
使用只有攝影機才能識別的紅外光線為她打光,由於在拍攝現場人眼無法識別紅外線,這種效果只有通過監視器才可以看到艾米麗的臉龐微微泛紅,以此來表現她此時內心地興奮。


這種紅外光線給人物面部帶來的獨特的表現力離不開數字攝影本身獨特的影像獲取方式。
在談到數字攝影機對於膚色的表現力時,攝影師史蒂芬·菲伯格曾說過:「RED 攝影機拍攝人臉時會捕捉到許多面部的瑕疵,所以在拍攝時習慣使用反彈的柔光或者格柵來柔化光源。」
雖然整體上來看數字電影與膠片電影在為人像布光時沒有太多本質上的差別,但是數字攝影機在表現這種角色面部細微的光線和色彩的變化上更有優勢,為攝影機捕捉人物的情感變化提供了便利。
從模擬夜色到真實夜色
與場景布光有關的發展與改變更多地只涉及到了攝影棚和實景拍攝之間的轉化,而有關如何為夜晚實景進行布光,一直以來是電影攝影布光的重要議題。


夜景是許多電影敘事中必不可少的場景,但是由於夜晚的照度通常很低,曾經一段時間內如何為實際的夜景布光一直是個難題,在電影發展歷程中創作者們總在不斷嘗試各種技術手段來展現夜景,努力在技術的局限和藝術創意之間尋找平衡。
從膠片攝影到數字攝影,夜景的布光方法和效果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1、模擬夜色
在數字攝影機出現之前,人們通常使用各種攝影技術來模擬出印象中的夜景效果。
電影誕生初期,通常使用色彩來象徵黑夜。早期黑白膠片的感光度很低,夜景通常是在全日光的情況下拍攝的,在後期洗印膠片時使用著色法對夜景和日景進行區分。


在色彩的選擇上,通常使用藍色染料對需要呈現為夜晚的場景進行上色,被火光照亮的室內場景一般則使用紅色染料,這種通過著色來區分場景的方法在19世紀20年代被廣泛使用,完全以黑白效果呈現的電影反而比較罕見。
隨著聲音的引入,著色工藝開始變得罕見,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用於著色的染料會影響膠片對於聲音信號的記錄,導致現場錄音的質量變差。
最主要的還是因為著色法對於電影場景的特徵只是一種象徵的表現方法,與隨著聲音的到來而建立的審美現實主義的新標準並不相符。此後,人們才轉為通過布光的方式來表現夜景,出現了各種模擬夜景的方法。


在早期黑白電影當中,主要通過增加畫面中的陰影範圍和光照對比度來表現黑夜的整體視覺感受。
在為畫面中的物體或者人物進行布光時,依舊以體現光線的「造型性」為原則,大部分的夜景中的燈光只用來打亮前景中的人物或者景物的輪廓,以此來將人物和畫面的前後景分離。
後景會使用各種小型燈具來營造畫面的縱深感,同時在鏡頭前配合使用柔光鏡對畫面整體進行柔化來模仿月光的效果。
在影片《一夜風流》中,大量使用這種方法來營造出浪漫的夜景效果。攝影師使用一個正面的主光照亮埃莉(Ellie)來減少人物面部陰影,使埃莉的臉部看起來更柔和,同時強烈的背光為人物的輪廓提供高光,柔光鏡的使用為高光帶來了額外的光彩。


這種高光同時也可以讓畫面的亮部和暗部的過渡更加柔和,表現出人們對於浪漫夜晚的主光感受。這種方法是在30年代浪漫愛情劇的最常用的夜景布光方法。
這種基於光線造型作用的夜景布光方法一直沿用到了早期的彩色電影中,主要利用光線不同的色溫的光線來表現夜晚,
在《亂世佳人》的夜景中,通常使用高色溫的燈光模擬月光來勾勒人物的輪廓,使用同色溫的補光使畫面變得柔和。這些早期經典的夜景布光方法,至今仍在沿用。
除了上述利用光線造型作用營造夜景的視覺感受外,在拍攝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還經常使用日拍夜的方式來拍攝夜景外景,在拍攝過程中需要配合攝影濾光鏡的使用來過濾暖色的光線並降低曝光,布光時則要刻意模擬出在夜晚才有的光照感覺。


70 年代前由於膠片的感光度還不足以在一般夜景照度下曝光,大量的彩色電影使用此種方法來拍攝夜景。在《音樂之聲》中,朱莉離開豪宅並走到湖邊的場景就使用了日拍夜的方法。
攝影師在湖的對面布置了一排大功率的白熾燈泡,用來模擬成夜晚公園裡的照明燈,同時用來提升畫面整體的亮度作為場景的底子光。這些燈的功率很大,足以蓋過原本的太陽光,並能夠在水面上投下美麗的倒影,給人一種涼爽的夜色的感覺。
在後期膠片洗印過程中,為膠片降低一檔曝光,使得畫面中的顆粒更加細膩色彩更加紮實,雖然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背景中山的輪廓,但也會給人感覺故事是發生在月色下。
這種夜景拍攝方法對於前期場景的選擇和布光、以及後期膠片洗印時的曝光控制都有較高要求,如果取景時不慎將晴天的白雲拍入畫面,或者是前期畫面過亮產生大量噪點,都會影響到對夜景效果的呈現。


隨著彩色膠片的感光度越來越高,已經能夠在真實的夜晚下拍攝,逐漸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夜景布光方法:使用大功率鏑燈或者柔和的氣球燈作為場景主光來模擬月光或天空光,畫面中的人工光源大多使用低色溫的暖色用來和夜色進行區分。
為了使畫面更有深度和層次感,通常會在畫面的後景中放煙,並從逆光的角度將空氣中的煙霧顆粒照亮。
從根本上來看,這種方法還是通過光線來營造出人們心目中的夜景感受,更多的是一種「概念」性的夜晚,與我們生活中的真實夜色還有很大差別。直到越來越多的電影開始使用數字攝影機進行拍攝,電影中的夜景才開始變得不一樣。


2、真實夜色
數字電影中的夜景不同以往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現在電影布光多使用邏輯光源,避免了無依據光源的人造感。
另一方面主要是數字攝影機對於暗部光線的敏感性為夜景拍攝時打破常規的嘗試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許多電影創作者通過簡化夜景中大量的人工照明來呈現不同於以往的黑夜。
大衛·芬奇的影片《十二宮》是當時好萊塢第一批眾多使用數字攝影機進行拍攝的影片之一,由著名攝影師哈里斯·薩維德斯擔任攝影指導。
整部影片的照明風格遵循了自然、真實的原則,對大量的無邏輯的造型光做了省略。


影片以國慶節慶祝活動的宏偉航拍鏡頭開場,然後切換到從汽車上拍攝的一個橫移長鏡頭,汽車穿過燈光昏暗的郊區,正在慶祝的酒吧、玩耍的孩子和星星點點的煙火點綴了平凡的場景,這個開場鏡頭迅速確立了影片整體的基調與夜晚有關,畫面大部分景物處於陰影之中,但同也保留了大量的細節。
在拍攝時只對房屋門前和花園中使用了小型鎢絲燈泡作為邏輯光源進行照明,所有房屋內部沒有任何燈光,在鏡頭移動結束時,攝影機的左側放置一盞20k的鏑燈來勾勒整個場景的邊緣,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光源,當這對情侶把車開到無人的郊外時,使用一盞泛光燈模擬路燈來拍攝汽車內的夜景,在畫面遠處布了另外一個10k的鏑燈作為場景遠處街道的燈光。


影片中的大量夜景都對傳統的夜景布光做了簡化,對光源的設計很大程度上依據的是環境中的已有光源,最大程度上保持了真正的夜晚的感覺。
《獵殺本拉登》是另一部近年來對夜景效果的呈現有最大突破的影片。該片記錄了對本·拉登長達十年的追捕,以及2011年在巴基斯坦進行的秘密獵殺行動,拍攝的地點和情節決定了影片場景會處於兩種極端的光效之中:
一種是中東地區日景的刺眼光線,畫面中會有大量高光;另一種是突襲行動的夜晚,沒有任何多餘的環境光照,畫面照度極低。
為了能夠捕捉到光比如此之大的動態範圍,攝影師格雷格·弗萊瑟使用有較大寬容度的愛麗莎攝影機進行拍攝,為突襲的夜晚布光時,在院子上空的腳手架懸掛了兩個燈箱,每個燈箱中放置 24 個Kinoflo 熒光燈管,使用柔光布對燈光進行柔化,用來模仿夜晚月色下昏暗的頂光,創造出了一種「零人工光照的假象」。


當從院子進入到室內時,使用一些小型 LED 光源和火光作為邏輯光源來引導觀眾的視線,除此之外沒有使用其他任何的人工照明。影片以此種方式呈現了完全不同於日拍夜或者有大量人工光源的夜景效果,給人帶來一種真實的夜晚觀感,令人印象深刻。
除此上述兩部影片外,由邁克爾·曼執導的《借刀殺人》《邁阿密風雲》《公眾之敵》等影片中,都利用了數字攝影機對低照度下的光線更敏感的特點,在拍攝夜景時僅僅利用環境中的現有光線進行拍攝,只有在演員特寫鏡頭時才對面部進行補光來減少噪點,完全摒棄了以往對夜景進行刻意布光的觀念。
(內容、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