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7月甘肃理论学刊 JuL.,2012
第4期总第212期 Gansu Theory Research No.4 General 212马克思主义研究
农民的前途: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的理论分歧
王勇1,郭倩倩2
(1.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兰州730070;2.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兰州730070)
[摘要]围绕农民的前途,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两派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澄清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在关于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分歧,有助于从根本上理清当下中国关于农民问题的纷繁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立场,进而为当下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的区别,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并不单纯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而是“革命派”和“渐进派”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这个大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分歧,主要分歧在于方式、方法和途径上,借鉴两派观点中合理的成分,对于当代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进而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老加图主义;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一4307(2012)04一0072一04
一、农民问题的两种思潮
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毋庸置疑,农民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所共同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围绕农民的前途,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两派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对农民进人现代工商社会持乐观态度,认为农民的出路就是经由农业现代化而最终转变为工商从事者,只有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趋势,农民才能有真正美好的前途。保守派则对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对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忧心重重。认为城市化为大量侵占有限的耕地,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计算,2001年每天大约消失76个村落,2002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0个村落,2003年大约为每天消失43个村落。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3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生命。与此相关的数据是,由于农田被大量非法侵占与不合理使用,从1996年至2004年全国每年减少大量耕地。大量到什么程度?一说500万亩,一说1000多万亩,一说3630万亩。无论以哪个数据衡量,任由土地如此锐减,那么中国的耕地全部消失的日子就不会十分遥远。显然,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保守派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是一个“农民的终结、“村落的消失”、“土地的黄昏”2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即将发生重大转型的关节点上,理论界涌现出各种思潮是很正常的现象。实践中的理论分歧远不止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不过,改革派和保守派是两种基本的理论立场和意识形态,其它理论观点大多是从这两个基本的理论立场上分化出来的。因此,本文将侧重于探讨这两种理论的思想渊源。研究发现,这两派的理论渊源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在关于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分歧,我们就能从根本上理清当代出现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纷繁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立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从学术视角进行的讨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与所谓的“新右派”与“新左派”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二、“老加图主义”的观点:回归田园
在西方,老加图主义观念出现在以奴隶劳动经营其领地的老加图主义(公元前234一149)时代。这种思想也就是以老加图这个领主的名字而著称于世。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一前149年)通称为老加图(CatoMaior)或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前195年的执政官。他也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老加图曾写过《农业志》这样一本书,这是一本论述奴隶制大庄园经济的著作,全文尚存,是加图最受赞誉的作品,大约完成于前160年。此书对于研究意大利前2世纪的经济状态有重大意义。加图本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地产者,他在书中总结了经营奴隶制庄园的许多经验,还描述了奴隶的生活状况。加图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
在关于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上,老加图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巴林顿·摩尔在其《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对老加图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归结和总结。摩尔认为,“加图主义的社会功能十分清楚,它通过论证强迫性的社会制度来为当权者帮忙;它抗拒使农民解体的现实变化;它否认社会有进一步变革特别是革命性变革的必要。”“现代形式的加图主义有着同样的起源,这便是使用强制剥削手段的土地贵族对市场经济日渐侵人农业经济的反应。这种观念的突出代表,包括19世纪20世纪的德国容克地主,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本世纪初俄国的黑帮分子运动,最后以维希作为政治橱窗的法国极端保守派,以及美国内战前南方辩护士中的骨干分子。加图主义是20世纪欧亚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因素,也贯穿于蒋介石对中国的纲领宜言中,”[3399
回归田野,厌恶都市,认为农民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是老加图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老加图主义中有着许多温情的“人文关怀”,在其复杂而矛盾的理论关切中有一个理论轴心,这便是大谈特谈全面的道德复兴,他们以道德清谈取代了对社会主要状况的现实主义分析。摩尔对老加图主义成因进行了深人的分析,“在加图主义眼中,艺术必须是健康的、符合传统的、阳春白雪式的。加图主义艺术观的核心是民间艺术和地方艺术,致力于有教养的市民阶级中恢复农村的礼俗、歌舞、庆典。要描述加图主义赞成什么,必须说明他反对什么。具体而言,他们仇视商人、高利贷者、大富翁、世界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美国,加图主义的态度是,不但憎恶城市式的智慧,而且对一切优异于原始的民间思想的理性精神持敌对态度。在他们看来,城市是毒瘤,充满无形的阴谋家,挖空心思地去欺骗和腐蚀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当然,这种切齿痛恨有着现实的基础,它发源于在市场经济中受到严重挫折的农民的日常生活经验。”]401
在对老加图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摩尔评论道:“反理性、反工业社会前景的加图主义,把现代都市文明看作人性的贬值,看作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知非人格化。”的“在加图主义理论中,组织’和‘整体’是令人心的模糊字眼。农村有组织的生活,据认为优越于原子离散式的现代科学世界和现代都市文明。农民和土地的联系,已变成一个宣传远甚于实际的题目。带着怀古之幽情的传统的宗教虔诚风靡一时,这种传统有如日本的神道,已在很大程度上初改造为社会制度,不过并不是全盘复古。”[。显而易见,在摩尔眼中,老加图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混合体,理论立场常常与情感等道德立场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老加图主义常常以道德清谈取代对社会主要状况的现实主义分析?这大概与老加图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老加图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典型的保守派人物。他靠追随保守派起家,坚决维护罗马的旧原则,对喜爱东方文化的以大西庇阿为代表的另一派人物表现出明显憎恶。在加图看来,罗马社会风气的变坏,几乎全是来自希腊的不良影响导致的(例如,他对酒神崇拜在罗马的出现深表震惊)。这种想法有部分道理:在加图的时代,罗马由于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而从海外获得大量财富。商业与战争带来的利润导致罗马的贫富分化加剧,很多富人开始效仿希腊奴隶主的生活方式(在罗马人看来是非常骄奢淫逸的),在社会上助长了道德败坏之风。加图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他主张维持罗马原有的简朴生活,防止社会分化。然而,加图的见解和他本身却有部分矛盾,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大地产者,而且追求利润(加图在他的名著《农业志》里指出最有利的是种植经济作物,而粮食只排到第6位)。看来,加图只是反对奢侈腐化,而不反对积聚财富
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有学者提出了以农民为“本位”的研究立场,认为学者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研究问题,为农民的利益着想。以农民为本位,立党为公,执政为“农”。这些学者在政策取向上的基本立场是渐进式改革和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以农民为“本位”的研究立场,实际就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三农”问题。在基本的理论倾向上,与老加图主义有相通之处。
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农民消亡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老加图主义对农民采取了静止的、机械的看法,认为农民的身份不会发生转变。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立场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现代工业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一一‘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5578事实也是如此,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变革是加速了以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的解体过程。是什么原因或动力导致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呢?马克思分析:“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912在这里,可以发现,巴林顿·摩尔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也主要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农业商品化、资本化、企业化、工业化、社会化交织在一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这条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了农业改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围绕着农民的解放这个价值关怀展开研究的,他们的研究具体涉及到农奴或封建依附农民的解放与独立的、自由的小农阶级的诞生,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和小农的贫困化,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关系等问题。他们认为,农民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和城市人口,纯粹的小农阶层出现了经济上的贫困化和社会地位的没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前途作出了较早的预言,这种预言无疑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在社会主义阵营以政策正式付诸实践时,却带来了激进主义的后果。马克思经常这样说,手工织机带来的是封建主义,而动力织机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机械化的现代农业是历史发展的必要趋势。对于农场和工厂来说,规模越大、资本越密集就越好。列宁带有极端现代主义的情结。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是一种积极的农民观,是以改革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农民问题的一种社会思潮。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改革派的主要理论资源。不过,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列宁的较为激进的农民观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而不宜全盘接受。
四、城乡统筹发展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前途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的区别,似乎并非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而是“革命派”和“渐进派”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这个大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分歧,主要在于方式、方法和途径上。在当下的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以积极的改革的姿态进行,在理论界也好,实务界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关键在于改革的手段和方式上。渐进派的观点得到了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拥护。但是,对于所谓的激进的改革派背后的一种“革命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这种“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巴林顿·摩尔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判断。巴林顿·摩尔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什么地方的人民群众向往工业社会的来临,倒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民并没有这种愿望。归根结底,一切形式的工业化,都是一种上层革命,是少数人的冷酷无情的历史使命。”[“我很不情愿地说,以上论据表明,现代化所需付出的代价,至少也等于一场革命的代价,很可能还要高昂得多。”“人们看到,未经革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法西斯主义及侵略战争受难者的悲剧,就是实现了现代化却没有一场真正革命的后果。”[41
这说明,发生于当今中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须的代价,是对农民的一个“革命”。目前,中国式“圈地运动”的关键词是强制征收和暴力拆迁。“只要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着世界向着压迫逐渐递减的方向演变,革命的强制思想就是必需的。”2当今中国的“革命”旨在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即减少农民,进而壮大中产阶级和市民的力量。在摩尔看来,只有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运动才称得上是“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林顿·摩尔主张的是一种现代的“革命论”一一即对农民的“革命”。传统的“革命论”:通过发动下层来推翻专制政权;现代的“革命论”:作为上层发动的工业化进程。显然,革命论也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派”背后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和商家共谋进行推动的话,就很值得担忧了。这正是渐进派的理论关切点所在。渐进派特别强调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的保护。“一般来说,革命最可憎的特征,是用恐怖手段压制少数。”[41这说明,中国“圈地运动”中的暴力强拆是绝对要制止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有这样的主张一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应当遵循自愿和示范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498一4在向合作社的过渡上,如果小农还未下定决心,工人阶级政党要给小农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而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因此,可以说,渐进派在道义上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但是,渐进派没有看到,部分农民利益受损,这是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代价。从理想的层面讲,如果我们真正确保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农民利益的完美保护,那么,我们的改革进程将举步维艰,以至于无法进行下去。这样看来,革命派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正是因为如此,当下的改革派从两个方面吸取了其理论资源一一马克思主义和巴林顿·摩尔的“革命论”。只是革命论的理论旗帜并不没有公开地打出来,而是巧妙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后。我认为,解决当今的中国农民问题,渐进派和革命派都有其理论优势,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两种理论的指导作用。
比如在城郊地区,由于农民已经成了真正的“一袋马铃薯”,因此,加快社会重建,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有一定的必要性。农民什么时候是真正的“一袋马铃薯”?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法国小农有一个著名的描述:“一袋马铃薯”一一许多同样的单独个体,但没有整体的结构和凝聚力。但是,斯科特在其《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却作了一个重要的说明。他认为,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逐步衰减的农村社区(实为传统村落)往往成为集体抗议的发源地,而不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与此相反。我相信这个社会解体的逻辑是上述事实产生的关键因素。移民,不管是自愿或是强制的,都会导致原有社区(村落)的消失,而代之以新居民的无组织的聚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人更接近于“一袋马铃薯”,是不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在村庄(传统村落)中的农民。[]254事实上,中国传统村落里的农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袋马铃薯”。因为,那时的农民至少还存在宗族、血缘等社会联系纽带。当然传统村落中的社会纽带彻底解体,而农民又大规模流动起来的时候,农民才更像是“一袋马铃薯”。因此,当下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才是真正的“一袋马铃薯”。这是建国以来,离散化程度最高的时候,这也是农村社会政治形势变数最大的时期。这在客观上为农村“社会重建”一一社区建设提出了极为紧迫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的过渡形态,最终目标是“道路通向城市”。
但是,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边远农村,渐进地推动城乡一体化是明智的。也就是说,要尊重中国现实存在着的差序格局,循序渐进地进行。如果说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一揽子工程”的话,这个工程在各地区的规划和推进就有必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比如,在中东部地区,星罗棋布的中心城镇(市)已经由一个发达的交通网所联接,城市是作为一个个的“田野明珠”而呈现的,介于这些中心城镇之间的村落距离中心城镇并不遥远,而且交通相对便捷,因此,村民将很容易直接流动到城镇。社区建设定位在“地级市”乃至省会城市的接点上较有前景。也就是说,如果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在规模上、品味上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规划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在其建设之日即沦为“空心化”社区的命运。
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情况略有不同。这里的城市往往呈现为一个一个的较大的“戈壁绿洲”,而村落则呈现为一个一个的小的“戈壁绿洲”。城镇对乡村的辐射半径较大,中心城镇数量较少,且相互之间的相对距离相对较远,交通条件及路网建设相对滞后。因此,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由中心城市直接带动乡村发展的代价较大,城乡一体化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作为向城市化的过渡形态的农村社区,在西北地区其存续的时间可能相对较长,可能会有更多的容纳空间。社区建设定位在“乡镇”乃至县城的接点上较有前景。另外,西部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后发的村落形态作为一种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风险的先期防范和备选方案是明智的。所有鸡蛋总不能都放在一个筐子里,这是一个朴素的常识。
总体看来,当下正在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最佳的机遇,错过这个宝贵的历史契机,我们就很有可能失去由“农业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个面临关键性的政策方向选择的关头,认真回顾并理清马克思主义和老加图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见解和智识,对于我们做出明智的抉择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张柠,土地的黄昏—一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
[3]老加图[EB/OL].http://zh.wkipedia.org/zh一cn/%E8%80%81%E5%8A%A0%E5%9B%EE,维基百科,
[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1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英]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赵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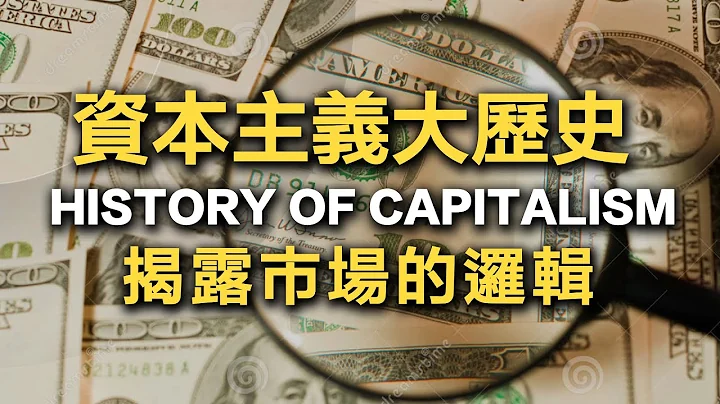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获大赏后全员毫无反应 “你们忘了吗?我们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