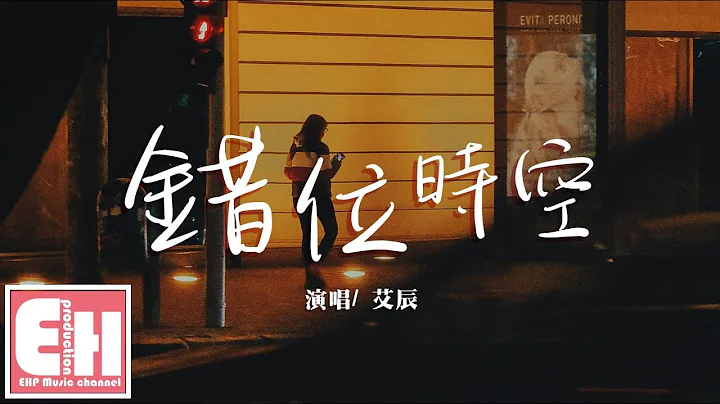《微影海上》新书分享会现场
手机可以拍出好作品吗?
中秋假日期间,徐明松《微影海上》新书分享暨雅集在大沪联合艺术空间举办。作为国内手机微摄影探索者、人与环境摄影大赛多年评委、沪上知名艺术评论家,徐明松将对于文学、绘画、哲学、建筑等的思考融合在作品里,不断打破、重构,在琐碎的日常、破碎的风景里捡拾着诗喃般散落的情绪,呈现出手机微摄影之美。
借此新书发表之际,我们跟他聊了聊他与手机微摄影。
- 徐明松 -

1963 年生于上海。
现居上海,沪上知名艺术评论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上海艺术摄影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艺委会委员,《艺术管理》杂志执行主编、《艺术当代》《创意设计源》《公共艺术》杂志编委。已出版《纸上风景》《建筑乌托 邦:明天我们住在哪里》(合著) 等图书多部,业余兼事公共艺术理论与实践。

徐明松2622
Q:上个月《微影海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否介绍下这本书?
A:这本书是我在疫情期间完成的,虽然做了一辈子编辑,但是从海量图片中遴选作品还是存在困难,不过疫情也给了我沉淀、反思的机会,所以完成的时间不算很长。
它缘起于我在八年前的展览,叫“三言两拍”,有记者查证说这是国内第一个手机摄影个展。除了展览里的作品,书里也包含我的其它手机微摄影作品,内容分为“时间的记忆”、“看不见的城市”、“静观万物”、“生活的漫歌”、“画里画外”五部分。

《生活的漫歌之似索题诗句》徐明松

《金秋》徐明松
Q:您曾经提出了微摄影的概念,可否详述。
A:手机的便捷性和摄影的功能让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把它称为后摄影时代新的美术现象或者摄影文化现象。
《手机微摄影,一种洞察的艺术态度》一文阐明了我对微摄影的观念和理解:“‘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博伊斯的名言在当下成为了现实。尤其是当数码手机旋风式地占据市场进而占据人们的心灵之际,这种手机照相直抵人心的魔力,相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摄影生态的改变而呈现得更为广泛和深刻。因为,如果说照相机只是人们观察与表现事物的工具和视觉延伸;而手机摄影则堪可看作身体机能(与身体关系最为紧密)的延伸和视知觉智能的延伸。它也从此成为微生活圈的构成部分,诸如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自媒体发布与分享手机摄影的个人作品,故名之为微摄影。”

《残忍的四月》徐明松

《都市里的村庄》徐明松
Q:对您来说,开始手机微摄影也是偶然的过程。
A:是的,我在书里的后记里有写,大概十年前,我的朋友,《南方周末》的记者、诗人王寅,把在世界各地游历的采访和摄影作品集合出了本书,叫《摄手记》,由北三联出版,他的文字和影像给我了手机微摄影的初印象,也是诱发我创作的冲动。之后我一发不可收拾,在手机微摄影的领域里探索到今天。
Q:您的手机微摄影和传统摄影的区隔是什么?
A:其实,我也用单反拍过旅行照,不过由于物理负担和技术要求,并没有引发我对摄影的热情。传统的单反相机常用广角表达大场面,空间感更强烈。手机微摄影因为画质的限制,更关注局部、细节,当然随着科技发展,这可能会得到解决。其实问题的本质不是技术,不管是手机微摄影还是传统摄影都反映出我的美术摄影理想。它不仅仅是记录工具,我更在意它的表现力与丰富性,我觉得这种丰富性在手机微摄影时代体现得更彻底。


《看不见的城市之关于海上的N个梦忆》徐明松
Q:您的手机微摄影很多是拍城市,城市中大多数人是奔波的,您的摄影却有着淡淡的诗意之美,您眼中城市的魅力是什么?
A:这个世界上有超过5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书里我引用了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作为第二部分的名字,我很喜欢建筑,如果用传统摄影表达感受,可能会出现很多人熟悉的场景表达,但我觉得如果城市像一片森林,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片树叶,这些断掉的细部、稍纵即逝的碎片,恰恰成为城市记忆、城市风景的载体,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琢磨,不断深度发掘的城市影像题材。
我拍的很多内容,比如一个烂泥塘、一张斑驳的海报、汽车雨刮器留下的痕迹等。都是一些很具体但是又有象征性的意象,这也是我在手机微摄影中追求的以虚拟实或是说虚实相生的美,它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核心要素之一。

《坐看云卷云舒》 徐明松
Q:您生长于上海,也拍上海,如果用几个意象形容上海,您会选择什么?
A: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定义很多事情很困难,它很像哲学中的命题:当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我无法描述时间本身,因为我身处时间之中。就像我们站在城市当中却看不见的城市,该如何去描绘它。
我愿意称上海为魔都,以为她确实魔幻。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或者新上海人,都能感受到上海很独立的特质:它的不变就是变化。所以当摄影者面对城市,它有那么多题材,你可以从中不断发现最新鲜的东西。
我想起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的一组拍大海的作品,每个人都能拍大海,但是他拍的大海非常安静,表达了他对人、生命跟自然、宇宙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关系。这种哲学关系使我们看影像的时候,觉得它可以不断被发掘。同样,我们的前辈拍了很多上海,但是今天的城市永无定式,摄影是流动的,这个城市是流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

《看不见的城市之惊诧》徐明松

《水何澹澹》(组图之一)徐明松
Q:什么样的画面瞬间让您有拍摄冲动?
A:如果一个人有敏感的心思,他很容易在很多别人看起来类同的事物中发现情感。视觉的画面,就是能不能找到跟你共情的人。也有很多作品很理性,但是理性也是一种感动。感动会让你的视觉对象跟作品建立联系,产生再次创作。
Q:您是敏感的人吗?
A:我认为我是敏感的人,我是双鱼座,心思可能更细腻一点。我有幅作品叫《两个人的车站》,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不少艺术家跟我讲这张作品太好了,其实拍摄时并未触动我的敏感,但是当别人不断提醒我,情感效果就会累加。所以我改成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两个人?站台上有个人,还有个人可能在赶来路上。这个文学意向使这个作品与大家的共情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所以可能别人七分满意的作品,我只有五分满意,也有可能我有七分满意的,别人只有三分满意?我们就是在不断让人跟你共情,这就是艺术传播的目的。

《看不见的城市之两个人的车站》徐明松
Q:这些年您一直在不停拍,日常朋友圈也有大量作品更新,您如何保持创作力?
A: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摄影跟绘画不同,它很便捷,没有那么长的创作过程。我的摄影类型不拘泥于题材,我关注的是身边的细节,我的视角不同、构图不同,任何东西都能纳入其中,所以我永远不会枯竭,只要你有创作的热情,总能寻找到可能性。那么你会不会厌倦?我也有过,就是发现自己拍的东西跟之前的创作有雷同。但后来,我想我积累的海量图片就是我的图像史。
再者,微信朋友圈是很重要的社交内容,你会被不断鼓励、跟别的艺术家沟通,所以我的创作热情一直没有衰退。这是迄今为止我还比较自得的一件事。有时候开车,天下雨了,我会把车停到合适的地方去拍雨水、拍挡风玻璃朦胧和模糊的意象。所以要不断发现周边,保持一种习惯。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对于视觉或者文字工作者是第一位的事情。
Q:您提到雷同,可以理解为即便跟过去相似也是您个人风格的体现吗?
A:也不叫个人,我并不把相似看做相似本身,任何一个瞬间都是历史,而照片是虚拟世界跟现实之间的对话。从个人来讲,你拍的场景,哪怕有细微的变化,都可以有不同解读。就像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发一组作品出来,其实每一张都是不同的侧面。可能你只要选一张就可以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林路老师曾评价说我的手机微摄影作品有种禅意,他原话讲的是“徐明松的手机微摄影,让我们看到骰子的第七面”,在很多人倡导元宇宙的当下,骰子可能有第七面。所以,我有个口号就是“将手机摄影进行到底”。

《时间的记忆》徐明松
Q:回头看,您的微摄影作品同十年前是否有变化?
A:我早期的微摄影稍微粗糙一点,但是我的拍摄方法和理念基本没变,我喜欢拍折射的反光、虚拟的光影,喜欢用东方美学的东西去表达,可以说其中的脉络基本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
但摄影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十年前的摄影作品,你现在再也拍不出来,就像十年前的文章,你今天也写不出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瞬间捕捉的东西,艺术很多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跟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心境都有很大关系。

Q:林路老师评价您的微摄影作品是一种被打破又重建的‘秩序’,您如何实现这种打破与重建?
A:我想到两幅作品,一张是《伸出你的手吧》,它是一本画册里很著名的图像,画面中女性的手几乎要伸出画外,我拍摄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伸到镜头前,似乎跟图片里的人有呼应,这就是在解构原作品同时又重新构成了我自己的摄影作品。

《伸出你的手吧》徐明松
这是我在拍摄时使用比较多的方法,再比如我拍了一个人体雕塑的剪影,画面看上像是大海,实际上是卫生间蓝色玻璃形成的意象。我拍了这一逆光的景象后,起了带有文学性的名字《面向未来的蓝色遐想》。

《面向未来的蓝色遐想》徐明松

《夕照下》(对话钟鸣)徐明松
在《微影海上》的第五部分,我给一些上海的艺术家朋友写的十篇评论,与此同时,我用影像的方式跟他们对话,这是很有趣的。
我举个例子,何曦有组玻璃的作品,上面有只鸟在城市中飞,感觉存在无处不在的阻挡,仿佛一层层玻璃把人和城市形成了噩梦般的空间。后来我到了他的工作室,把这幅作品反射的影像拍出来,从视觉上看,好像一只要飞到重重高墙之外的鸟,我把这幅作品称为《天边外》,这也是挪用和重构。

左:《陌生》何曦 右:《天边外》徐明松

《看见莫迪里阿尼》徐明松
我也通过摄影与历史上的一些大师们对话。因为日常生活中很多景象跟大师们的作品有某种相似性,我把它们拍下来,我的作品就跟他们实现某种连接,比如有致敬里希特的作品、致敬罗斯科、莫兰迪的作品,还有致敬爱德华·韦斯顿、曼·雷的作品。这些都是我跟艺术对话的方式,它已经超越了摄影本身,也是我倡导的——手机微摄影要反映创作者内心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青椒的联想》致敬爱德华·韦斯顿 徐明松
Q:您刚刚讲到一些艺术家和摄影家,除了这些,您也很喜欢文学、哲学。
A:我觉得阅读跟摄影之间的关联度,可能不会显性地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讲“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大量的阅读,特别是读艺术相关的书籍,会让你对美的感知力更强。
我是读中文出身的,从事了30多年的艺术出版,一直在跟艺术、艺术家打交道。长期的积累让我不自觉形成个人特色。有人觉得我的作品非常有诗意,有人觉得我的某些作品更接近绘画,我想在全媒体时代,这些都不应该成为问题,你对它的理解也是你的长期的积累、你的悟性。至少从我个人的创作来看,我从不把摄影看作孤立的艺术样式,它和其它美术样式都是跨界的、融合的。
这本书里有将近200幅微摄影作品,每幅的题目都想赋于文学色彩,这些文字不仅是对图片的解释,有时候让原先的画面产生新的可能性。

《兰馨溢窗外》徐明松
比如,我曾在西班牙拍夕阳西下的教堂的时候,画面突然抖了,出现了并不逼真的、晃动的影像,可能它对很多摄影者就是废片,但是我把它取名《圣音》,换成文学意象去表达,有种唱诗班的声音在空中震动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再比如我拍了张宣纸,纸上是一幅兰花作品,我把宣纸旁边的窗户也拍进去了,取名《兰馨溢窗外》,让人联想起兰花的香味溢出窗外了。
我觉得文学和视觉有很多连接,有时候会反哺画面,这也是通感,它需要摄影家不断积累。

徐明松
Q:近些年当代艺术受到推崇,绘画如此,摄影也是如此,有些作品当然很好,有些看完后却觉得空有形式,您觉得这两者之间如何辨别。
A:摄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被狭隘定义了。1839年摄影刚开始出现,完全是表达世界的一种新的存在。一百多年过去,无论是表现性的摄影还是纪实摄影,无论是把摄影与设计结合的莫霍利.纳吉还是现在常提的观念摄影,都跳脱出我们对摄影的常规理解。在当代艺术中,摄影、摄像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媒介,它是艺术家重新观察世界的方式。很多人说后期改变了原有的图像,我不以为然。
很简单,摄影从开始就存在后期——暗房,随着时代发展,到了数字时代,photoshop就是新的摄影暗房。中国著名的摄影大师郎静山的很多图片也是后期图像的整合,尽管这棵树不是拍摄的那棵树,但它恰恰体现出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所以我们不能用固化思维思考后期。
但是有些摄影作品确实看起来很空洞,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相同题材的摄影——天光云影、沙漠大海、青藏高原等等,你会觉得厌倦。问题在哪里?就是所有的影像,其中也包括绘画图像,都存在着艺术家创作的思想性。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是什么?大量的形式美感。我称之为“糖水片”,经不起推敲。
我举个例子,就是到了荷花节或荷花盛开的时候,满坑满谷都是拍荷花的人。拍出来的作品大同小异,只有光影、线条等形式美感,缺乏摄影者本人的思想认知。上海画家何曦,他也拍荷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画册,他视觉中的荷花完全不同。摄影家如何寻找它的思想性?数码摄影成为大众摄影时,手机摄影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可能?这是我在寻找的。

《痕迹》徐明松

《迷失的时间》徐明松
Q:您也说过“这是一个后波普的时代,也是一个影像生存的时代”,各种媒介交融,我们表达的形式更多,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城市建筑还是人的个性都越来越类似,您觉得年轻摄影人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
A:为什么会有雷同化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传统文化中集体意识的反应有关。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习惯看到别人的好,但是能不能发现自己的好,发现自己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创作者,特别值得思考的。你发现了自我才能发现世界的精彩。否则这种精彩是别人的精彩,不是自己的精彩,摄影要发现自己的精彩。
我常说:“我看见的你,就是我自己”,从美学的角度理解就是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你是影像的主宰者,你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里呈现的是自己。
布列松那张很有名的《带着酒瓶的小男孩》,一个小男孩抱着酒瓶,在镜头前吹着口哨,很喜悦地往前奔。很多人也能拍,关键你是不是第一个。同样,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满脸沧桑的老农民,从写实的角度讲当时很多专业画家或许能画,但是艺术家不是技术本身,艺术家要表达对时代的感知力。
在那时,罗中立突破了画巨幅领袖肖像的束缚,用强烈的视觉张力表达了中国社会的农民,这是他的思想性。我觉得所有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在于你的积累,摄影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开始,这很重要。

《时间的肌理》徐明松

《生活的漫歌之秋深的街》徐明松
Q:您觉得未来的手机微摄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A:我完全不懂技术,所以无法想象未来技术生活的场景。但我曾看到一篇报道,说是手机未来会跟人的身体结合,在这个时候,你的物理空间就跟数字环境融为一体了。比如我们看到邓丽君在台上唱歌,这就是用模拟影像的方式让人实现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交流。数字化时代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真假难辨。
最近有公司来找我做NFT,我也做了尝试。我觉得它也是探索的过程,就像摄影刚刚出现的时候,花了八个小时才完成曝光,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摄影就跟当时的艺术思潮结合,产生画意摄影、印象派、实验摄影等等,这些都是跟时代同步的,手机微摄影也在与时代同步,但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Q:最后一个问题,作为第十二届人与环境摄影大赛的评委,您的标准是什么?
A:我更关注人与环境摄影大赛的主题演绎,希望糖水片越来越少。我更注重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性的力度。往年评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文类摄影,显得雷同化、扁平化、浅碟化。我认为即便是自然摄影,也要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识。就像我们看杉本博司的大海,会看到久久的平静一样。所以,我觉得摄影者要表现他独特的艺术感受力。
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环境摄影大赛确实也走到了需要反思和总结的阶段,我们积累了很多好作品,如何挖掘它们的人文内涵?建议可以做一些论坛、研讨会,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