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山東淄博有陳縣令,好到民間去體驗民間疾苦。一天,他趁衙內無事,於是換上便裝,又到民間去體驗生活去了。

他順着田間小道,七彎八拐,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村落。他每到一個村落,看見有農閑的人,他都會停下來與之交談,順便問下他們的生活狀況。可是這一天,陳縣令走了四五個村落,都不見有一個農閑的人。陳縣令自覺無趣。此時,接近晌午,陳縣令自覺腹中飢餓,於是在一個叫做紅葉村的小村莊坐下休息。
陳縣令坐在村東頭大道旁的一棵大槐樹下,他掏出隨身攜帶的大餅,便自顧自地吃了起來。正在他吃得得意的時候,大道上來了一個衣衫襤褸,滿臉倦容的老年男人。
老年男人徑直來到陳縣令身邊,觀看着陳縣令吃大餅,嘴角不停地嚅動。
陳縣令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問道:「你是不是也想吃」。老年男人點了點頭。
陳縣令掏出身邊僅剩的一張大餅遞給這個老年男人。老年男人接過,竟狼吞虎咽起來,好似他有幾天沒有進食似的。
陳縣令等老年男人吃完,便與其攀談起來。原來老年男人姓王,名叫王知三,今年七十八歲,生有三子二女。
家有五個子女,自己卻在路邊行乞,陳縣令深感奇怪,便問道:「你的兒女不管你嗎」?王知三聞言,仰天長嘆,好似有難言之隱。陳縣令想欲再問,這時從旁邊田裡上來幾個中年男人,也來到大槐樹下歇息。王知三見了這兩個中年男人,便默默地離去了。

瞧着王知三離去的背影,陳縣令心想這個老人身上一定背負着什麼故事,否則也不至老來如此!他向坐在樹下的兩個中年男人打聽。
只見一個精瘦的中年男人打量了陳縣令幾眼,說道:「兄弟是外鄉人吧」!
陳縣令道:「我偶爾路過此地」。
只見坐在精瘦男人旁邊的一個絡腮鬍子說道:「難怪你不知道,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王知三呀」!
陳縣令答道:「願聞其詳」。
絡腮鬍子露出輕蔑的笑聲道:「說他鼎鼎有名,那是以前了,現在的他是一個乞丐」。
陳縣令道:「他說他有五個子女」。
精瘦男人接道:「他確實有五個子女,但是現在五個子女都不管他,這也怪他以前太無情無義了」。
陳縣令道:「怎麼個無情無義法」?
絡腮鬍子道:「客官有所不知,這個王知三以前在外經商發了財,可是有了錢之後他的,休妻另娶,萬貫家財一點也不留給前妻,對前妻生的子女也不管不問。相反,他將所有的錢都給了他的後妻,和他後妻的孩子。
後來,在他五十歲的時候,他生了一場大病,他被他的後妻和他後妻的兒子從家裡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與後妻辦理結婚手續,而他置辦的家業又全在後妻娘家那邊。
他被他的後妻逐了出來之後,無家可歸,而又身患重病,便又想尋找其前妻複合。可是此時,其前妻因為撫養五個兒女勞累過度,意外身死,只留下五個子女。
他的五個子女恨其年輕時拋棄他們與他們的母親,太過無情無義,因此在王知三登門求五個子女贍養的時候,其五個子女都異口同聲地拒絕了他。子女不接納他,他之有沿街行乞。」
精瘦男人道:「這也是王知三以前做得太絕之過,如果他對前妻和幾個孩子稍有情義,也不至於此!」

陳縣令道:「那他現居於何處?」
絡腮鬍子道:「村西邊末尾處有一座破瓦窯,他就住在裡邊。」
陳縣令順着絡腮鬍子的指向,從內心也覺得王知三可恨,但他終究是一個讀書之人,又是當地的父母官,遇到這樣的事他不能不管。在二人的陪同下,陳縣令找到了王知三,又找到了王知三的五個子女,曉以大義,王知三才免於行乞,由五個子女輪流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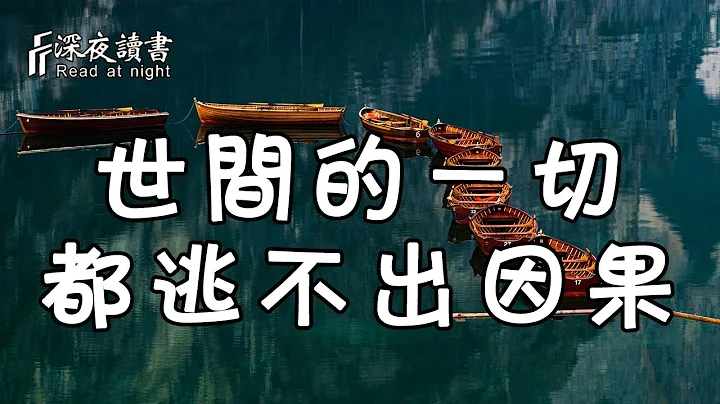










![【搞笑】虧成首富從遊戲開始 [EP176-255] #小說 #繁體中文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lx1W-xi5aE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Qfu9hgfmB9IOhrITD1fLKK0Rf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