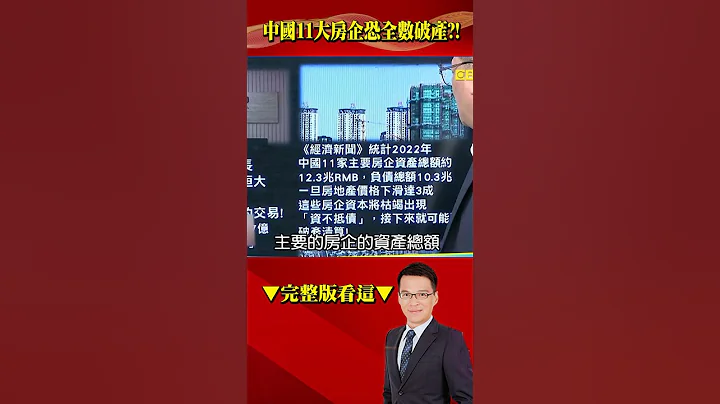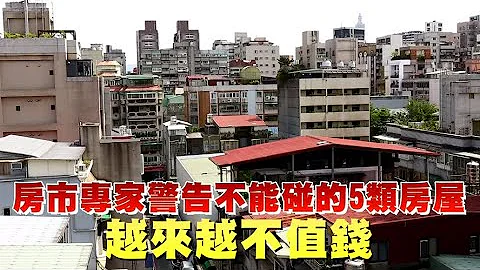李偉 長江商學院 2023-10-23


從恆大到碧桂園,房地產開發商、尤其是全國性頭部開發商的接連爆雷,為經濟的恢復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
對於風雨飄搖中的房地產開發商,該不該救助?該如何救助?
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在財新網發表的最新文章中指出,房地產開發商已經與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完全融為一體,部分頭部開發商的影響已經具有了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要在不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拆彈」化解房企風險——需要救助,更需要整改。
作者 | 李偉
來源 | 財新網
李偉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長江商學院大數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亞洲市場副院長
恆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碧桂園又出事了。
根據2023年10月18日的媒體報道,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簡稱碧桂園)有一筆境外債應於9月17日付息,碧桂園未能在30天寬限期屆滿時向債券持有人支付總計約1540萬美元票面息,恐已屬實質性違約。
中國恆大集團(簡稱恆大)出事後,本來大家認為碧桂園是恆大的對立面,是頭部房企中控制風險較好的一個,但事實證明,我們太樂觀了。
房地產如今爆雷不斷,大量房地產開發商(簡稱開發商)拖欠了相當規模的境內外債務,未來的走向非常不確定。
面對如今的局面,有人認為政府不應該救助開發商,應該讓市場去發揮作用,儘快讓開發商該活的活,該死的死,促使市場重新走向均衡;有人反對這樣的看法,因為一些全國性的開發商已成為了「太大而不能倒」的典型企業。
兩種觀點互相辯論,令人有些暈頭轉向。前路迷茫,一切都伴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不過我們需要做的恰恰是從中去尋找一條正確的道路,跨過這危險的荊棘。
01
救助與否
在進行一切討論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橫亘在我們面前——是否應該救助開發商?
假如答案是不應該救助,那麼我們需要討論這種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以及到時候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假如答案是應該救助,那麼我們可以再具體進一步討論應該如何救助。
閑話少說,我們先來看看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背後的理由。
不應該救助的觀點,其背後最大的理由就是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是一個金融學上的專有名詞,其是在交易之後出現的,指借款人將從事不受貸款人歡迎的活動而使貸款人面對風險,因為這類活動降低了貸款將如期償還的可能性。
例如,一旦借款人取得了貸款,他就可能冒比較大的風險(其收益可能很高,但面對的違約風險也很大),因為使用的是別人的錢。
讀到這裡你會不會產生一種感覺:這個詞似乎是為以恆大為首的一批激進擴張的開發商量身定製的。
以恆大為例,它從銀行融資,從境外資本市場融資,讓供應商和建築承包商墊資,甚至要求員工購買自身發行的理財產品。
根據2023年上半年的恆大財報顯示,許家印個人握有恆大約60%的股權,其利用恆大這個平台從各個渠道融資,融來的錢大規模購進土地,修建住宅,還有一系列低效的多元化投資。
當地產市場紅紅火火的時候,許家印賺得盆滿缽滿。當地產市場下行時,恆大則發生危機,最終搞得公司資金鏈斷裂,資不抵債,但許家印卻已經通過上市公司分紅的方式獲得了幾百億港元的財富。
賭贏了,許家印獲得其中的大部分收益;賭輸了,許家印可以將這個爛攤子甩給全社會。這樣的行為就可以歸屬為道德風險。
假如我們去救助恆大這樣的企業,不等於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許家印導致的窟窿嗎?
這不但有失公平,更是在鼓勵道德風險的擴大。
經濟史已經用無數的事實證明,道德風險擴大只會帶來更大的危機,因此我們不能救助恆大。
不應救助恆大的理由從邏輯上講非常正確,但在現實中卻會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很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風險。
這背後的理由很多,至少有四點:
第一,房地產是中國最重要的行業,沒有之一;
第二,恆大的債務龐大,而且通過各種方式與金融體系存在各種或強或弱的聯繫。一旦恆大倒閉,沒人知道金融體系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三,恆大有大量的樓盤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無法按期完工。假如這些樓盤爛尾,那勢必會引發社會問題;
第四,恆大是頭部開發商,其興衰盛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人們對中國房地產業的看法,甚至是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在這個多事之秋,信心可能比黃金都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恆大的命運有着很強的外部性。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恆大不是一個處於市場核心地位的大型金融機構(這種機構往往具有系統性風險),但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系統性風險。
假如不救助,那麼這可能會成為經濟風暴的導火索,而這很可能是全社會所無法接受的局面。
救助會造成道德風險,不救助則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從整體的社會效應來說,或許最終我們只能採取折中的方案:
一方面救助具有系統性風險的開發商,另一方面加上一系列的限定條件以控制道德風險。
02
恆大人壽模式
實際上,在救助恆大系公司的探索中,政府已經邁出了第一步,即海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海港人壽)對恆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簡稱恆大人壽)實施的貼身監管和風險處置。
恆大人壽屬於恆大系內部的金融公司,由於充當恆大的提款機等原因,該保險公司處於嚴重資不抵債的狀況中。
2023年9月1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簡稱國家金監總局)發佈了關於籌建海港人壽和開業的批文。
同日,國家金監總局深圳局發佈公告稱,批複同意海港人壽整體受讓恆大人壽的保險業務及相應的資產、負債。
海港人壽則在官微發佈公告稱,海港人壽將履行以恆大人壽名義簽署的保險合同義務,切實保護保險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雖然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將海港人壽對恆大人壽採取的措施稱為貼身監管,但從以上公告中可以看出,貼身監管和接管的區別並不大。
在這次的行動中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
一是海港人壽股東的構成。海港人壽的註冊資本金為150億元人民幣,股東有五家。
其中,深圳市鵬聯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地方國企)投資金額76.5億元,持股比例51%;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官方行業公司)注資37.5億元,持股比例25%;廣東粵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廣東省國企)、重慶市渝新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國企)和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央企下屬人壽保險子公司,簡稱太平人壽)各出資12億元,持股比例均為8%。
這樣的股東構成體現了監管層在這方面的思路。
首先,對出險公司的監管以屬地化為重,夯實地方政府在區域監管上的責任;其次,引入官方行業公司和專業公司,為日後的經營打下基礎。
二是高管的構成,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董事長和總經理的人選。
海港人壽的董事長為朱迎,其在監管機構和業界均有長期任職。在出任海港人壽董事長之前,朱迎在招商局仁和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央企控股的保險公司)工作,任副總經理、首席風險官(合規負責人)、董事會秘書。
海港人壽的總經理為喬寧,其為太平人壽原合規負責人、首席風險官。
很明顯,監管層認可保險業的技術門檻,因此調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希望海港人壽在接受恆大人壽業務的時候實現平穩過渡,並改進海港人壽的專業度。
03
四個建議
現在許多開發商所處的形勢危如累卵,如何處置這些開發商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前文已述,一些全國性的頭部開發商,例如恆大和碧桂園,已經具有了系統性風險。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全國性的開發商之外,各地還有大量分散的小開發商,它們能獲得的資源較少,保交樓的難度也不小,因此其生存狀況不容忽視。
開發商已經與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完全融為一體,要在不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拆彈,就好像外科醫生要給被身體組織嚴密包裹的腫瘤動手術一般困難。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筆者有四個建議:
第一,對開發商按照規模和影響力分類,在處理時抓大放小。
這方面我們可以效仿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將那些出險的全國性頭部開發商交給中央政府來處理,或者至少要提高中央政府在這方面的參與度,將區域性的小開發商交給各地政府處理。
第二,引入市場化的機制,對出險開發商合理估值。
從恆大人壽的處理方式上可以看出,政府在處理出險民營企業的時候,有傾向於讓國企接盤的意願。
政府這麼做有一定的道理:
一是各級國企屬於各級政府的抓手,代表着政府的意志;
二是國企的行動更為迅速,在危急時刻,時間就是生命。
然而,國企有三個問題解決不了。
一是民營開發商這次是大面積出險,國企恐怕沒有那麼多人才和資金,很難全部接盤;
二是國企的效率或不如民企,讓國企去接管民企會造成開發商領域的「國進民退」,這會降低經濟效率;
三是出險開發商的價值幾何,這不是國企接管能解決的。
例如恆大目前是嚴重的資不抵債,但其手上還有2.1億平方米的土地儲備(截至2022年12月末),那麼恆大在市場上到底應該值多少錢呢?
因此,國企可以接管民營開發商,但最好不要長期持有民營開發商。
在渡過危險期之後,政府和國企可以儘早在公開市場上通過各種方式,例如招拍掛,將出險的民營開發商轉讓出去。
市場化的處理方式會帶來市場化的價格,這也免得日後為企業估值而各執一詞,甚至對簿公堂。
第三,對出險開發商債務重組。
現在很多開發商深陷債務泥潭,假如不對其債務重組,那麼這部分資產將難以盤活。
我們需要救助開發商,尤其是那些具有系統性風險的開發商,但我們救助的對象應該是交過購房款卻沒有拿到住房的購房者,應該是墊資的供應商和建築承包商。
對於開發商本身來說,我們更需要的是整改。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開發商的股權應該全部清零,一部分債權也必須減值。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減少救助過程中產生的道德風險,才能給社會公眾一個交代。
最後,國際經驗表明,對危機的處理越早,成本越小。
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美國監管層與儲蓄和貸款協會(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簡稱儲貸協會)之間的博弈。
1980年代中期,儲貸協會就出現了危機,但通過政治遊說等方式儲貸協會得以繼續運轉下去。
這滋生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因為許多資不抵債的儲貸協會具備了強烈的動機去冒險:
如果賺錢了,他們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而如果虧損了,他們則無需承擔足夠的責任。
在拖拉多年之後,監管層才最終重組儲貸協會。
假如可以在早期就及時關閉那些資不抵債的儲貸協會,那麼救助成本就可能是500億美元,而非日後的1500億美元。
不過這個例子也清晰表明,改革往往會讓普通民眾受益,但代價卻由小部分利益集團來承擔。
結果呢?這些小利益集團自然會拚死反抗。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屢見不鮮,在我們今後對開發商的救助中,也需要對此類現象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