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電影業逐步復蘇。
令人興奮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
最近,就有消息傳出,昆汀要出來拍片了。

昆汀曾公開表明,自己這輩子只拍十部電影。
因此,這部新片很可能是他最後一部電影。
絕對稱得上,看一部少一部系列。

自從31年前的處女長片《落水狗》一鳴驚人。
昆汀一直憑藉自己獨特的魅力,吸引了無數擁躉。
也以自己傳奇的人生,成為無數後輩電影人追逐效仿的對象。
只可惜,好萊塢至今也未能再誕生一位如昆汀一般極具顛覆力的導演。
在很多人看來,昆汀的電影是暴力、血腥的代名詞,也是玩弄敘事花招、類型拼貼的反叛者。

不過,魚叔卻以為,那些僅僅是昆汀電影的一部分,甚至是最表象的一部分。
複製昆汀的成功,絕不可能只依靠那些花頭。
也有人說,昆汀老了,才盡了,不再像曾經那樣瘋癲、新銳。
果真如此嗎?

昨天,恰逢昆汀60大壽。
魚叔藉機再和大家聊一聊,這個世紀鬼才。
也想告訴大家,這麼多年來,我們或許一直在「誤解」昆汀。


「我是一個專業電影人」
眾所周知,昆汀是個「野路子」。
中學時輟學,短暫地上過表演課,在一家音像店工作長達5年,期間觀看了大量電影。
這些,都是人們知道的事情。
大部分人只拿這些故事當做趣聞笑料,卻很少有人發問:
一個連大學都沒上過的「打工人」,如何可以一躍成為世界電影大師?
有人將他的成功,歸結於暴力美學的創新。
有人則迷戀於,他對敘事法則的徹底顛覆。
還有許多人從迷影的角度,津津樂道於昆汀電影中對各種老電影、B級片的致敬與混搭。

以上這些總結都對。
不過,魚叔想補充一點,昆汀首先是一名專業的電影人。
雖然他從未上過電影學院,也從未接受過系統、專業的電影培訓。
但昆汀在電影知識的學習上,是專業的,並且非常非常專業。
首先,他作為頂級影迷,觀看過數量龐大的電影。
影史經典,熱門商業片,冷門B級片……
好萊塢,歐洲,亞洲……
其次,他不僅觀影量大,還深諳電影中的拍攝技巧。
能夠對各種鏡頭語言、風格設計,如影評人一般品頭論足。

昆汀評價王家衛的《重慶森林》
最後,昆汀精通大多數電影類型的精髓,並能融會貫通。
於是,才有了可以隨心所欲進行混搭,並且效果毫不違和的膽魄和實力。

這其中,分兩部上映的《殺死比爾》就是多元混搭類型的個中翹楚。
這樣一部講述新娘復仇的故事中,昆汀至少塞了三種以上的電影類型:
意大利式西部片。

日式劍戟片。

港式武俠片。

用戲仿和拼貼的方式填滿自己電影,既體現了昆汀的專業與才華,也彰顯了昆汀的頑皮與忤逆。
畢竟作為一個電影創作者來說,最害怕的就是被別人說「抄襲」。
昆汀反其道而行之,生怕別人看不出來他的「巧思」。
《落水狗》中,三人舉槍對峙的經典橋段,源自1987年的香港電影《龍虎風雲》和昆汀最喜愛的電影之一《黃金三鏢客》。


《低俗小說》中蜜兒和文先生經典的扭扭舞片段,借鑒的也是昆汀最愛的戈達爾電影《法外之徒》中餐廳跳舞的橋段。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也是昆汀電影公司的名字。


集大成者的《殺死比爾》,更是將四處拿來的元素,塞得滿滿。
高潮片段「藍葉茶室對決」與石井尾蓮的雪中對決之戰分別來自《武士暢想曲》與《修羅雪姬》。


上:《殺死比爾》,下:《武士暢想曲》
混搭與拼貼之外,是類型的解構。
而解構的前提,依然建立在專業性的基礎之上。
只有對不同類型電影的結構了如指掌,才能找到最巧妙的解套之閥。
例如,在好萊塢常見的犯罪片、動作片中,設置明確的正邪對立兩方是不言而喻的套路之一。
昆汀抓住了這個套路的咽喉,輕巧一轉,便消解了二元對立的枯燥。
處女作《落水狗》中,一共六個主要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是其他角色的對手,彼此間相互猜疑,形成一個多重的連鎖對立模式。
就連作為上帝視角的觀眾,不到最後一刻也無法得知結局如何。

還有《低俗小說》中,真正處於對立面上的應該是黑幫頭目與地下拳手布奇。
可昆汀卻讓布奇在殺了頭目的手下文先生,且讓兩人在共同復仇的前提下達成和解。

理解規則,才能打破規則。
精通套路,才能解除套路。
昆汀之所以能夠以一介野路子,吊打所有專業出身的電影人,立足好萊塢,自成一派。
恰恰是因為他做到了比專業人士還要專業的水準。
「痞子」這個稱號,其實是對他的一種誤解。
雖然外表上看不出來,但昆汀確是一個資深得不能再資深的文藝青年。
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直都在堅持學習,永不停歇。
我一生都在為成為一名專業的電影人而學習,直到死亡那天才會畢業。

「我是一個好編劇」
很多人喜歡昆汀電影里的暴力。
昆汀也喜歡電影中的暴力。
他曾說過,暴力是自己電影才華的一部分,也是一種有人喜歡有人則不的電影口味。
但,這個世界上的暴力電影太多了。
昆汀的電影又有何不同?
實際上,在很多場合里,昆汀強調最多的只有一點——
講故事的重要性。
「當代電影90%的問題出在劇本上,講故事這門手藝已經失傳了」

1994年,昆汀用一部《低俗小說》在好萊塢打響了自己「鬼才導演」的名聲。
故事整體分為三個大章節,每個章節又分成了7個部分。
昆汀將這故事片段打亂重組,利用道具與人物進行巧妙的呼應。
此舉一出,徹底打破了好萊塢長久以來的主流線性敘事法則。

昆汀好像用電影製作了一個拼圖,與觀眾愉悅的玩耍。
觀眾也的確「玩」得十分開心。

電影中的章節標題
其實,這種非線性的敘事模式早在昆汀的處女作《落水狗》中就可見一斑。
這個故事本身並不複雜:
六個相互不認識的強盜計划進行一場珠寶搶劫,結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事後他們試圖尋找隱藏在其中的卧底。
昆汀用反常規的敘事藝術手法,賦予了這個故事不一樣的光彩。
被完全抹去的搶劫過程。
不短插入談話間的閃回敘事。

雖比起《低俗小說》複雜程度只算得上初級水準,但卻讓昆汀以「規則破壞者」的姿態敲開了好萊塢的大門。
這樣的非線性敘事,在90年代後期形成了一股狂潮。
直到21世紀,仍然有不少新銳導演試圖模仿。
一時間,這種非常規敘事成了眼花繚亂的裝X神技。
但昆汀多次在採訪中表示——
「我想要打破敘事,不是為了顯擺智商,也不是為了炫技
而是為了讓影片更具戲劇性」
「我認為電影應該享有小說的自由」

可見,核心要點依然是「故事的戲劇性」。
說到底,也是為了追求「電影的自由」。
因此,當人們以為,昆汀電影即將成為新的風向標時,他又打破了自己的規則——
放棄敘事詭計。
自2007年的《金剛不壞》開始,昆汀不再選擇用眼花繚亂的敘事技巧戲耍觀眾的觀影體驗。
即便也有打出「時間差」的小把戲,但完全稱不上觀影門檻。

如果就此認為昆汀回歸主流,那可是大錯特錯。
進入21世紀,好萊塢十分偏愛史詩級的宏大敘事。
這一點從那幾年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2000年的《角鬥士》,2002年的《芝加哥》,2003年的《指環王:王者無敵》,還有後來的《為奴十二年》。

可是昆汀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選擇用一種戲謔的方式,在電影中「篡改歷史」。
《無恥混蛋》中掃射機槍,噴涌的血漿,燃燒的大銀幕。
昆汀用反常識的手段,直指了「故事」的核心定義——屬於作者的獨立世界。
沒錯,去他的歷史!
在我的世界裏,想怎麼來,就怎麼來。

儘管他本人可能並沒有這個意識。
但說起來,昆汀似乎打響了如今席捲好萊塢「政治正確」大潮的第一槍。
如果說《無恥混蛋》還只是小試牛刀。
那麼,2012年的《被解救的姜戈》則徹底顛覆了歷史法則。
姜戈這個地道的黑奴角色,區別與以往作為被拯救的形象出現。
而是帶有一定救世主的意味遊走在故事之中。
這種設定,在此之前的好萊塢幾乎為零。

以此為基礎,2012年,好像是好萊塢的一個分界線。
昆汀打破的那些舊規則從這一年開始,被一套全新的規則替代。
然而,昆汀可沒有被後續的發展攪入其中。
無論是非線性敘事,還是篡改現實歷史,抑或是玩味政治正確。
在昆汀這裡統統不是唯一的準則。
被改寫的血案,是他心中對於電影歷史與未來的認知:
不被確定,才是電影的本質魅力。
2015年,昆汀推出《八惡人》。
用一個發生在小環境中的「小」情節告訴大家,電影的吸引力到底來自什麼:
故事,永遠是根本。


「我不做打工人」
作為影迷,魚叔常常會回想那個激蕩的1990年代。
那個斯皮爾伯格、馬丁·斯科塞斯、雷德利·斯科特寶刀未老,卡梅隆、科恩兄弟正值盛年,昆汀、大衛·芬奇、諾蘭新人輩出的黃金時代。
反觀現在的好萊塢電影,卻感到越來越缺乏新意。
要麼是千篇一律的超英大片,要麼是套路至死的網飛爽劇。
在某次採訪中,昆汀被問到一個問題:為何不執導超級英雄電影。
他這樣回答:
「要做這件事你必須受雇於人,但我不是僱工,我也不是在找工作。」

在30年後的今天,昆汀似乎是顯得有些「老派」了。
他堅持不拍超英電影,不用數碼攝影,甚至都不再拍攝純粹的犯罪片。
上一部新片《好萊塢往事》,是他寫給好萊塢曾經的黃金年代的輓歌。
下一部新片據說將聚焦影評人。
兩部都是頗具影迷特質的電影。
好像早已脫離大眾喜聞樂見的敘事之外。

可話又說回來。
昆汀又何時歸於主流之內呢。
當年的《落水狗》《低俗小說》到底是一部偽裝成犯罪片的文藝電影。
只是意外引發了好萊塢敘事變革,才逐漸被主流高高捧起。

一直以來,「破局」可以說就是昆汀電影的核心要義。
但他的「破」的,不止是電影的風格與內容。
就像昆汀的電影公司「法外之徒」一樣,他電影的主角也是儘是一些法外之徒和邊緣群體這樣的局外人。
我們常見的正面傳統人設幾乎消失於故事之中。
《落水狗》中的劫匪,《低俗小說》中的黑幫,《危險關係》中周旋於黑白兩道的黑人空姐。

《殺死比爾》中走上日式復仇之路的白人新娘;
《金剛不壞》中邪惡的特技演員與「不純真」的女大學生;
《無恥混蛋》中猶太女孩與戴罪立功的納粹機小分隊;

《被解救的姜戈》的黑人姜戈更不用說,《八惡人》更是魚龍混雜,賞金獵人、奴隸主的兒子、殘殺黑人的昔日少校等。
還有《好萊塢往事》中過期的演員與替身,以及嬉皮士少女。

這些在傳統電影中絕不可能成為主角的人物,卻在昆汀的故事中有了另一層光輝。
反傳統的角色設置解構了好萊塢一貫的人物形象,更是對其他電影的一種反諷,也更能激起觀眾的反思。
昆汀的確是一個喜歡惡搞的頑童。
但他絕不是善惡混亂的人,他推崇的是有信念的人。
在《八惡人》的結尾,黑人賞金獵人與曾經的奴隸主白人靠在一起。
兩人讀着一封偽造的林肯之信。
心中字裡行間充滿溫暖的話語,與周圍滿地的死屍和兩人對立的身份形成一種強烈的互文。
這個畫面傳達的意義,不用多說一個字,觀眾就能深刻體會到。

還有《好萊塢往事》的結尾。
現實歷史中被曼森家族殘忍殺害的莎朗·塔特和她的朋友,卻在電影里四肢健全。
而誤入鄰居里克家中的曼森家族,卻在電影中遭反殺至死。
昆汀用虛構的暴力,還我們一個假象的歷史。
無需多言,讓人倍感溫馨與柔軟。

昆汀既是電影規則的破壞者,也是電影藝術的守衛者。
他從來都很「老派」。
遵循的是一種最古老也最笨拙的電影創作原理:
大量觀影,逐個研究電影類型和拍攝技法,踏踏實實地寫出一個好故事。
他從來也都很「新銳」。
在他固守的核心理念之外,所有的外在法則皆可拋棄。
只有讓電影自由,才能讓電影進步。
這也是為什麼,昆汀始終要保持創作的獨立——
不受制於傳統,不屈服於資本,不投降於主流。
只有獨立的創作,才是自由的創作。

電影表達需要多樣性。
無論是什麼題材、類型,都有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是毋庸置疑的結論。
可惜,這恰恰是我們缺少的部分。
多元和包容,不應僅靠自上而下的干預得以實現。
我們更需要的,是像昆汀這樣的電影人,勇於去填補電影中的現實空白。
規則從來不是困住表達的牢籠。
缺少逆流而上的勇氣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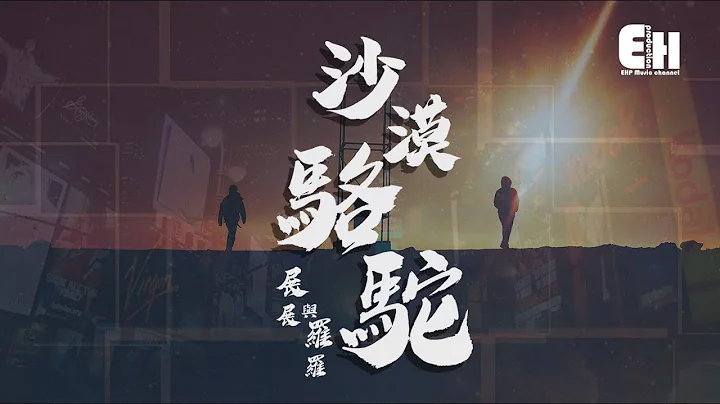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