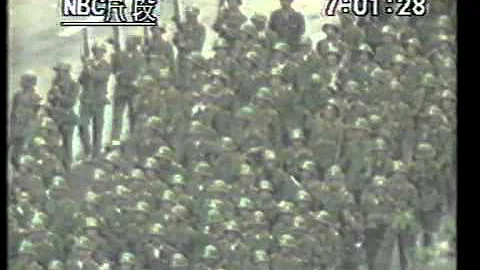本文來源:《英美文學研究論叢》
轉自:敘拉古之惑

1885年,英軍攻佔緬甸首都曼德勒,開始了對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在此期間,駐緬英國人將緬甸人視為劣等人種,而且對於「給土著士兵或傭人造成的不公與苦楚,臣屬國民中僅有的一些職業人士的墮落,以及弱肉強食的自我擴張,大多數英國人甚是自得,或者至少也是默許」。
奧威爾在緬甸擔任警察期間目睹了帝國主義的種種罪惡,儘管他承認英國人在管理緬甸方面確實比本地人做得好,但依舊將殖民統治視為不合理的苛政,並對自己參與其中感到深深的罪責,因此在退役時間尚未到時就辭掉了這份收入頗高的工作——「我確實曾在印度警察隊中服役5年,也確實中途放棄這份工作,部分是由於它並不適合我,更主要是由於我不願再為帝國主義賣力。我反對帝國主義,因為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這段歲月的歷史可以在我的著述中找到,包括一本小說」。此處所指的即是他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故事的背景是在英殖民統治日薄西山之際的緬甸小鎮凱奧克他達,一群英國人相聚在白人俱樂部,整日飲酒,以排遣內心無法言說的寂寞。其中內心柔弱的弗洛里深知英國殖民統治毫無意義,可又缺乏足夠的堅毅,不敢為自己的印度朋友維拉斯瓦米醫生爭取進入白人俱樂部的會員資格。奧威爾在書中不僅對駐緬英國人的生活做了生動的記述,還探討了其中複雜的種族關係,特別是英國人對印緬土著行使權力的各種方式。
從權力關係看種族政治
現代社會的權力行使方式以規訓為主,指的是實現服從的各種系統方法(包括觀察、記錄、計算、調節和訓練等)。根據福柯的觀點,規訓是「一種權力類型,是一種行使權力的形態,包含一整套的工具、技術、程序、應用標準以及對象」。它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權威對個體的塑造和控制。在國家政治的語境下,權力行使方式被阿爾都塞劃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RSA指通過警察、軍隊和刑法制度等手段對從屬階級公開行使權力,這些暴力手段不僅在經濟上花費較高,而且在維持社會生產與階級關係上的效果也並不理想。根據福柯的觀點,對權力的行使必須謹慎小心,以此減少引發抵抗的可能性。而過度依賴暴力的方法顯然是「一個軟弱政權的標誌,在這種政權中,從屬階級(也包括部分統治階級分子)會認為自己處於不公的境地,並試圖改變它」。因此,更好的方案應該是一種從統治群體到從屬群體,人人都覺得當前體制公正合理的局面,即「確保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使用權力的局面在大多數社會成員眼裡是無比自然的,或者根本就不讓他們意識到」。這就需要非暴力的ISA手段來調節社會矛盾、複製階級關係。ISA指通過宗教、教育、大眾傳媒等手段對從屬階層行使隱含的權力。由於這種隱秘性,ISA更為高效和恐怖,沒有它的支持與協助,RSA根本無法長期維持社會現狀。在《緬甸歲月》中,英國人對印緬殖民地行使權力,不僅利用了警察、軍隊和刑法制度這些壓制性國家機器(RSA),更利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這個無形的武器實現了思想上的統治,把一種人為構建出來的劣等民族身份強加到土著頭上,並讓他們予以認同,從而將自身的優勢地位永久化。

《緬甸歲月》
「身份」(identity)一詞在字面上是「同一」的意思,即將個體視為某個群體成員所依據的一整套行為或個人特點。根據巴赫金的觀點,所謂「自我」是抽象與空幻的,只有通過與一個坐標點(即「非我」)的不斷比照與互動才能實現自我認知,這個對構建自我不可或缺的坐標點即為「他者」。換言之,自我(感知者)與他者(被感知者)並非作為單獨的實體孤立存在,而是作為「兩個坐標之間的關係存在……彼此進行區分」在種族政治中,身份的建構和區分往往不是生物意義上的,而是文化和思想意義上的,並且常常伴隨着誇大與扭曲,成為「一種用以支持和鞏固帝國主義自我界定的產物」。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言,既然人們總是通過「我們不是什麼」來界定自我身份,那麼「我們所不是的」就必然被客體化和妖魔化為「他者」——「瘋癲、任性和相異之人被內化為『他者』,這樣有助於我們鞏固自己的身份:他們的存在意義,僅僅就是證明既定權力的合理性」。
歐洲人深知構建一個對立面的形象對自身至關重要,隨即將目光對準了東方人。為了把二者區別開來,他們把東方人簡化成一種固定的形象,總是跟無知、野蠻、骯髒相關聯,以此來襯托自己的種族優越。換言之,在歐洲人身份構建的過程中,東方人失去其真實的身份,被迫變成他們被期待的樣子。賽義德曾提出:「東方是歐洲的文化對手,是其最深刻和最常見的他者形象。此外,東方作為對照性的形象、思想、個性、體驗,也有助於界定歐洲(西方)」。不管這種形象正確與否,它「一直是大眾的參照系」。其結果便是:歐洲人認為自己的優越感乃是理所當然,並希望被殖民者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即有意無意地以歐洲中心觀為先決條件)內在化,從而習慣於毀損自己的民族、接受自身的從屬地位。
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
在《緬甸歲月》中,歐洲人在各方面都強調自身和緬甸土著的區分,因為任何模糊這種區分的行為都會對他們的身份構成潛在的威脅。這讓人想起霍米·巴巴的「模仿人」概念——所謂模仿人,就是深受宗主國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他與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對殖民權威構成進攻型威脅。殖民話語中模仿人的在場,就是針對殖民權力表徵結構的解構」。 這種例子遍及整個小說——埃利斯是一個典型的英國沙文主義者,此人鄙視緬甸土著,其無禮之言充斥整個故事,如「這個國家暴亂橫行就是由於我們對他們太手軟了。唯一有效的政策,是把他們當成臭泥」。與這種公然的咒罵相比,書中的一處細節更能體現英國殖民宣傳(即把先進文明引入落後國家)的虛偽:在一個驕陽似火的早晨,埃利斯問俱樂部管家還剩有多少冰塊。當管家回答「我發現如今保持冰塊低溫可真夠困難的」(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keep ice cool now)的時候,埃利斯勃然大怒。發火的原因倒不是因為防暑的冰塊不足,而是由於土著管家的英語過於標準和文雅:「你他媽的少這麼講話——還什麼『我發現可真夠困難的!』難道你剛吞了一本字典不成?『對不起,主人,冰塊冷不了』——這才是你該說的話。哪個傢伙英語開始講得太好了,我們就得讓他走人。我可受不了會講英語的傭人」。在英國人高傲的作態下,是一種潛伏於所有帝國主義者心中的恐懼,這種恐懼導致征服者無法容忍土著的任何才智——雖然從純語言學的角度講,英語並不優於其他語言,但在英國人的心目中,一口文法嚴謹、措辭文雅的英語,代表着良好的修養和顯赫的身份,假如土著變得和他們一樣有教養,其「他者性」自然也就不復存在,隨之一同消失的自然還有英國人的優越感。因此,殖民者對土著的教化(哪怕只是象徵意義上的)只能有限度地接受。正如阿特金斯所言:「帝國的偉大時代,就是他們帶領土著奔向文明之光的歲月,而當這光芒真的就在眼前的時候,卻變得不能忍受」。
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歐洲人對待宗教的態度上——故事中的英國人沒有幾個真正相信教義,但他們又把基督教看做自身與土著之間差異的象徵,由此出現了殖民時代頗具諷刺意味的一個現象:西方傳教士不遺餘力地宣揚教義,勸說土著信仰基督,而普通歐洲人則對土著的皈依充滿恐懼,害怕由此導致身份上的混亂。在《緬甸歲月》中,埃利斯本是個憤世嫉俗、褻瀆神靈之輩,在祈禱時總是用讚美詩集擋着臉低聲咒罵上帝,可面對土著信徒的加入,又儼然一副基督教捍衛者的姿態:
「我可受不了那些他媽的土著基督徒擠進咱們的教堂。一幫馬德拉西傭人和克倫人教師,還有那兩個黃肚皮,弗朗西斯和塞繆爾——他們也自稱是基督徒。牧師上一回來咱們這兒的時候,他們倆居然膽敢跑到前排跟白人坐在一起。應該有人出來跟牧師說說才對。我們對那些在緬甸的傳教士聽之任之,真他媽傻到家了!居然去教那些集市上掃大街的,說他們跟咱們沒什麼分別。『抱歉,先生,我是跟主人一樣的基督徒啊。』真他媽厚顏無恥。」
在埃利斯眼裡,東方人就應該維持低劣、野蠻、粗鄙的他者性,他們在任何方面與歐洲人的趨同都會破壞歐洲人用以自我界定的參照系。正因為這樣,歐洲人不肯與土著交往,而是封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整天在俱樂部打牌飲酒、閑談漫扯,生活死一般的沉寂和無聊。
主人公弗洛里不同,他對東方文化異常痴迷,十分反感帝國主義統治以及本國同胞對土著的蔑視。雖然他也曾酗酒狎妓、沉淪度日,但是對自身乃至整個大英帝國的墮落卻能感到道義上的羞恥,對身邊同胞的矯揉造作和無知自大深感嫌惡。因此,他走出俱樂部,與緬甸本土社會建立了廣泛聯繫——他不光同僕人科斯拉以及醫生維拉斯瓦米關係密切,還同中國雜貨商李曄交好,這些關係同帝國主義理念以及英印地區的種族隔離與等級制度背道而馳。因此在其同胞眼裡,弗洛里的言行實屬異類,而他跟維拉斯瓦米醫生之間的友誼,更是破壞了他本人在白人社區中的種族身份。埃利斯把弗洛里比作美國黑人教育領袖布克·華盛頓,把他蔑稱為「黑鬼的夥伴」,以此將其「他者化」。就連初來乍到、對弗洛里尚有好感的英國女孩伊麗莎白,也對他領着自己到土著社區觀看當地的皮威戲感到困惑不解——弗洛里對美好生活尚有企盼,巴望能有一個異性知己來分享自己的感受,去除心中的落寞與孤寂,所以才對初來緬甸的伊麗莎白充滿了遐想和期待,可對方根本不欣賞這種蘊藏在原始文化中的美,心裏只有惶恐與不安:「她環顧四周,看着這大片的黑色臉龐和可怕的火光;這奇怪的場面令她驚恐。自己在這種地方做什麼?毫無疑問,像這樣坐在黑人當中、幾乎觸碰到他們、聞着他們身上的蒜味和汗味,這難道對嗎?為什麼自己不回俱樂部跟那些白人在一起?為什麼他把自己領到這兒,跟這群土著在一起,看這種醜陋野蠻的表演?」只有在返回俱樂部以後,伊麗莎白才感到安全和寧靜,因為俱樂部那種「溫文爾雅」的氛圍,還有四周那一張張白人面孔,都能讓她倍感安定。
小說還有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意象就是弗洛里的胎記。雖然在故事中被描述成「暗青色」,但在埃利斯眼裡,這個胎記根本就是黑色,——「就我看來,他也有點太布爾什維克了。我可受不了誰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統,我也不會感到驚訝的,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他臉上有塊黑斑的原因」。根據後殖民理論,膚色是種族政治這一指涉體系中的能指,而所指其實是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與膚色類似,胎記「暴露了弗洛里的他者性,是其非英國性的標誌」,象徵了他對緬甸土著的認同、對種族界限的挑戰;而在他自殺身亡後,胎記代表「他者性」和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隨之消失,於是也就慢慢褪色,成了一塊淡淡的灰斑。反觀遭受殖民統治的土著,帝國主義者人為建構的身份左右了他們的言行與思維,甚至成為某種無意識,以至於他們把這種強加到自己頭上的身份看得十分自然。詹明信借用弗洛伊德有關「壓抑」(repression)的思想,提出了「政治無意識」的概念,認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壓制「革命」——不僅壓迫者需要政治無意識,被壓迫者也同樣需要它,假如「革命」沒有遭受壓制,他們反倒無法承受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說,東方人在有意無意地根據西方人構建的他者形象塑造着自己。在《緬甸歲月》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此人謹言慎行,為人謙和,但極度崇拜歐洲文明,堅信東方人天生比白人低劣,單憑自身無法成就社會進步,而要依靠英國先進的管理技術來拯救這片落後的土地。他那一口句式冗長、極不自然的英文,是當時印緬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跟白人朋友弗洛里的爭論中,當對方斥責大英帝國「就是一部為英國人提供貿易壟斷的機器」時,作為被統治民族一員的維拉斯瓦米卻堅定地捍衛大英殖民統治:
「我的朋友,聽到您這麼說,我感到很可悲,真的很可悲。您說你們到這兒是來做生意的?沒錯,這一點不假。緬甸人靠自己會做生意嗎?他們能造機器、造輪船、修鐵路、修公路嗎?沒有你們,他們什麼也幹不了。……在你們手裡,林子越來越好。你們的商人開發我國的資源,而你們的官員則出自純粹的公德心,使我們得以教化,將我們提升到同他們一樣的水平。」
由是觀之,維拉斯瓦米醫生不僅接受了施加在自己民族頭上的原型形象,而且以西方文化為模範。實際上,當時有很多這種「黑皮膚、白面具」的中高層印緬知識分子持有類似態度,這自然符合殖民者的利益。
俱樂部:種族身份的象徵符號
小說中種族區分最顯著的例子當屬歐洲人俱樂部的排他性。對於駐印英國人而言,俱樂部已不僅僅是一處供娛樂和社交的場所,而是種族身份的象徵符號,是白人至上的中心所在:「整個俱樂部概念可說是這個世界上最具英國性的事物……儘管別處確實也都有俱樂部,但英國算是最超群的俱樂部之國」。在這個國家,「凡是人盡可入的地方都不會受到尊敬」。因此,英國俱樂部常常限制會員人數,以此體現其卓爾不凡;而在英屬印度地區,俱樂部會員資格更是英國人的專屬權利,它能大大強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區別:「這種苦心造就出來的俱樂部會員制,其功能就是一方面確保殖民者獨特非凡的素質,另一方面則是確保被殖民者永遠都是等待被拯救的角色」。由於這種種族排他主義,歐洲人俱樂部在當地土着眼中被賦予了一種神秘感甚至是神聖感:
當你看到俱樂部的時候——那是一座破舊的獨層木製建築——你就看到全城的真正中心了。在印度的每座城鎮,歐洲人俱樂部都是其精神堡壘,是不列顛權力的真實所在,是土著官員和百萬富翁們徒然嚮往的極樂世界。就這一點而言,此地尤為如此,這是因為,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引以為傲之處,就是在全緬甸所有的俱樂部當中,它幾乎是唯一一家從不接納東方人會員的俱樂部。
這家嚴重排外的白人俱樂部儼然成為「英國人的要塞,守護英國性不受外人侵擾的最後象徵」;而對於土著來講,它則代表聲譽和權力的覬望,是一處「遙遠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還要難登的至聖之所」。
20世紀20年代,面對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狂飆以及緊張的種族關係,駐印英國政府發出一份公函,要求尚無土著會員的俱樂部吸納至少一名土著。作為全緬甸最後一個抵制土著會員的俱樂部,這一決定自然在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引起了一陣騷動。除了弗洛里,所有英國人都極力反對,他們一想到「肚皮大、個頭小的黑鬼隔着橋牌桌直往你臉上呼大蒜的臭氣」就感到噁心。究其深層原因,則是因為他們深信:給土著(即使是身處高位者)以會員資格,將無可避免地模糊種族差別,威脅到自己的身份。因此,他們決意捍衛這僅存的公共空間,抵制非歐洲人的介入。
在土著社會中,俱樂部納新的消息也引發了地方治安官吳波金與維拉斯瓦米醫生之間的爭鬥。醫生既是弗洛里的摯友,又是本地職位最高的土著官員,入選的可能性極大。同樣垂涎會員資格的吳波金則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一切代價搞臭醫生的名譽。俱樂部會員資格並非正式官銜,為什麼這兩人還如此不遺餘力地爭取呢?歐洲俱樂部這種物神崇拜般的價值,部分來自這樣一個觀念,即「它是英國性的本質所在,因此獲得了會員資格就等於融入了大不列顛的內在傳統」。換句話說,既然俱樂部已然成為英國性的象徵,那麼一旦土著得以登堂入室,就等於獲得了「准歐洲人」的身份,而這種新身份所起的實際作用要遠遠勝過一千份公文。因此,當弗洛里不明白維拉斯瓦米醫生為什麼如此想要加入俱樂部時,醫生極力強調其中的「聲望」所在:
「我的朋友,這種事情,就是聲望決定一切。其實吳波金倒不會公開攻擊我,他也沒這個膽子;可是他會誣衊和誹謗我。而他的話有沒有人信,完全取決於我在歐洲人中間是個什麼樣的地位……你根本不知道,一個印度人一旦成為歐洲人俱樂部的會員,他的聲望能提高多少。進了俱樂部,你幾乎就變成歐洲人了。任何流言蜚語也不能把你怎樣。俱樂部會員是神聖不可褻瀆的。」醫生將俱樂部視為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壘,一旦獲得會員資格,自己就會變得不可侵犯,誰也不會相信對他的詆毀。這種「准歐洲人」的身份情結也適用於權力爭鬥的另一方吳波金。作為凱奧克他達的地方治安官,他已是權重一方,可在他眼裡,同俱樂部的會員資格相比,自己一生的其他成就都不值一提:
一個低等官員一路爬進歐洲人俱樂部——這將是真正的偉業——而在凱奧克他達更加如此。歐洲人俱樂部,那座遙遠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還要難登的至聖之所!波金,這個曼德勒的光屁股窮孩子,這個小偷小摸的辦事員和無名小吏,將會走進那個莊嚴的地方,稱呼歐洲人為「老夥計」、喝着威士忌和蘇打水、在綠桌子上把那些白球敲來敲去!
這番內心獨白同維拉斯瓦米醫生對弗洛里的傾訴如出一轍。儘管兩人在性格和人品上有着天壤之別,但在對俱樂部會員資格的熱切渴望上實在別無二致。吳波金的妻子瑪金是一個心地善良的緬甸婦女,她對丈夫不擇手段要搞垮維拉斯瓦米醫生很是不屑。可即使是她,在聽到吳波金提到自己意欲躋身歐洲人俱樂部的宏願時,也不禁憧憬起來:「她將在腳上套上長筒絲襪和高跟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用印度斯坦語同歐洲女士們談論嬰兒衣服。無論是誰想到這番景象都會感覺眩暈的」。思考着歐洲人俱樂部及其包含的榮耀,她平生第一次不帶責怪地思量起吳波金的陰謀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弗洛里的最終覆亡同土著人對俱樂部近乎病態的迷戀是分不開的——吳波金對會員資格的貪求,使他必須將支持自己競爭對手的弗洛里除掉;而權力鬥爭的失敗者維拉斯瓦米醫生,對白人俱樂部亦是痴戀不改,最後參加了一家經常有印度律師出入的二流俱樂部,這傢俱樂部最大的榮耀便是其唯一的白人會員,此人由於嗜酒如命而被船隊公司解僱,如今靠修車過活,日子極不穩定——「邁克道格爾是個乏味的笨蛋,只對威士忌和磁電機感興趣。可是,醫生就是不肯相信一個白人會是傻瓜,幾乎每天晚上都試圖讓他參與進自己所謂的『文明交談』中來,可結果總是讓人很不滿意」。
帝國主義的雖死猶生
在整部小說中,帝國主義思想根深蒂固,沒有哪個英國人能夠完全擺脫影響。弗洛里似乎是一個勇於對抗種族政策的悲劇英雄,但他內心也有着遵從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大誘惑。他一方面反抗殖民者強加到土著頭上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在有意無意地按照「白人老爺」的原型形象(即陽剛、高尚、文明)進行自我塑造。儘管弗洛里一心想要平衡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堅持讓土著獲得俱樂部會員資格),但他對土著女性的態度卻十分符合帝國主義邏輯——弗洛里的性伴侶緬甸女孩馬拉美始終以一副客體化和他者化的形象出場,如同一個寵物或玩偶,而非獨立的個人:「她那橢圓形的平靜臉龐呈鮮銅色,眼睛小小的,很像個洋娃娃,是那種長相奇特卻異常漂亮的洋娃娃」。「她的牙長得很好,就像小貓的牙一樣。她是他兩年前花了300盧比從她父母手裡買了下來的」。從弗洛里的視角看,馬拉美根本不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女人,而只是一個養來供自己玩樂的寵物。由此看來,弗洛里雖然在某些政見上同自己的同胞激烈抗爭,但實則跟其他英國人沒什麼本質區別。而整個故事中正面人物的缺場,也揭示出奧威爾的態度,即殖民統治對宗主國的國民思想具有普遍的腐化效應。
由於當時的奧威爾尚未形成系統的政治觀點,只有個人道德上的好惡,所以面對帝國主義制度,他並未提出什麼實質性的解決方案,正如茲沃德林所言,《緬甸歲月》「對帝國主義做出了深刻的診斷,卻沒有指出脫離這個泥沼的路徑」。為了擺脫這種罪惡感,奧威爾離開緬甸後即放棄了皇家警察的體面工作,以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與社會底層的勞工、無業者、流浪漢廝混在一起,將自己的關注重點從種族關係轉向了階級關係,以更加敏銳的觀察力和更加犀利的筆鋒創造出了《巴黎倫敦落魄記》、《通往維岡碼頭之路》等作品,為日後深度挖掘社會權力關係的扛鼎之作《一九八四》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