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和圖片均出自網絡,如有侵權,請私信我刪除,謝謝!

1、
我爹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而我,只想當一名平平無奇的錦衣衛。
畢竟能成為皇家的特務,遠比呆在這個小鎮上,守着那座灰不溜秋的瓷窯強多了。
體制內欸,丈母娘都會高看一眼。
說起來,我這個願望來自我們鄰村的二勇。
二勇小時候因為家裡窮,被父母送到了宮裡,本來打算割了的。
結果卻陰差陽錯地被送進了東廠,訓練成了一名特務,現在飛黃騰達得了不得。
去年,他回家來省親,騎的那匹馬要多威風有多威風,連流出來的汗都特么是紅的。
如今,我已二九年華,精神小伙一個,正是成家立業的好光景。
我之所以還留在這裡,沒有選擇離家出走,是因為鄰居家的二丫頭孔慈。
她兩隻杏眼要比鎮子上唱戲的花旦還水靈。
夏日裡,我去河邊取水做泥胎,曾不小心偷看過她洗澡。
月光如水,她似芙蓉,纖纖婀娜,淺淺漣漪。
我躲在草叢裡,緊握着一隻絲滑無比的青蛙,讚歎青蛙居然有那麼長的兩條腿。
我的腦門被蚊子叮了兩個包。
我的雙腳陷進了淤泥里。
爹說,等爹有了錢之後,就在鎮子上給我買一座宅子,要那種青磚紅瓦的,然後把孔慈娶進門,再生一堆胖小子。
我知道,他是想用一個家庭來拴住我這顆放蕩不羈的心。
我很有骨氣的……答應了。
我心裡盤算着,在他幫我買了房子之後,將房子倒手一賣,再帶着二丫頭遠走高飛。
不過,到那時我得看看行情,要是房子的價格還像現在這樣火的話,我就多在手裡留上幾個月。
三年前,鎮子上的竇二傻花了二十兩買了一個小宅子,上個月出手,居然賣了八十兩,娶了仨老婆。
你想啊,我倒騰房子要真賺了錢,走哪不是大爺啊,我又何必在乎那一時半會。
孔慈的爸爸也是個燒窯的。
他老覺得是老伴給女兒娶的這個名字連累了他。
因為他燒出來的瓷器上總有好多小孔,品相不好,總賣不上價去。
所以,他十分想早點讓女兒嫁給我這個二愣子。
一來,他家少張嘴。
二來,等我娶了孔慈之後,我家的瓷器上說不定就有孔了。
我們兩家是競爭對手。
這對他來說是件兩全其美的事情。
那些日子,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和孔慈一起拉着車去城門口的街市上賣我們兩家產的瓷器。
雖然我們兩家不是大明皇帝親封的官窯,但是憑着父親從爺爺的爺爺那傳承下來的技藝,我們家燒制的鈞紅瓷,跟官窯比起來,也是有過之而無比及。
因此,銷量也是不錯的。
只不過,孔嬸一直阻攔。
說非得等我買了宅子後才願意讓女兒嫁給我。
孔叔懼內,所以我和二丫頭的事情就這麼一直耽擱下來了。
我坐在南牆根,把雙手插在袖管里,坐在小馬紮上,眯着眼睛看着面前正手忙腳亂的幫我應付客人的孔慈。
有那麼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夢想突然就沒了。
我覺得,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也挺好。
我一看到孔慈,就想跟她生孩子。
我覺得的她生的孩子一定很漂亮,前提是,長得別像我。
當然,我說的這些都是順利的時候。
我們也經常有走背字的時候。
上次就有小流氓到我們這白拿了一對雙耳瓶回去,我問他要錢的時候,他還揚言讓我在四九城裡打聽打聽他是誰,還要砸了我的攤子。
後來,我就沒屁了。
說實話,我覺得沒文化真可怕,還「四九城」呢?
四九城是指宣德皇帝住的北京城好不好,跟我們這江南的景德鎮有半毛錢的關係?
他要告訴我竄天猴是燒炭的,我要拿正眼瞧他一眼,都算我輸!
還有啊,他讓我打聽打聽他是誰,我用得着打聽么,他爹不就是東門口的柳屠夫么?
我怕的只是他藏在袖子里的那把殺豬刀罷了。
不過,欺人最甚的還是官府的那群巡捕。
有一次,我們在集市上擺攤。
他們非說我們的攤子破壞了官府的風水,把我們的瓷器一通亂砸,沒收了銀兩後還拉走了我們的車。
走出沒一百米,又砸了一個賣菜的老婆婆的攤子,搬了幾顆大白菜放到車上,拉回官府裡面燉粉條了。
我依舊記得孔慈當時的模樣。
她輕輕地走到那位老婆婆的跟前。
掏出我偷偷塞給她讓她買胭脂的幾文碎銀子,塞到了她那雙布滿裂紋的蒼老的手中。
然後,她重新走回到我的面前,拉起我的手。
笑笑地看着我說:「文秀哥,人人都有老得走不動的時候,你說那些壞事做盡的巡捕,等到老了,誰願意對他們伸出援手啊。」
她的頭髮上有淡淡的桂花香味。
我仰起頭來看向她身後繁華的大街。
鱗次櫛比、青磚紅瓦的宅子里,什麼時候才能有屬於我們這樣小小的平民的一座。
2、
「南城附近的宅子價格又漲了,現在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兩。」
這是爹最近常跟我說起的一句話,不同的只是後面一直再往上加的數字罷了。
他說,照這個速度下去,你這輩子都甭想娶孔慈了。
我坐在工棚裡面,用沾滿紅泥的手一邊為一隻夜壺塑着形,一邊抬起頭來看向遠方。
西邊天,一朵白馬形狀的紅雲正隨在晚風向西飄散,飄到了我再也看不見的地方。
見我不說話,爹爹轉身走向了已冷卻的窯口。
在把那一爐瓷器運出來之後,他端詳了一番,突然把手中的一個瓶子摔在地上。
「文秀,你剛才是不是又加柴了?跟你說了多少次了,要注意火候,你就是不聽,看吧,又出了一窯廢品,賣不上價去,爹還怎麼給你買宅子!」
說到此,他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坐在凳子上低頭抽了一會旱煙:
「最近你去街市上應該看到告示了吧,告示上說宣德皇帝三個月後要祭神,命令景德鎮的官窯燒出一種血紅色質地剔透的瓷器來,可是那些官窯卻沒一個燒得出,官府為了討好朝廷,便下了告示,說無論誰燒出了那種紅瓷,不管是官窯還是民窯,都是三百兩的賞銀。所以,爹想試一試,那樣,你的房子就有着落了。」
我猛地轉過身:「不行啊爹,我們怎麼能跟官府打交道,他們的話你怎麼能信。」
爹不再說話,把煙斗裡面的廉價煙葉磕出來,嘆了口氣,緩緩退了出去。
透過破了洞的木窗看過去,不遠處孔家的窯門口,孔叔正在孔慈的幫助下把一車瓷器從窯洞裡面拉出來。
不用問,從老爺子那一直低垂着的腦袋上就可以看出,這次的成品一定也布滿了孔。
整整三個月了,孔家的瓷器一共只賣出去兩件。
一件被人買去當了燈籠罩,一件被城西的宋光頭買去當了花灑。
這些日子,要不是我家暗中幫襯着,恐怕他家早就已經斷糧了。
我洗乾淨雙手,從床下拿了幾兩碎銀子,避開爹的視線,從窯後緩緩地迂迴到他們家。
從窗外看過去,他們一家人正在吃飯。
桌子上擺着的是兌了糠麩的窩窩頭,粥里只飄了幾片菜葉。
我把那些銀子放在他們家窗台上,敲了敲窗戶後就跑掉了。
那一天,我忍着眼淚,一口氣跑到柳屠夫那,為孔慈買了兩隻豬蹄。
我聽人說,姑娘家多吃豬蹄對皮膚好,我可不想孔慈在還沒嫁給我之前就變得人老珠黃!
孔慈將豬蹄從我手中接過去的時候,非要給我留下一隻。
我死活不要,拍着胸脯跟她保證說我身體強壯的很。
我們推來攘去,手就握在一起了。
她連忙把手抽了回去,我們倆也只是敢在街市牽牽手罷了。
豬蹄掉在地上,一隻完好無損地躺在紙上,一隻已經粘滿了塵土。
我將那隻粘滿塵土的拿起來緊緊地握在手中,將另一隻包好,重新遞到她的面前。
我說:「好啦,好啦孔慈,我吃這隻還不行么?」
孔慈不再說話,她就那樣笑笑地看着我,坐在身後的台階上,眼圈突然就紅了。
她一邊拚命地啃着豬蹄,眼淚一邊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豆大的淚滴落進積了幾寸厚的熟土裡面,把塵土砸出一個個的洞,像是擊穿了我的心。
豬蹄上的沙礫硌得我牙磣,我從沒想過,柳屠夫的豬蹄,能做出一種別樣的味道,叫傷心。
我本以為偶爾能有豬蹄吃的日子會這樣平平淡淡下去的。
可我沒想到,我家老豆居然來真的。
在家裡,殺雞都不敢的他,居然敢去揭皇榜!
3、
爹揭下張貼在城門口的皇榜是在那一年的九月。
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瞞着我們的。
他沒有告訴我們,如果揭了皇榜,三個月後沒有燒出皇帝要的那種紅瓷,便是欺君大罪,滿門抄斬。
他是被南城內的宅子給逼瘋了。
那幾日,他時常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研究燒制紅瓷的配料。
他加了鐵粉,加了硃砂,加了磁石,可是終究還是沒有燒出那種像血一樣的艷紅。
而那時尚蒙在鼓裡的我在做什麼呀?
我在偷偷地攢錢,想要為孔慈做一件紅色的嫁衣。
因為在此之前,爹曾信誓旦旦地告訴我說,三個月後他就有錢為我買宅子了。
從小到大,雖然過得窮苦,但他都是一個說話算話的男人。
所以,我輕易就相信了他的話。
現在想來,那時的他,也是是對自己傳承的百年的技藝太過自信,所以連官窯不敢接的活都敢接。
經過幾個月的積攢,我終於在年關將近的時候,為孔慈置辦了嫁衣和首飾。
那一天,當我們從裁縫店裡出來的時候,天已經下起了大雪。
這在景德鎮是難得一見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身穿紅色嫁衣的孔慈顯得很興奮。
她拉着我的手,沿着以為躲避風雪而變得空空如也的長街一路飛奔。
齊腰的黑色長髮迎風飛舞,與大紅色的嫁衣服相得益彰,這樣料峭的節氣,她的掌心裡卻出了汗。
長街的盡頭,她突然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然後眉眼含笑地看着我說:「文秀哥,雖然我們還沒有拜堂,沒有宴請賓客,但我感覺像是真的嫁給你了一般。」
望着她白瓷一般的好看臉頰,有那麼一刻,我突然有些忘情。
我看見輕柔的白色雪花緩緩地落在她清秀的眉目之間,猝不及防般便已消失不見。
我伸出手來,將她耳畔的碎發理順:
「孔慈,我爹說這個月就能把城南的那座宅子買下來了,到時候我們兩個人就能天天在一起了,我們可是轉行做些小生意。我再不要讓你受煙熏火燎之苦。」
話音未落,我便趁熱打鐵將她擁入了懷中。
她的身體可真軟啊,像是抱在了一團棉花上,抱得我微微一顫。
在她身後,積了寸余的雪地上,一個晚歸的貨郎正挑着貨物從街口經過。
在看見緊緊擁抱在一起的我們二人之後,鼻子里冒出兩股冷氣:
「媽的,癟三都能娶老婆了。」
然後,搖搖頭走掉了。
我知道,那老貨是嫉妒我。
他肯定還自作清高地認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呢。
我在大街上抱我自己的未婚妻,關他鳥事啊。
後來,孔慈把嫁衣脫下來,重新包好後,小心翼翼地交到了我的手中,轉向了自己家中。
望着消失在風雪中的那個消瘦的身影,我微微一笑,心裡泛起一股暖意。
我與孔慈素來要好,事到如今已經整整十八年過去了,現在,終將修成正果,怎麼不滿心歡喜。
然而,那一天,當我懷抱嫁衣走回家中的時候,卻發現父親傻了。
他就那樣獃獃地坐在窯洞口的落雪之中,痴痴地望着窯內剛剛冷卻的瓷器不說一句話。
沿着他的目光看過去,面前成千上百的瓷瓶之中,有九成以上全都布滿了裂紋,剩下的一成,也都暗淡無光。
兩行清淚沿着他布滿皺紋的臉旁無聲滑落。
「爹,爹!」
我輕叫兩聲,在確定他本無絲毫反應之後,走上前去輕輕地推了推他的肩膀。
那一刻,他居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他的聲音很低很沉。
那還是我第一次看見我爹哭。
以前,就算是被官府藉著納稅的名義,把一年的積蓄全都沒收,也沒曾見他這般絕望。
後來,伴隨着他斷斷續續的哭訴我才得知——
如今三個月的大限已到,自己卻還沒有燒出皇帝祭天用的那種紅瓷。
眼看一家人就要被推到菜市口砍頭,這才追悔莫及。
4、
爹說,憑藉他的技藝和經驗,其實已經完全掌握了燒制紅瓷的要領。
原本,他還以為是配料上出了問題。
直到最後一窯瓷器出爐,他才恍然大悟,紅瓷的成色之所以顯得暗淡無光,其實是火候不到的緣故。
像我們這種傳統的民間小作坊,窯爐的密封程度一般都不高,所以溫度達不到那樣的高度。
可是事到如今,再想改建瓷窯已經沒有時間了。
無奈之下,父親只好去找負責御窯的那些太監商量,借他們的官窯一用。
可是那些太監,一聽父親能燒出紅瓷,紛紛以各種理由拒絕。
如果父親真的燒出了他們燒不出的紅瓷,那不是明擺着他們無能嗎?
說到此,爹轉身看向窗外。
南城門內的那些高樓玉宇,此刻,在大雪之中,已經模糊的只能看見一抹抹青影。
我坐在凳子上,望着他蒼老的背影,大氣都不敢喘。
我真怕他突然對我說「文秀,爹答應你的宅子買不成了」。
他如果真的這樣說了,我該怎麼辦呀,我連嫁衣都幫孔慈做好了。
好在,爹在沉默良久之後,長長地嘆出了一口氣:
「其實辦法倒有一個……」
我睜大了雙眼。
「那就是泥坯入窯以後,封窯的時候在裡面封死,那樣,整個火窯就可以達到密不透風的程度,溫度就可以達到要求了。」
聽到這句話,我猛地站起身來,大叫一聲:「不行!」
我知道,他口中所說的在內部封窯是什麼意思。
從裡面將窯洞用磚封死的同時,也把人磊在了裡面。
那樣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在高達幾千度的烈火之中,粉身碎骨。
用自己的生命,成全紅瓷的艷麗。
在我大聲喊出那句話的同時,窗外突然傳來了一陣盤子掉在地上碎裂時的清脆聲響。
定睛看時,孔慈已經哭得梨花帶雨地沖了進來。
她本來是要給我送飯的,那一天那家裡燒出了一爐不帶孔的瓷器,孔叔擺酒慶祝,做了好吃的。
結果,聽到了父親的話,便匆匆地撲到他面前,聲淚俱下地央求他不要做傻事。
那一天,在大逆不道地把爹灌醉之後,我和孔慈兩個人手拉着手在風雪之中整整站了一個時辰。
就彷彿,沒有金銀,沒有美食,沒有房屋,沒有瓊樓玉宇,單單只是相愛的兩個人,僅僅是手拖着手,也能夠,天長地久。
那天晚上,孔慈她娘也來勸我爸了。
她說他們家不要房子了。
孔慈依舊嫁過來。
可是,爹眉心愁雲依舊。
皇榜上寫得清清楚楚。
欺君之罪,已經不是我娶個老婆能沖得了喜的了!
5、
朝廷最終也沒有放過我們。
童二勇帶領那幾十名錦衣衛,把我和孔慈一家老少十數人團團圍住,是在三天以後,
那時,我們正拿了行李,準備出逃。
可是我娘非得帶上那些破被褥,要不是因此耽誤的功夫,恐怕眼下我們已經遠走高飛了。
這也不怪她,畢竟,那差不多是我們家全部的家當了。
童二勇就是我一開始說的那個二勇。
除此之外,他小時候還有個諢號,叫作二蛋子。
也許他現在覺得兩個名字都不好聽,居然給自己改了一個名字叫「童統領」。
其實我覺得「銅鈴」還不如二蛋好聽呢。
銅鈴在我們家鄉都是用來拴在驢脖子上的,不上檔次。
我之所以還認得他,是因為看見了他臉上的那道疤。
那疤是小時候我賜給他的。
那時候,他喜歡耍流氓,有一次居然強親了孔慈的臉,於是我就惱了,用一隻梅瓶拍了他,將他的腦袋拍成了醬瓜。
看到領頭的那個人是他,我的心中突然又燃起了希望。
我猛地甩開那幾個小嘍羅,一下子衝到他面前,抱住那匹汗血馬的大腿,央求道:
「二蛋子,你還認識我不,我啊,就是小時候揍你那個。」
我的「揍」字還沒說完,就被他給揍了。
他只那麼輕輕地一仰腳,咚的一下,我就飛了出去。
我的腦袋發矇,腿發嘛,我記得他以前的功夫沒那麼好的。
見我倒地,孔慈連忙跑了過來,蹲在地上幫我查看傷勢。
此時,我聽見她身後的童統領呵斥道:
「既然揭了皇榜,想必就能燒出陛下所要之紅瓷,陳師傅眼下卻為哪般?」
他說話的時候用了個「之」字,看,見見過世面的人就是好,說話都那麼有氣質。
後來,我們又被押回了瓷窯。
眼看皇榜上規定的日子越來越近,而周圍又已被訓練有素的錦衣衛團團圍住,父親和我幾乎陷入了絕望的境地,就差引頸待戮了。
因為擔心父親做出傻事,那幾日,我特意搬進了他的房間與他住在了一起。
我怕他真把自己磊進了火窯裡面,化成了一掊灰燼。
為了放鬆錦衣衛的警惕,以便趁虛脫逃,那幾日,雖然自知無望,我們還是按部就班地按照圖紙上的模樣塑着泥坯。
暗褐色的泥坯擺滿了架子,也不知道過火之後,哪一隻,能夠如天邊的雲霞般艷紅!
第一次發現童二勇對孔慈圖謀不軌,是在那天傍晚。
那天,他一個人悄悄地溜進了孔慈的房間。
等我拎着一根木棍衝到門口的時候,只聽見戚哩哐啷一陣亂響,我還沒站穩,童二勇就從裡面衝出來了。
再次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看見,他那張本來就不知道多精彩的臉上,又多了幾道血痕。
他經過我身邊,將我撞了一個趔趄,將一口鮮血吐在地上:
「娘的,老子在京城什麼樣的女人沒見過,誰稀罕你這個鄉下娘們。」
然後,他仰起頭來,盯着我的鼻孔說:「看什麼看,實話告訴你,七天後,要是你老子還燒不出紅瓷,你們兩家的腦袋都得搬家。」
他之所以盯着我的鼻孔,是因為他的個子實在太矮了。
平常他喜歡騎在馬上,那樣能使他整個人看起來威風些。
我曾偷偷看到過他上馬時的樣子,要在馬前擺一個椅子,讓一名手下趴在椅子上,另外一名手下把他抱上那名士兵的後背,他踩着後背才能翻上馬。
他上馬比翻山都難。
童二勇走後,我猛地衝進孔慈的房間,我看見她正蜷縮在牆角瑟瑟發抖。
她閉着眼睛,手裡握着一把剪刀,胡亂揮舞着叫囂:「你別過來,別過來,再過來我就刺死自己。」
看着她的樣子,我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
「阿慈別怕,是我。」
聽到我的話,她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啪的一聲,剪刀掉在地上,緊緊地抱住了我。
「文秀哥,也許我們這輩子都註定有緣無份了,我們下輩子再結連理好不好。」
「我知道,陳伯斷然燒不出皇帝要的紅瓷,到時我們必定會被處死,只要跟你死在一起,也沒有什麼好怕的。」
破了洞的窗紙里,一絲鉛灰色的天空,透來微薄的光芒。
不遠處的爹爹,正將最後一窯泥坯運進土窯裡面小心翼翼地碼放整齊。
明天就要封窯了,要按照往常在外部封窯的做法,溫度依舊很難提上去。
除非,有一個人,提前進入窯內。
在外面封了以後,再在裡面按照沿着外面這道封火牆的走勢和餘下的空隙,砌另外一道牆擋住冷風。
之所以說只能在裡面才能砌這道牆,因為只有人在窯洞裡面,通過窯內外的明暗對比,才能發現所有的縫隙所在。
這樣想着,我狠狠地咬了咬牙。
打算在明天父親封窯之前,自己悄悄地摸進窯洞裡面,親手砌下這道死牆。
早死晚死都是一掊灰,我又何必執着人世。
反正,就算我能從二勇手中死裡逃生,也斷買不起南城的宅子。
就算孔慈委曲求全的嫁給了我,我也不能忍受眼睜睜看她勞苦終生,疲於奔波。
常言道,貧賤夫妻百事哀。
我的夢想,是讓自己心愛的那個女子,着霞帔鳳冠,住金屋捧銀盞,事事無憂。
她若能如此,哪怕嫁得那個人不是我。
6、
然而第二天早晨,父親終於擺放完了最後一批經過了素燒和釉燒,只差金燒的泥坯了。
結果就在這裡被錦衣衛五花大綁起來。
當然,我也沒能倖免。
一位聲音如同鳥叫的太監,從童二勇的身後走上來,翹着梅花指拍了拍父親的肩膀:
「陳工,如果這一爐燒不出陛下要得極品紅瓷呢,你們全家都得死,現在先綁了,省得過會兒麻煩。」
「我一定能為陛下燒出極品紅瓷。」我爹自信地說。
「燒得出又怎樣,燒出來了我我便告訴陛下是我的官窯燒出的,功勞是我的,同樣得把你們全家處死,哈哈哈。」
我掙扎着想要大罵這個死了之後墳頭上都沒有子孫燒香的老絕戶,可是剛一開口嘴就被童二勇那個王八蛋給堵上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呵呵地對我說:
「放心吧陳文秀,你死之後,我會替你好好照顧孔慈的,你可以安心地去了。」
我的雙手被縛,嘴巴被堵,我想跳起來咬掉他的鼻子都沒可能。
於是,我只能頹然地站在原地,看着那個老太監指揮着自己帶來的窯工,一絲不苟地封起了窯門。
我暗暗地心想,好在自己方才還沒來得及躲進窯內。
現在看來就算我葬身火海,燒出了紅瓷,也斷然救不了全家性命。
半個時辰以後,窯工終於封完了窯。
老太監焚了香,掐算了時辰,方才起火。
足足九個時辰的煅燒,窯門口的磚石都已燒成了紅色。
又經過了三個時辰,紅色漸漸褪去。
老太監才指揮着手下的窯工一塊塊地拆下了封窯的土磚。
然而,當第一道封火牆拆去的時候,面前的窯工卻一個個被驚呆了——
第一道封火牆之後,赫然聳立着另外一道牆。
我的腦袋轟的一下就大了。
父親還站在我的面前,不遠處孔叔正坐在對面的市階上抽着悶煙。
那麼,是誰躲進了窯內,用自己的生命砌下了這一道血牆?
此時,只有孔慈的房間還房門緊閉。
我本以為她是在以這種方式把色眯眯的童二勇,擋在了門外。
現在看來我錯了。
老太監戰戰兢兢地讓窯工們拆掉了第二道封火牆。
此時,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堆早已粉化的白骨。
在骨灰之間,安安靜靜地躺着那隻我送給孔慈的陶制手鐲。
我曾想送給她一隻玉鐲,也曾想送給她一隻金鐲,可是我買不起,於是只能偷偷地做了一隻陶鐲,戴上她的手腕。
我知道,玉鐲會在高溫下變了色,金鐲也會化為一灘水。
惟有早就經過了高溫煅燒的陶鐲,才能在這種情況下,釉色溢出,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我低吼一聲,撞開人群,衝上前去,蹭掉口中的布條,一下子撲倒在那堆灰燼之中。
我的手腳被綁不能動彈,只能像條狗似的,叼起溫度尚存的陶鐲,聲嘶力竭地叫着孔慈的名字。
可是,她卻早已聽不見。
再也聽不見了。
孔慈你好傻,就算這樣,你以為能救得了我全家?
老太監哪裡顧得上我,此時,早已帶着眾人,踩着我的屁股衝進了窯內。
我用身體緊緊地護住那一掊灰燼,我寧願他們踐踏我的臉。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時,童二勇那個王八蛋,居然良心發現,在我身邊緩緩地蹲下,將我扶了起來。
他又找來一隻陶罐將孔慈的骨灰裝到了裡面。
他裝骨灰的時候居然流淚了,眼淚一滴滴地掉進早已冰冷的灰燼裡面,發出噗噗的聲響。
7、
那一天,瘋狂的老太監砸碎了上千件贗品,最終在架子的盡頭找到了一隻艷如雲霞的紅瓷。
那瓷盤,簡約雅緻、細緻紅潤、胎薄如紙、擊聲如磬,實乃亘古未見之精品。
他抱着那隻瓷盤,如獲至寶般的衝出了窯洞。
卻在下一秒,被童二勇擋了下來。
「公公若拿了這件寶貝獻給陛下,陛下肯定龍顏大悅,可是,這東西卻害死了孔慈姑娘,難道你不覺得有點可惜么?」
「童統領不會是傻了吧,這世間哪還有比這紅瓷更珍貴的物件,莫說是一介平民女子,就算是天上的鳳凰,老夫也覺得死不足惜。」
說到此,他伸出手來,拍了拍童二勇的肩膀:
「童統領,今天老夫就告訴你,其實,這人世間啊,女人是最沒用的東西!」
瞧他那話說的吧,他沒那功能,自然覺得女人沒用。
然而他的話卻惹惱了童二勇,只見他輕輕一兜手,長刀便伸伸地刺入了他的胸膛,再一轉身,瓷盤已經落到了自己手中。
噗的一聲,老太監倒地,激起一地煙塵。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童二勇的身手。
我覺得就算他以後失了業,到城東柳屠戶那裡,肯定也能找到一份兼職。
後來,童二勇把瓷盤交到了我的手中,讓我代替父親進獻給皇帝。
我手捧那隻冰冷的紅瓷盤,走在空曠的紫禁城內。
身邊御林夾道,文武膜拜,風光無限,可我突然覺得自己沒了靈魂。
很快,宣德皇帝給我們家產的這種紅瓷取名祭紅,意在祭奠那位為了燒出紅瓷,而英勇獻身的女子。
這宣德皇帝也挺不要臉的,孔慈獻身是為了給你燒瓷么,她只是想要救我們全家罷了。
後來,景德鎮的御窯工按照父親的指點,重新改造了土窯的結構,開始大量生產祭紅瓷。
但是每次封窯之前,都會把封火牆砌成一個少女的形狀。
可是雖然加大了規模,祭紅瓷由於要求過高,十難成一,所以每件都是稀世珍品,平常百姓,難得一見。
後來,父親為我買了宅子,置了田產。
可是,坐在瓊樓玉宇,紅磚綠瓦之間的我,心中卻充滿了從未有過的空落。
我終生未娶,卻經常會做一個夢,夢見我的新娘,披着烈火織成的嫁衣,眉目含笑地嫁給了我。
她說:「文秀哥,從此以後我便是你的妻子了。」
她只輕輕說了那麼一句話,我便老了。
老到再也沒有能力去愛,再也沒有能力去想。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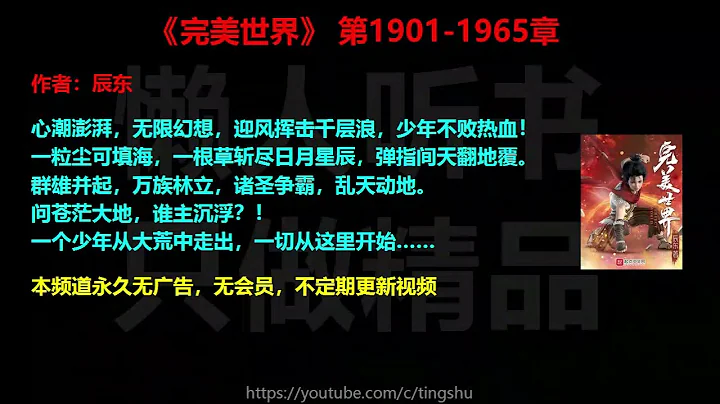










![【搞笑】虧成首富從遊戲開始 [EP176-255] #小說 #繁體中文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lx1W-xi5aE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Qfu9hgfmB9IOhrITD1fLKK0Rf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