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6日,美國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周。雖然相關部門一再表示疫苗安全有效,但美國人的整體接種意願卻並不高。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出台一項調查顯示,全美僅有42%的非裔美國人表示願意或可能接種新冠疫苗,相比之下,白人群體的接種意願為61%。
非裔美國人對疫苗的抵觸,不僅來源於對疫苗安全性的考量,還與美國醫療衛生史上的種族歧視案例有關。至今,許多非裔美國人仍在為美國醫療體系內的種族歧視問題所傷害,平權道路在疫情期間可謂“難上加難” 。

△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非裔美國人中,願意接種疫苗的人甚至不到一半
“黑暗歷史”令非裔美國人難以信任醫療衛生系統
1932至1972年間,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曾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開展一項實驗,目的是“更好地了解疾病(梅毒)的自然過程”。該實驗跟蹤了塔斯基吉市600名低收入非裔美國人,其中399人患有梅毒。
然而,研究者在實驗過程中卻對招募的非裔被試者隱瞞了實驗目的,以此誘騙他們長期配合實驗。研究者讓這些非裔以為醫院在給自己進行免費治療,但實際上,他們並未對這些參加實驗者提供任何治療手段,而是在觀察梅毒自然發展的後果。不僅如此,研究者還對被試者隱瞞真相,稱他們患的不是梅毒,而是“壞血病”。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種族歧視的偏見影響到了醫療衛生的方方面面
因此,許多非裔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將梅毒傳染給了家人,最終導致了許多無辜生命的死亡。這項“罪惡的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體曝光後才終被叫停。
哈佛大學醫療史和科學史教授艾倫·波蘭特說:“這一實驗揭露的不僅是梅毒的病理問題,更多是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問題”。《紐約時報》評論認為,該實驗後,非裔美國人對美國醫療衛生體系的信任逐漸土崩瓦解,其他醫療衛生方面的努力也因此次失信而付之東流。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馬賽拉·阿爾桑和瑪麗安·瓦納梅克的研究顯示,非裔美國人向美國醫療體系求助的可能性普遍要比白人低,並且更有可能因缺乏救治而在年輕時便喪生。此外,分析表明,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預期壽命差距的1/3都可以被歸結為塔斯基吉實驗所引發的失信問題。
非裔美國人對新冠疫苗普遍抵觸
除去“黑暗歷史”帶來的痛苦記憶,非裔美國人之所以對疫苗持抵觸態度,也源於對疫苗安全性的懷疑。《紐約時報》採訪了55歲的非裔美國人丹尼斯·蘭金,她坦言自己對疫苗的安全性充滿質疑,因為她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人們接種疫苗後出現面部神經麻痹,這使她格外擔心疫苗潛在的副作用。

△美國《時代》周刊表示,由於歷史上曾遭受不公正對待,非裔美國人對新冠疫苗持不信任態度
此外,據美國凱撒家族基金會和“不敗”網(The Undefeated)共同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70%的非裔美國人認為,當他們在疫情期間向醫療衛生機構求助時,會因為自己的種族而遭到“不公正對待”,這使他們身心遭受嚴重打擊,加劇了他們對醫療衛生系統的抵觸。調查指出,非裔美國人是在接種新冠疫苗時態度最為猶豫的群體,他們對疫苗安全性的顧慮在日益上升。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非裔美國人對新冠疫苗難以接受。數據顯示,登記參加疫苗臨床實驗的35萬美國人中,只有10%為非裔或拉丁裔。這兩個群體的人口總和佔美國總人口31.9%,但是,美國一半以上的新冠確診患者都來自這兩個群體。即便如此之高的感染率,美國《時代》周刊調查顯示,也只有35%的非裔美國人表示肯定或可能接種疫苗。
種族歧視深藏於醫療體系
其實,非裔美國人所獲醫療資源的質量,至今仍遠低於白人。在癌症和艾滋病治療以及產前保健、疾病預防上,他們只能默默接受美國醫療體系的歧視性差別對待。此外,非裔比白人更難獲得心血管疾病的相關治療,他們也更有可能接受不必要的身體截肢。

△《紐約時報》稱,許多非裔美國人對新冠疫苗有抵觸情緒
不僅如此,非裔還是受鐮狀細胞疾病影響的最主要群體,但該疾病在醫學界獲得的關注度遠低於其他疾病,這也引發了各界學者對醫療研究在種族平等問題上的深思。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伊芙琳·哈蒙茲表示:“在美國歷史上,黑人的健康水平從未與白人持平——歧視和差異是隱藏在在醫療體系系統之中的。”
美國醫療體系內“歷史性”的種族歧視現象,至今仍威脅着少數族裔群體的生命健康,非裔群體在疫情期間求醫難、救治難等現象進一步加劇着美國社會的“撕裂感”和分化。在遍布歧視的土壤中,美國的抗疫之路愈發艱難。
(編輯 楊博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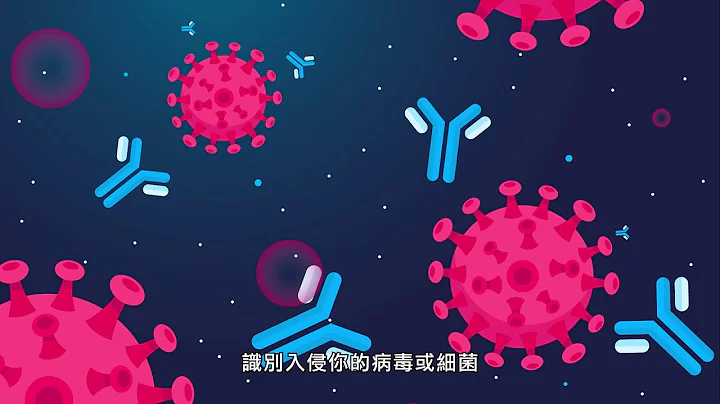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