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歷來為人津津樂道。那場生死瞬間,荊軻拔劍刺向秦王,而秦王倉皇逃跑,侍衛卻未能立即上前救援。歷史上的這一幕令人費解,尤其是當初上學時讀到這一段,我曾認為秦國的侍衛迂腐不堪,甚至覺得秦法過於僵化。為何侍衛眼睜睜看着荊軻追殺秦王,卻因“非有詔不得上”而無動於衷?他們是為了遵守一條死板的法律,而甘願看着自己的君王陷入險境嗎?

當時,我的理解停留在結果層面,認為只要能救下秦王,任何行為都應當被寬恕和嘉獎。然而,參加工作之後,我開始學習和熟悉法律,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細節時,才意識到其中的複雜性。這不足百字的情節,表面之下蘊藏着比想象中更深的法治理念。原來,這並不是單純的侍衛無能或秦法僵化的問題,而是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間的張力。
秦法為何如此嚴格,連拯救君王的行為都可能被判死罪?答案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確立的兩大核心原則:“壹法原則”和“明刑原則”。前者強調舉國一法,任何人無論地位多高,都不得享有法外之恩;後者則強調功過不相抵,即便救了君王,若違反了法定程序,依然不能免除懲罰。這一原則從商鞅時代起便根植於秦國法律體系中,確保執法嚴格公正、不徇私情。

試想,如果當時侍衛不顧秦法的限制,持兵器衝上大殿刺殺荊軻,儘管他們救了秦王,但按照秦法,他們的命運依然難逃死刑。秦國的法律不允許在沒有詔令的情況下執兵上殿,哪怕動機再正當、結果再完美,都不能免除程序違法的事實。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侍衛救了秦王,秦王是否會因感恩而赦免他們?事實上,這是不太可能的。在商鞅的《畫策》中,他明確指出:“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家的混亂源於有法不依,法律若不能被嚴格執行,國家便會滑向衰敗。商鞅變法的初衷就是確保法律的剛性和權威,防止君主或任何人以私情破壞法律的公正性。正因為如此,秦王自己也不敢隨意破壞秦法的原則,否則將動搖整個帝國的法治根基。

更重要的是,秦法不僅要求對違反法律的人嚴格懲罰,還對執法不力的官員進行更嚴厲的處置。在商鞅的法律體系中,執法官員若不行使王法,罪加一等,甚至可能連坐三族。這種對法律執行力的高要求,使得秦國的執法體系異常嚴密。侍衛們非常清楚,即使他們上前解救秦王,等待他們的也不會是獎賞,而是法律的無情懲罰。在這樣的法律氛圍下,他們寧願選擇旁觀,也不願冒着生命危險去違反秦法。
這種對法律的絕對敬畏,正是秦國成為一個強大帝國的基石。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秉持“法外無恩”的原則,幾乎沒有任何例外。因此,秦法的威懾力不僅體現在士兵和官員的行為約束上,也體現在整個社會對法律的尊重和恐懼上。即使在秦王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法律的力量依然主導了整個局面。

回顧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歷史時刻,我意識到,真正讓我震撼的不是荊軻的勇猛或秦王的狼狽,而是侍衛們內心的掙扎。他們急切地想要解救君王,卻被秦法束縛得不敢上前。在那一瞬間,展現的不是秦法的僵化,而是法律的勝利。即便身處生死存亡的時刻,法律仍然主導着所有人的行為,彰顯出古代秦國法治的嚴肅性和力量。
現代社會中,我們經常討論法治與人治的關係,但當我們回望秦國的歷史時,可以發現秦法的嚴格和無情正是其強盛的源泉。虎狼之師不過是秦法的產物,真正令人生畏的,是那套使每個人都敬畏的法律體系。這種無情的法治精神,在當時的燕國、齊國,甚至後來的漢唐都難以見到。

如果我們回到兩千多年前的那個場景,焦點不該是秦王倉皇逃竄的狼狽身影,也不應是荊軻捨命刺殺的英勇姿態。更值得關注的是侍衛們面對秦法時的內心掙扎與恐懼。在那一瞬間,呈現出來的不是秦法的僵硬,而是法律的權威和力量。曾經被認為殘暴的秦國,依靠這套冷酷無情的法律體系,不僅維持了國家的秩序,還展現了其對法治的高度重視,令兩千多年後的我們深感敬畏與唏噓。
當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或許可以從中思考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在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博弈中,真正勝利的究竟是什麼?在秦國,答案顯然是程序正義。這種對法律的絕對遵從,正是秦國成為強大帝國的秘密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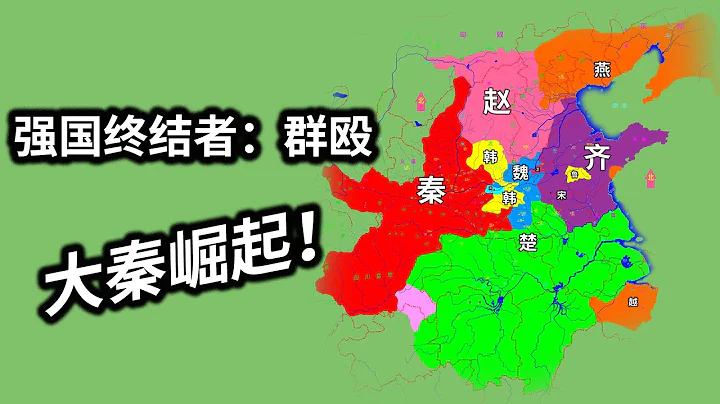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