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立門閥,本是孝文帝擺脫舊勢力,加強皇權的工具。
好不容易有了成效,為北魏擺脫了危機,結果了又迎來了內患,都說兒子和當爹的是一頭的。
結果到了孝文帝這,太子元恂卻成了帶頭反對親爹改革的。

孝文帝時期—漢化道路孝文帝定姓族、遷都南下進入中原,並詔令鮮卑族人必須改漢姓、穿漢服、習漢語。
南下是鮮卑民族歷來的發展宗旨。孝文帝之前的推演、拓踐詰汾率部族南下,但範圍都不大,仍然在草原文化文化圈中徘徊。孝文帝也對南遷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但他有更加宏大的理想。

孝文帝一心南遷,而且在遷都洛陽後,先後三次親率大軍南伐。可以看出孝文帝的意圖在於爭取江南,統一華夏。在如此雄心壯志之下,必須將都城遷至中原中心地帶,才有可能進一步南圖。
但是一旦繼續南下,就會使鮮卑民族脫離草原文化圈,進入中原地區,這必將使鮮卑民族面—個更大的、更不熟悉甚至被排斥的生活環境,此舉必然引起一些守舊人士的反對。

說明當時北魏內部針對南遷已經產生不小的分歧,“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對於此種情況,孝文帝南遷幾乎是在半哄騙半威脅下完成的。
分析北魏鮮卑族不願南遷原因,認為可能有以下幾點:第一,長期生活於草原地區,不習慣中原的生活習俗。
在平城以及北方地區已經培植了深厚的政治、家庭關係網絡,而且土地、財產都在北方,不想既得利益有任何可能損失的情況出現。

在長期的征戰以及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了解到中原漢族的政治模式,明白門閥、豪強勢力在中原地區的發展狀況。所以不希望進入漢文化圈,就是擔心受到漢族門閥勢力的排斥。
孝文帝南遷,要謀求更大的政治利益,這些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那麼在有各種不利因素存在的情況下,孝文帝南遷後應當如何做呢?孝文帝選擇走漢化門閥的道路。孝文帝的漢化思想主要受到明太后馮太后的影響。

馮太后自身極力推崇漢文化,重用漢族士人,所以孝文帝自幼受到漢文化的熏陶。馮太后主政時期積極推行漢化,推行均田制、三長制、整頓吏治等。文明太后的政治主張在孝文帝時期被繼續推行並進一步擴大。
在這樣的漢文化情結下,孝文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統一南北,他選擇漢化的方式來實現,反映在其門閥政策上便是力圖在本民族中培養出一批文化門陶。可以看出孝文帝走漢化門閥道路的目的有三:第一,學習先進漢文化。以落後的民族統治先進的民族,要取得勝利,就必須改變落後的狀態;

贏得北方漢族門閥士族的信任,取得其支持,減少政權建設過程中的阻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走這樣一條門閥道路,是為了適應魏普以來中原形成的門閥與政治緊密結合的政治形態。
孝文帝也走上門閥的道路,是為了對抗漢世家大族的門閥勢力。西晉及南朝傳統的門閥家族,都是經歷過數代的發展,才形成後世的規模。
而孝文帝則是通過人為規定來提高穆、陸等家族的地位,最初定姓族是因為代人“先無姓族”,後人雖然“位極公卿”,其先人卻“居於狼任”。

從中反映出孝文帝定姓族是為了提高部分鮮卑貴族的家族地位,即扶持一部分貴族以與中原大族社會地位相當。
孝文帝努力培植可以與漢族門閥相匹敵的本族門閥勢力,就是希望打亂北方在這些大族控制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利益縱橫、家族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門閥制度已經弊端橫生的時候孝文帝仍然會賦予這種模式以生機,甚至通過皇權來扶持。
第三點可以說是孝文帝的政治意圖,那就是以門閥治門閥,這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僅是民族政策。

所以孝文帝的漢化門閥的意圖便是希望通過走門閥之路以融入中原世家大族的生活圈,籠絡漢世家大族為北魏政權服務,因此這一時期的“門閥化”走的是文化門閥的道路。
通過學習漢文化,講漢語,穿漢服,積極與有名望的世家大族聯姻,以改變自身胡族文化習俗,來更好的融入漢人高等階層。

同時也是為了打亂當時北方漢世家大族已經形成的生存秩序,為北魏政權的發展尋找出路,所以此時的門閥政策更多的是從民族利益出發的,是為了本民族能在漢民族地區幵疆擴土,站穩腳跟。
但不論根本意圖如何,孝文帝成功了。通過他的家族、門閥發展政策,當時人,主要是早期入洛鮮卑族人的思想中已經建立起了門第觀念,甚至會因為姓族而產生糾紛。

但此舉卻拉大了鮮卑族內部的地位差距,對以後北魏政權消亡埋下了禍根,這一點將在後面詳細論述。
總之通過孝文帝定姓族,在鮮卑姓氏之間建立起了高低次序。其中當以元氏即北魏呈族最為尊貴,穆、陸、賀等八大家族次之。孝文帝漢化門閥政策的具體措施:首先,大量封爵。
孝文帝對於鮮卑族門閥化,首先所做的準備就是封爵。孝文帝的封爵行動不同於以往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於功臣的賞賜,他的封爵的一大特點就是範圍廣、人數多。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頭百姓,均有可能被賜予爵位。

而對於一般平民階層如此大範圍封賞,在史書中似乎並不多見。孝文帝之前,獻文帝拓踐弘已經下詔禁止非類通婚。孝文帝又延續了這一政策。這裡所說的“非類”便是被排除在高等門第之外的一般姓氏。
再次,禁胡服、胡語,積極推行漢化政策,籠絡中原漢人。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太和十九年六月,“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而且孝文帝對於穿漢服、習漢語表現出了極大的決心,他曾經在街上見一坐在車中的女子作鮮卑打扮,便立即詔任城王拓拔澄督察此事。

孝文帝以極大的決心積極促使鮮卑族學習漢文化、漢俗,目的就是將北魏朝廷中的胡族按照漢世家大族的標準打造成北魏政權中新晉門閥貴族。
孝文帝還通過祭拜漢族先王、聖人,來籠絡漢族百姓。孝文帝祭祀亮、舜、禹以及孔子發生於太和十六年,距離遷都洛陽還有三年的時間,此時孝文帝已經開始為進入中原地區進行謀劃。
在太和十九年遷都前夕祭拜漢高祖劉邦,再一次祭孔、並且封孔子後人為崇聖侯。孝文帝以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祭拜漢族的先王、聖人,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此舉既是向鮮卑族弘揚漢文化,為後來的遷都、漢化,提前打的預防針,而從漢族來看,則是為了籠絡仍留據北方的漢族勢力,特別是門閥勢力的支持。

通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將北魏貴族,特別是早期入洛貴族逐漸引上了一條門閥化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特點主要是“漢化”,孝文帝希望通過這樣一條捷徑可以達到鮮卑族的快速門閥化。
例如位列八大家族之首的穆氏家族,靠軍功起家,但在孝文帝的漢化門閥政策下,幵始注重家族的文化修養,形成了文武兼治的家族文化。
穆羆之弟穆亮自幼頗有風度,研習歸家經典,官拜太子太傅,孝文帝初定氏族,便欲以弼為國子助教。在平定憲族之亂中有功,加前將軍。入則參與朝政,與皇帝講經論道,出則征戰沙場,稱雄一方。

這在當時以及後世都是一個特殊的現象。而且在東、西兩魏提倡恢復鮮卑文化的政策下,北方地區有沒有可能出現如漢族一般長期存在的門閥現象呢?下面將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
對於北朝“鮮卑化逆流”的研究們知道門閥制度是漢族經過東漢、魏晉,發展而來的特殊階層,那麼在兩個提倡“鮮卑化”的統治集團內部,還有沒有存在的可能呢?所以在研究這兩個統治集團的門閥道路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他們“鮮卑化”的真正意圖何在。

北魏孝文帝痴心漢文化,一生都在致力於鮮卑漢化,在鮮卑貴族門閥化的道路上亦是如此。
然歷史的脈絡沒有朝着漢化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西魏權臣,後被北周追封為文皇帝的宇文泰,這個時候來了一個歷史的迴轉,開始從漢化轉向鮮卑化,他首先恢復鮮卑舊姓:“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
有看法認為這是一次針對漢化的逆流,是歷史的倒退。嚴耀中先生持這種觀點,他在論述北齊“幹祿制”時提出,北齊“幹祿”制的重新出台是對鮮卑舊制的崇拜。

在《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中寫道:“北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制度恐怕與其以鮮卑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強烈反對漢化情緒有關,他們熱衷於崇拜鮮卑舊制,雖然因此後來造成了國力衰退,當時卻在社會上層風行一時,奴役勞動色彩很強的食幹制便是其中之一。”
王永平先生《擁抱文明一十六國北朝改革的啟示》中寫到:“‘河陰之變’以後,孝文帝以來的漢化運動跌落到低潮,而鮮卑化逆流卻由此勃興高歡、宇文泰都出自六鎮中下層軍校。

他們立國所依仗的也是鮮卑化武士,他們做了北方的統治者,意味着六鎮起兵之後六鎮鮮卑軍人獲取了勝利,六鎮兵士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反映在文化習尚等方面,他們一開始都不自覺地倡導鮮卑化,復興鮮卑舊俗。”
王永平先生提到漢化運動的跌落與鮮卑化的勃興,從王先生的文中們可以看到“漢化”與“鮮卑化”之間確乎存在聯繫—此消彼長的關係,但王先生提到這是一種“不自覺”地變化。
對此有一些需要補充的觀點,認為不一定是“不自覺的”變化,有可能是這是一種政策的導向,至午這種觀點恰當與否,以上幾種觀點都認為北朝曾發生的“鮮卑化”是歷史之逆流。

學術界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黃永年先生以北齊為例,指出高歡所擁有的六鎮餘眾多是鮮卑和鮮卑化的漢人,所以所謂的“興胡抑漢”不能完全從民族意義上講。
高氏執政時期,仍是比較重視漢族士大夫與文人,呈族也多與漢人士族或已漢化的元氏皇族聯姻,而至於北齊鮮卑常說的“漢兒”、“漢軍”實際上指的是六鎮鮮卑以外的地方豪強武裝,因為地方豪強武裝中以漢人居多,所以稱之為“漢兒、漢軍”。
即使一直漢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變得更腐敗”。陳先生也認為這是一次退化,但同時也指出“並非全為退化,而是胡漢民族又一次交混產生的新局面”。

總之,北朝的門閥從產生之日起就依附於皇權,藉助呈權發展壯大。
而門閥的存在於權而言是一種統治策略,孝文帝發展鮮卑族文化門閥,目的是抗衡漢世家大族,所以通過鮮卑文化門閥打亂中原的漢族勢力,可以說是打亂牌局重新洗牌。
於是開始了皁權對門閥的置換,最終門閥家族輝煌不再,僅存一種門閥觀念影響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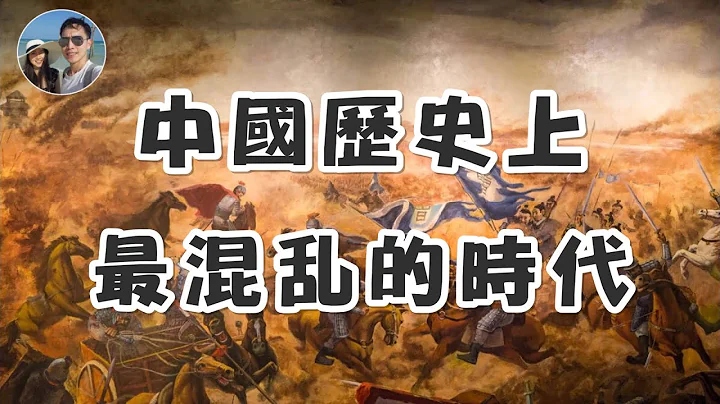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