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雖然在1943年把大量的軍力放在太平洋戰爭中,但是在中國國內,日軍和偽軍在中國南北方都不斷地推動“三光”式的“掃蕩”、“清鄉”作戰,對中國民眾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企圖用這種手段嚇到中國人民。
但是從世界局勢上講,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也舉步維艱,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天平逐漸向盟軍轉移。
當時正在重慶的徐悲鴻為了鼓舞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創作一幅《會師東京》的畫作。

徐悲鴻以“獅”字的諧音,創作了這幅群獅登臨富士山怒吼的國畫——《會師東京》!
許多人都知道徐悲鴻畫的馬是一絕,其實徐悲鴻不僅僅善於畫馬,他也非常善於繪製獅子。
徐悲鴻自己回憶在自己在柏林動物園經常去速寫,“柏林之動物園,最利於美術家。猛獸之檻恆作半圓形,可三面而觀。余性愛畫獅,因值天氣晴明,或上午無范人時,輒往寫之。”
徐悲鴻自己回憶在這裡“故手一冊,日速寫之,積稿殆千百紙。”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1938年,日寇鐵蹄肆意侵踏中華大地,無數百姓被日寇殘殺,大半個國土全面淪喪。
面對此情此景,徐悲鴻悲憤地創作出《負傷之獅》。
在畫面中,一隻受傷的雄獅蹲坐於畫面中央回首而望,雄獅的神情中充滿着憤怒和不甘。
徐悲鴻在畫面右上方題寫道:“國難孔亟時與麟若先生同客重慶相顧不懌寫此以聊抒懷。”
徐悲鴻在畫中把中國比作負傷的雄獅,雖然身體受創,但是雄獅沒有萎靡不振,反而目光中蘊含著繼續作戰的堅韌精神。

再比如同樣是在1938年繪製的這幅《雄獅側目》。在這幅作品中,徐悲鴻同樣把中國比作雄獅,把日本比作毒蛇。
雖然毒蛇盤踞準備向雄獅發起進攻,但是雄獅目光炯炯有神,絲毫不懼毒蛇的威脅。
在畫面左上方徐悲鴻寫道:側目。卓庵先生方家惠教,廿七年七月抗日之際,悲鴻。
而後,隨着戰爭形式的變化,獅子這一藝術形象已經成為作者家國情懷的寄託。
徐悲鴻的獅子畫不僅結構準確,造型生動,是繪畫藝術上中西合璧的典範;而且徐悲鴻的獅子寄託着作者的浪漫主義理想,也已然成為憂國憂民、為振興中華竭盡所能的典型符號之一。

而徐悲鴻的《會師東京》更是屬於獅子畫中的精品。
《會師東京》這一概念根據徐悲鴻初稿題記的記載,是曾經參與辛亥革命,後來在香港做軍事分析的陳孝威所提。
陳孝威是福建閩侯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後來參加辛亥革命,官居中將旅長。1929年離開軍界,1937年遷至香港,創辦了一個全球軍事分析雜誌。
陳孝威曾經在自己創辦的媒體上成功預言德國必定會發動對蘇聯的戰爭、日本和美國必定會爭奪太平洋而名聲大噪。
陳孝威於一次講演中表示:在二三年內,日本必敗,盟軍會師東京已指日可待。
當時在桂林的徐悲鴻被陳孝威的演講所打動,在1942年就創作出《會師東京》的初稿。

圖註:徐悲鴻《會師東京》初稿
在這幅《會師東京》的“初稿”上,徐悲鴻寫道:會師東京初稿,卅一年秋徇陳孝威兄意作於桂林。卅六年冬悲鴻居北平補題。
由題識可知,此幅為徐悲鴻1942年秋作於桂林,1947年再次補題,應為一直隨身之物。
後來徐悲鴻又遷到了山城重慶。
在重慶,徐悲鴻居住在好友的石家花園內。由於日軍空襲頻繁,他白天冒着被炸的危險,坐着小船到對面松林坡的中央大學去授課,下課後就躲進石家花園石崖下,在一個小小的天然防空洞內作畫。
為防日軍飛機偷襲,整個山城夜晚一片漆黑,徐悲鴻就在防空洞燃起煤油燈進行創作,他在這裡又創作了一幅《會師東京》,也就是陳列在徐悲鴻紀念館裡的一幅。

在這幅作品中,畫面正中是一隻怒吼的雄獅,他英姿勃發,雙目怒視前方。繃緊的肌肉、粗糙的鬃毛和雄獅厚重的質量感,使畫面洋溢着一股雄渾的陽剛之氣。
它的左側有三隻雄獅,右側則是一隻母獅帶領着兩隻小獅子。
而這七隻獅子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日本標誌性的富士山。
畫面右上角雖然色調灰暗,有戰雲密布、風起雲湧之感,但是在雲層外似乎正在孕育着一輪紅日。

徐悲鴻在畫面右上角題到:“會師東京。壬午之秋繪成初稿,翌年五月寫成茲幅,易以母獅及雛居圖之右。略抒積憤,雖未免言之過早,且喜其終須實現也。二年端陽前後,悲鴻。”
這幅畫有很明顯的歷史寓意,怒吼的群獅代表了中國和反法西斯同盟;群獅會師於日本富士山山巔,寓意抗日戰爭必將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幅畫極富藝術想象力,也極具時事上的預見力,2年後,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

徐悲鴻曾經說過:“我不能拿槍去殺日寇,但我能用畫筆激勵人們的抗日鬥志,用畫展得來的錢支援抗戰。雖然家人跟着我暫時受了點苦,挨了餓,但聽到前線傳來的一個個捷報,讓我感到心裡坦然,所有的不快也一掃而光,覺得痛快了許多。”
在徐悲鴻紀念館參觀,不僅欣賞學習徐悲鴻的作品、技法,其實更多的是學習徐悲鴻的這種愛國情懷,這也是徐悲鴻留給我們的寶貴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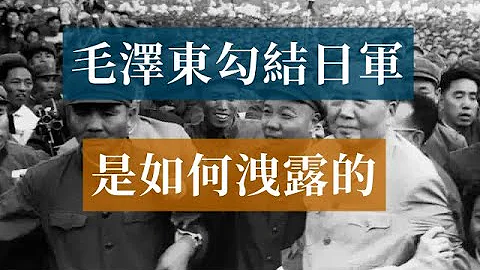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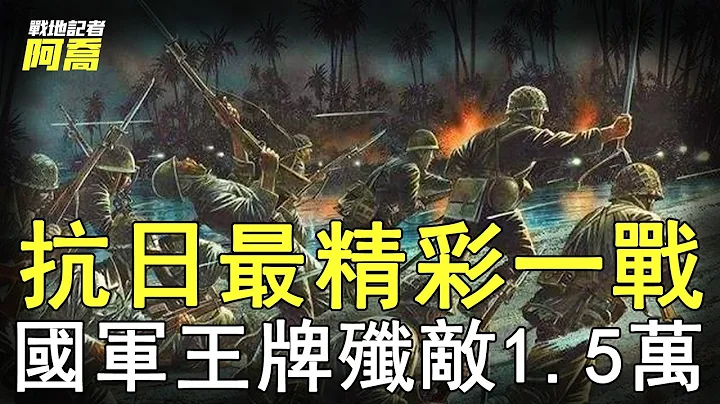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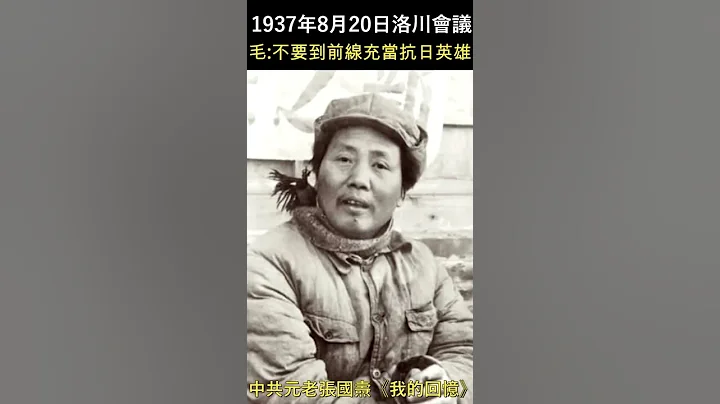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