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妝、穿搭、美容,美甲,甚至醫美、整容,這些都是“服美役”的代表。我們為了實現那個永遠無法實現的慾望——完美的外表——而不斷地催促、逼迫和剝削自身,最終導致自身筋疲力盡。曾經“為悅己者容”的而產生的積極“為己”,轉變成如今的消極“為人”,變美似乎不再是一件能夠令自己開心的事情,反而成為一項負擔、一個服役的苦差。而這難道不是已經直白地暴露出這件事情的問題所在?
如何看待“服美役”一詞的流行?在這一表達背後,有着怎樣的性別差異?今天的文章,就從最近的這一流行詞入手,看看我們如何能擺脫美麗背後的陷阱。
“女為悅己者容”?
中國自古便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之說,兩者並舉一方面說明其間存在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從兩者的相似與對比中讓我們意識到“女容”的重要以及具有的鮮明目的性。它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悅己者”,我們會為了自己喜愛的人精心打扮,所以這句話其實說的也是人之常情。但伴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當下遍佈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媒體中各種各樣關於美妝、護膚和形體塑造的信息鋪天蓋地時,這看似無形的宣傳本身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着我們關於“何謂美”以及如何通過個體的努力才能達到美的認知,而後者更加巧妙地利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告訴人們:只要自己願意且足夠努力,“變美”與達到美的標準往往指日可待。但問題恰恰出現在美的“標準”上。

《再造淑女》劇照。
不同的時代與社會文化氛圍會塑造出不同的“美”的標準,因此也就說明人們關於“美”從來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永恆的標準,但這並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時期內不會出現關於“美”的一些基本形象,從而形成一個標準或典範。如果稍微觀察當下的社交媒體的俊男美女就會發現,在他們為自己設計的形象就潛藏着關於標準“美”的一些基本構成元素。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標準美”也確實是可以被學習、模仿與創造的,當下頗受歡迎的醫美便具有實現這些夢想的能力,因此才成為許多男男女女趨之若鶩的“美之教堂”。
既然存在着關於美的標準,那麼個體就必然要受其影響。我們很多時候其實錯誤地理解了“標準”問題,認為它是一種由別人創造的、相對於我而言外在的,具有規訓個體效應的規範,但實則不然,“標準”自始至終都是一種關係,是我們存在於其中且彼此影響的權力網絡。所以從一開始,當人們討論自己被“美的標準”壓迫或是不得不臣服時,個體自身已經處於這樣的權力關係中,並且是自身的觀念、行為和實踐促使“標準”的繼續生產與施加影響。就如“服美役”這一流行語所暗示的:正是個體與“美役”之間的關係使得後者得以運作並且能夠對前者產生影響。即使在規訓社會,也不存在一種外部的強制力量迫使個體去臣服於某種規範與標準,而是這樣的規訓力量早已經內化進個體的心靈世界,成為韓炳哲所謂的當代績效社會的典型模式:我們要求我們自己去“服美役”。
這就是矛盾所在,個體一方面意識到“服美役”對自己不利或是並非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通過對其的討論、話語的再生產以及實踐令其得以快速地傳播和產生作用。最終就會導致個體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由此便產生了韓炳哲所觀察到的現代主體的最典型癥狀:自我攻擊。我們為了實現那個永遠無法實現的慾望——“服美役”——而不斷地催促、逼迫和剝削自身,最終導致主體自身筋疲力盡。曾經“為悅己者容”而產生的積極“為己”,轉變成如今的消極“為人”,變美似乎不再是一件能夠令自己開心的事情,反而成為一項負擔、一個服役的苦差。而這難道不是已經直白地暴露出這件事情的問題所在了嗎?
當“變美”成為苦差
既然“變美”成了苦差,那為什麼人們還要不斷地逼迫自己去繼續呢?原因也顯然就在於外部的社會文化環境在不知不覺地把外貌塑造成一項重要的評價個體的參數,“以貌取人”這一原本被批評的行為卻成為當下社會重要的看人與取人標準,尤其當涉及女性的工作、家庭和生活時,我們會發現傳統中對於“女容”的要求並未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改善,反而在一個開放的商業社會,消費主義所建構的“美之形象”不僅未能如其所承諾的那般讓女性找回自信,反而漸漸成為她們的負擔以及製造焦慮的生產工廠。傳統的“婦容”被整合在家族規範中的“婦道”,而且其所注重的也並非對於外在形象容貌的要求(且很多時候對此持批評態度),而是希望通過外在的容貌展現出內在的德性。
在現代社會,“女容”本身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它作為個體自我身份、風格與審美的體現得到了尊重。消費主義也恰恰是利用了這一意識形態背景,才能由此建構出一套關於“美顏”與個體主體性的話語體系,並且就如芮塔·菲爾斯基在其《現代性的性別》中所說的,當現代早期的女人們開始走進百貨超市購物時,能夠選擇的自由與感覺塑造了她們對於自我主體性的顯性意識;而當美容顏不再是為了取悅那個賺錢養家、作為戶主的丈夫(它與“為悅己者容”或許還存在差異),而只是為了自己時,現代女性意識也便伴隨着這一過程開始浮出水面。但伴隨着消費主義在資本社會中漸漸強勢,它抓住了消費與女性在“原初”聯結的那一刻所產生的火花,並進一步地在此基礎上建構出一套完美的“消費-美顏-主體性”的網絡,從而為以消費和牟利為目的的美妝行業賦予了一層進步且積極的門面。

《現代性的性別》,作者: [美]芮塔·菲爾斯基 ,譯者:陳琳 /但漢松(校譯),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0年6月
美妝產業精心構建的這一套意識形態至今依舊順利地運作着,並且隨着具體的社會環境與文化背景而能夠快速地進行相應的調整,如在亞洲地區的一眾國外奢侈品牌的代言人漸漸從白人女模特轉向亞洲的或是特定國家的明星。但無論如何更換,通過代言人他們所期望傳達的依舊是一種規範的“美之標準”以及意識形態消費品,品質首先是題中之義,但更重要的還是消費者通過購買而獲得的象徵性身份、審美與品位。當每個女孩都能通過花費一兩百塊錢就獲得迪奧或是香奈兒的當季口紅時,這一消費關係創造了一種雙贏的局面。女孩們消費的不僅是口紅,還有奢侈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徵性價值。而奢侈品則一方面由此擴大客源,增加銷售額,另一方面則被塑造成帶給女孩們自信、美貌與自主性的積極之物,從而也再次增加了它所具有的象徵性價值。
然而,除了美妝產業在建構“美的標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外,主流男性目光以及各種看似中立實則隱藏着強烈男權意識形態的社會結構同樣不遺餘力地強化着女性的外形焦慮。當我們討論“服美役”時,主語幾乎下意識地認為是女性,而男性似乎自始至終都絕緣於“美”的焦慮。難道是因為男性自古以來都是以才智和德性取勝,因此外在形象被貶斥為細枝末節或不值得過分關注的瑣事?然而,這樣的觀念不僅產生自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當下主流男性群體的潛意識,即“化妝=女性化”、“女性化=娘娘腔”,美顏被認為會削弱他們的男性氣質。雖然我們很難理解主流男性群體所讚許的“男性氣質”,但這一邏輯在當下也顯然成為許多男性對自身惰性以及不思進取的借口與擋箭牌。當女性美容顏被與其主體性聯繫在一起時,男性卻可以脫離這一聯結且不會遭到批評,並且還能由此進一步強化他們的男權位置。這樣的不平衡結構在當下遠未改變,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反而被進一步強化了。

《再造淑女》劇照。
當女性打開社交媒體,看到那些身材細瘦、妝容精美的網紅而不由自主地產生焦慮時,當她們困擾於是否要“服美役”時,男性們則似乎並不會因為其他男性的身材和容貌而感到不安或是反思自己是否需要關注下外形;而當結婚後的女性依舊努力地保持身材和每天化妝出門時,丈夫們則早已經放飛自我,大腹便便、形容粗糙……當這樣的現象反覆地出現在我們的身邊而漸漸普遍化後,人們一方面對其的視而不見說明了根深蒂固的關於男女在外形上的規範的不平衡依舊存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疑惑,男性們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難道他們不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嗎?當他們要求自己的女朋友身材消瘦、妝容完美的時候,他們會看到自己的不修邊幅嗎?且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不修邊幅的?
“變美”背後的性別差異
在這背後存在的差異本身就說明了關於男女兩性的規範中所滲入的不平衡並非簡單的日常問題,而恰恰是建立在男權意識形態上的性別制度的產物。“女為悅己者容”在當下受到批評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們開始意識到,“女容”不應該為了他人,即使是喜歡的人亦如此。但當她們為了自己而努力健身保持身材與化妝打扮時,性別制度悄無聲息地運作卻依舊會讓她們對自己的行為是否再次落入了圈套而感到不安。
這裡存在着十分微妙的、涉及個體的日常政治鬥爭,因而就不可能存在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最終,我們每個人只能根據自身當下所處的具體境況來展開具體的政治行動,因為當下的性別權力運作早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命令/恐嚇式”,它如福柯所說的那樣,變成了毛細血管滲入在我們生活的日常之中,因此他才會提倡“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當下許多女性所遭遇的困境,除了傳統中依舊存在的結構性壓迫,更讓她們切身的則是具體且日常的性別權力關係所投下的一片片陰影,它們出現在“美妝”的討論中,出現在關於健身的評價里,同時也存在於工作場所,而更多的則是在戀愛與婚姻里,兩性之間的權力不平衡關係就體現在那些看似瑣碎、無妨且能忍則忍的“小事”中。它們真切地牽動着個體的感覺,並且切實地影響着她們的日常生活和情緒狀態,並且潛移默化地塑造着兩性情感關係。
當各大視頻網站不遺餘力地推出一部又一部古偶、現偶、甜寵、霸道總裁等言情劇時,人們對於其中許多依舊遵循着傳統模式的男女角色和關係的不滿也日漸增多;而像對女生“戀愛腦”、“性緣腦”的嘲諷也再次體現出女性意識到她們在各種流行文化與大眾媒體中的形象依舊十分傳統。而大眾對於言情劇的痴迷、各種歌曲中對於愛情描寫的陳詞濫調,或許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這個依舊以男權為基本框架的社會文化中,提倡或痴迷“戀愛”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動機:作為啟蒙者、主動者和守護者的男性,以及那些千篇一律的等待着的女性角色,愛情似乎成了她們生命的全部,她們也由此被束縛其中。

《再造淑女》劇照。
我們不得不需要對這樣的流行文化現象里的男女兩性關係與角色進行女性主義的再思考,否則我們不僅未能弄明白其中遍布的性別制度的權力網絡,也難以對此真正的批判,進而改變現狀。
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當美遭遇性別制度時,我們卻發現它被規定為是屬於女性的範疇。區別於注重內德與才能的男性傳統,女性自始至終都遭遇着容貌的規範與負擔,並且在現代社會被進一步重組,一方面鼓勵對美的追求,因為它是個體自由的象徵;但另一方面這一鼓勵依舊是性別化的且大都只針對女性。主流男性不僅諷刺愛妝容和打扮的男性,以達到在男性群體內部進行男性氣質等級排序的目的,同時又大加讚美與鼓勵女性努力去達到標準的美,以供他們悅目和“拿得出手”。性別制度在個體追求“美”的過程中的性別化運作如今漸漸被我們識破,因此該如何與之對抗與解構這一聯結也便成為每個個體在遭遇後所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者/重木
編輯/張婷
校對/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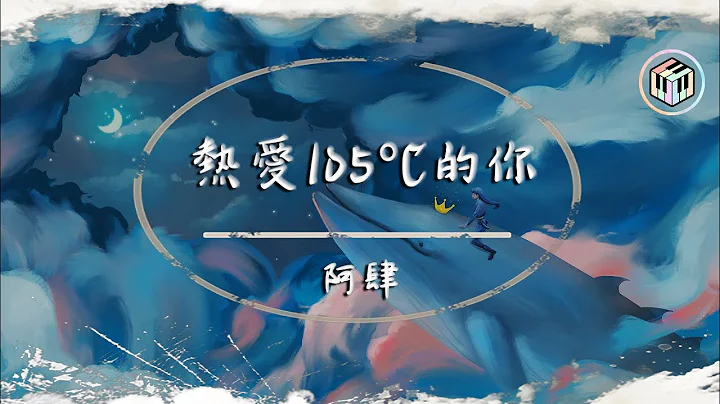







![[ ANNAS ] 正韓小香風針織外套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usHviHh_fvM/hq720_2.jpg?sqp=-oaymwE2CNAFEJQDSFXyq4qpAygIARUAAIhCGABwAcABBvABAfgBzgWAAtAFigIMCAAQARhlIGMoWzAP&rs=AOn4CLDtsV5fHNG03KF076hR53kT5KA3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