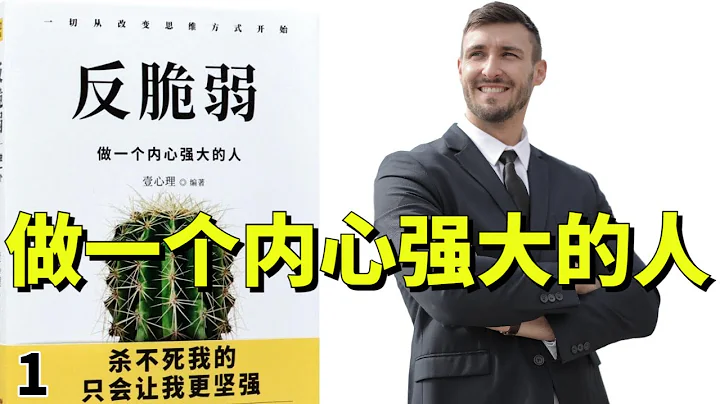那一日家訪,就讀於廣東某二本大學的學生正敏,從舊柜子里拖出一個破爛紙箱給黃燈看。箱子里是可以鋪滿一地的獎狀、證書和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用完的圓珠筆。黃燈數了數,證書41個,獎狀49張,圓珠筆接近200支。
這一場景,在近期出版的《我的二本學生2:去家訪》中,給予了黃燈“電擊般的觸動”——這是一個女孩從農村艱難走向城市念大學時的印跡,也是底色。
黃燈是廣東一所二本大學的教師,從2017年起,黃燈從廣州出發,沿着自己的學生回家的路,一路換乘高鐵、長途客車、中巴車,電動車、摩托車,走進他們的家庭。那些學生的家,散落在地圖的角落裡,是需要數次放大才能看到的小城、鄉鎮和村落。她用數個“正敏”的例子,講述了一個既定的、卻常常被社會誤解的事實:對很多年輕人而言,哪怕是考上二本院校,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家庭傾力托舉。

黃燈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的6月,中國的普通高等院校2820所,其中普通高校1200多所,高等職業專科學校1500多所。這其中,985、211高校只有一百多所,但在現實生活中,名校學生的耀眼,常常遮蔽了沉默且屬於大多數的二本學生。
黃燈說:“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


從正敏曾就讀的小水小學到她在廣東就讀的大學,只要三個小時的車程。但跨越這三個小時,用正敏的話來說,卻是“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
正敏1996年出生,來自粵西山區閉塞的山莊。媽媽是“越南新娘”,爸爸是農民,哥哥初中沒有畢業,正敏自己則是村裡“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學生,也是小學班級唯一的本科生。為負擔她的開支,媽媽必須拼盡全力工作。
正敏從小成績優異,但能繼續上學,全靠媽媽苦苦支撐。她細數過媽媽干過的活:種橘子、上山砍木頭、為紙廠砍竹子、卷鞭炮、到工地攪拌水泥、打包廢紙裝車……所有的工作,沒有一件可以持續、穩定地為媽媽提供過得去的收入。
爸爸對正敏上學態度很消極,不僅沒有給正敏提供情緒支持與安慰,反而說:“跟我呢,我不能保證有錢給你讀書,跟你媽,你就等於把你媽媽賣了拿錢讀書!”她的叔叔也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念書沒什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

紀錄片《出路》
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得知媽媽的收入被正敏拿來念書,從她上高中後就開始明目張胆地找妹妹要錢,每次遭到拒絕,便聲嘶力竭地慫恿妹妹找別人借。正敏向黃燈講述父兄帶給她的壓力,她說自己像是掉進了一個無底洞:“總感覺爸爸和哥哥,在拚命將我往下拉”。
在黃燈的家訪中,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黃燈的學生源盛,曾在作文中這樣描述他生活的地方:
“紅白藍防水篷布下堆放着鋁錠以及一些生鏽的器材。如果不掀開幾塊不起眼的軍綠色防水布,根本無法知道發黑布滿污漬的布下藏着幾道門。幾道門前擺滿了鋁錠,倉庫就隱藏在一片髒亂之下。父親將倉庫清理出放一張小木板床的位置,對我和母親說,以後這就是我們的家。”
初中時,學校離家有十公里,他騎車單程需要踩1個小時。初中三年,源盛常常學習到凌晨一點,為了準時到校,凌晨五點半就必須起床。長期的睡眠不足,導致了源盛的低質量睡眠,每天都只能勉強保持五六個小時的休息。

黃燈在演講中講述她的學生
源盛考上廣東這所二本大學,村莊為此沸騰了好長時間,家裡將親朋好友接來,擺了幾桌酒席。源盛父母希望兒子能留在珠三角,但源盛走出村莊後,雖對故鄉有依戀,卻從沒有想過回來:“沒辦法,為了生存,只能走出去。”
“父母的生計、勞動的歷練、祖輩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這些具體的日常生活,在學生的少年時代,都是一種‘教育資源’。”這使得他們要想從偏僻的鄉村來到城市念大學,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黃燈寫道:“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並由此散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這幾年,黃燈去過鬱南、陽春、台山、懷寧、陸豐、普寧、饒平、湛江、孝感等20多個地方。
有好幾次家訪,黃燈都沒能如願見到學生家長,後來她才知道,無論周末還是寒暑假去學生家,要同時見到父母雙方,並不是那麼容易:有時候雙雙在外打工,有時候一方在外打工,就算臨近過年也要刻意等候,才能見到匆匆而歸的身影。
就算能夠幸運地同時見到父母,他們大都沒有特定的時間用來跟老師交流。難得的聊天機會,更多只能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內開展,或在鍘豬草、煮豬食、織魚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的間隙中進行。
這些場景如此具體、日常而又必然,讓黃燈強烈感受到在這些具體的生計和勞作中,父母已經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孩子的勞動觀、價值觀。這通常會比空洞的說教,來得更為直接和深刻。
黃燈發現,在這些重視教育的家庭中,父母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威嚴身份,他們勤勞、質樸而又堅韌,堅信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對孩子的教育展現出了驚人的重視、不計代價的付出,比如於魏華爸爸為了讓他專註學習,無論多累,晚上都要陪他做作業,堅持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羅早亮媽媽堅持孩子一定要勞動,要分擔家務,絕不嬌慣孩子……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幾乎都具備勤勞的品質,在別人的眼中,他們常常被稱為“懂事的人”。文瑜從初一開始,每逢假期就會進廠打工,每小時工資七元,一個暑假她能賺四千多元;黎章韜在小學就熱衷和村裡的小夥伴們一起撿垃圾、拾廢鐵;羅早亮從7歲就開始學着做飯,作為家裡唯一的男孩,放鵝和放牛的任務由他獨自承擔……
除了父母的角色,他們也與祖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家訪中,黃燈目睹了文瑜給奶奶剪指甲,目睹何健站在爺爺墳前鄭重地追念,目睹章韜外婆慈愛地注視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孫,以及境軍扶着中風的爺爺在寬闊而簡陋的客廳走來走去,她才理解了祖輩毫無保留的情感滋養,怎樣給孩子們傳遞直面現實的力量和勇氣,讓他們走出大山之後,保持着內心的柔軟、情感的豐沛、充盈責任感與力量感。

黃燈觀察到,許多剛入學的學生,“興奮期一過,伴隨考上大學自信的稀釋,現實中洞悉到的種種真相,諸如同學之間的貧富懸殊、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總是很容易將他們推向無力或虛無的境地。”
大山外的世界,足夠新鮮有趣,卻也讓他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因資源差距而來的無奈。一次,正敏與網友討論家庭的經濟狀況,網友們告訴正敏:“當下社會,如果一個家庭拿不出兩萬塊錢,簡直不可思議。”
這讓正敏感到吃驚。在此之前,她一直認為這樣的家庭是社會的常態:“他們整天想着玩,也不幹正事,好像始終沉醉在爸爸媽媽疼愛的世界裡,畢業後通過家人介紹,就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認真地學習,很認真地實習,很認真地跟各種人打交道,畢業之後,有可能找不到什麼合適的工作。”

黃燈的學生曾在一次作文中,用“工業廢水”形容自己
與此同時,擁有大學生身份的他們也在親友們的期盼中,感到一種難言的壓力與尷尬。比如源盛的父親一直堅信兒子“考上大學,工作穩了,前途也穩了”,大伯還以為源盛畢業後國家能夠包分配,有些遠房親戚甚至試探性地問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萬一個月?”
源盛不知道如何向父母親朋們解釋他看到的新世界。

紀錄片《出路》
黃燈有時候很糾結。在去家訪之前,黃燈對二本學生群體的整體去向也是比較悲觀的,如今的大學,早已不具備當年可以“包分配工作”的含金量,這些二本院校的學生,畢業後將面臨嚴酷的擇業競爭,而他們自己和家庭,卻已付出那麼多、抱有那麼深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當她有機會貼近孩子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堅信,就會發現他們身上的力量感與信念感。也因此,學生們已經走向了和留在家鄉同輩人截然不同的命運。
學生文瑜家中,有不少與她一起長大的堂姊妹,無一例外,所有人都延續了“初中輟學——外出打工”的人生軌跡;源盛的堂弟車技驚人,卻沒文化考不上駕照,從而無法進城以此謀生;正敏剛剛上大學時,好幾位小學同學就已經生養了幾個孩子,而她通過讀書得以逃脫父輩那輪迴般的命運:“我爸那樣子,我哥又那樣子,那我哥的下一代,會不會還是那樣子呢?”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
“‘上大學’事實上是他們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機會。”黃燈說,她在種種遺憾和現實中,理解了他們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堅定,“在龐大的年輕群體中,我的學生,就算只能來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課堂,相比更為多數的同齡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圍和幸運,更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現實中無處不在的壓力打敗,終究依仗更為本源的滋養和力量,在喧囂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撰文丨 毛渝川編輯丨毛渝川